“70后”:最后的文人写作(曹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10日10:10 来源:北京日报 曹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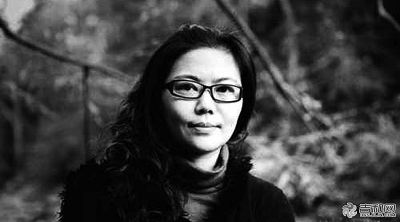 魏微
魏微 鲁敏
鲁敏 徐则臣
徐则臣 张楚
张楚 东君
东君新近出版的路内长篇小说《慈悲》再次引起文坛对“70后”写作的关注。“70后”向来被称为“夹缝中的一代”、“低谷的一代”、“被遮蔽的一代”,他们位于“50后”、“60后”与“80后”之间,既没有赶上充满红色激情的“革命”时代,与宏大意识形态和启蒙理想主义擦肩而过,又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生产利益场失之交臂。如今,“70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甚至离“知天命”也并不遥远,却依然没有能够产生像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那样的领军人物和标识性作品。面对这个各自为阵、难以归类的写作群体,研究者也只能以“复杂性”、“个性化”等词语总结之。然而,如果将“70后”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写作历史的整体链节之中,对这个形态参差的代际从精神气质上进行概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7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文人写作。
出身:最后一代拥有
“乡村故乡”的作家
文人写作与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息息相关。“70后”大多出身于乡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人。他们在“熟人”、土地、村庄、山川中获得的启迪使其在成年后的故乡写作中葆有了柔软和温情。鲁敏的“东坝”系列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温暖、宁静、淡泊、淳朴,有着东方乡土复杂微妙的人情冷暖和伦理;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将运河故乡描绘得湿润丰沛,如同一幅古典写意的水墨画,又充溢着“清明上河图”的烟火气息。李师江的《福寿春》激活了乡村风俗、节气时令之美,付秀莹的《花好月圆》、《定风波》绵密地白描出乡村蒸腾着暖意的境界。这是“记忆的乡愁”,它氤氲着古老的诗意和暖旧稔熟的气息,衔接起了“田园诗”、“山水诗”、“牧歌情调”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即将断裂。随着中国现代性和全球化发展节奏的加速,城镇化建设的迅急进程,以及网络、科技对世界的“平面化”处理,乡土中国正在面临“去根”的危机。作为与乡土中国在血缘和精神上有所维系的最后一代人,“70后”记录故乡,书写记忆,为我们保存了行将消失的“乡愁”的最后面相。
姿态:不俯视,也不精英
文人写作不仅仅是题材的选择,还意味着人文之忧思、之情怀,即对于民生人心的敏锐体察,对于世事变故的温厚哀悯。这种对于贫困、辛劳、卑微的凝重描绘与真挚同情,是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延续下来的感时忧世的中国文人精神传统。在“50后”、“60后”那里,也不乏对于贫穷委顿人生的描写,但由于写作主体自身长久浸淫其中,易于落入“怨憎者”的窠臼。对于普遍在富裕生活中长大的“80后”作家来说,描写这样的生活无异于纸上谈兵。而“70后”,既有对于匮乏的深刻体验,也由于时代的发展及时地止住了匮乏,这使他们有能力描写贫穷、卑贱、痛苦的人生,并持之以平常心、静观心。在“70后”作家中,文人传统在魏微笔下体现得尤为典型。她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异乡》、《家道》等着眼于底层人物和繁华底下的人事,以节制的叙事、情感和柔韧饱满的语言,将贫穷中的高贵、日常中的明亮、世事沉浮中的人性人情刻画得生动起伏。盛可以对打工妹“感情之殇”和“身体之痛”的勾勒,黄咏梅对城市里卑微者、残疾者和“游荡者”残酷生存的展现,田耳对道士、辅警、乡民的日常化书写,滕肖澜对上海小市民的持续关注,都表明了这一代人古老而弥新的人文情怀。他们不俯视,也不精英,而是将自己置于与之平行的视角,不仅看到了无常世事的苦和悲,也看到了那里蕴含着绽放着的光华。魏微在《家道》中借女主人公之口道出,真正的穷人“实在要高贵平静得多”、“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可谓“70后”文人情怀最为庄严纯朴的体现。这种敦厚承接的是废名、朱自清、沈从文、汪曾祺一派于散淡中蕴含热能、在节制中实现生命自足的风格气度。
美学:对高蹈气韵的承接
和终结
将人生进行审美化的做法是中国文人性格、性情和生命形式的外化。形而下的人间江湖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构成了文人写作内在的巨大张力与魅力。在弋舟的《金农军》、《怀雨人》、《等深》、《所有路的尽头》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满载诗歌、爱情、梦幻、理想的美好生活成为当下物质社会的精神反衬。现代人低伏、陷溺于俗世物象之中,只能独自凭吊那逝去的灿烂的时代辉光。这种凭吊本身便蕴涵着“70后”以“迟到的一代”的身份对八十年代进行“文化化”、“诗意化”的慨叹与企及。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曲别针》、《野象小姐》、《良宵》里都有着超拔于俗世之累的精神象征,这使主人公在历经艰辛困厄时依然能够保持对星空、云朵、良夜的追慕。张惠雯的小说洁净、空灵、轻逸、囿于尘世又超脱于此。她的《爱》、《安娜和我》、《蓝色时代》、《书亭》、《场景》写现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对精神、爱情、美的寓言式表达。她以天真明媚之心带着我们重返充满纯真与诗意的年代,并将之升华为一种持久饱满的精神力量。唯有那些在旧梦般的清晨、在草叶和花瓣上写下过诗篇的一代人,才能在坍塌的时代废墟上生动准确地提取并复原那些精神的景致。而这样的一代人,已然是被迅疾发展的现代化列车抛弃的“静物”与“古董”。“70后”,对高蹈气韵有所承接,同时又是某种终结。
在人物塑造、气韵、语言、文意的营构上,“70后”对于中国文人写作继承得较为充分的当属东君。他的小说颇具古意,简淡有味的语言、徐缓有致的节奏、青山流水的意境,构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面相。《苏薏园先生年谱》的主人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小说以“年谱”传记体的形式记载了苏薏园先生历经战争流离的生平,从形式到内容都契合了主人公的身份和内涵。《听洪素手弹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致敬。洪素手痴迷于古琴,造诣颇高,不愿为俗务所累。东君着力于烘托物欲时代中的清高气节,意在“召回”已然微茫衰落的精神传统。他最近的《某年某月某先生》同样也带着低温的古意,主人公东先生就像是安静恬然的隐士,在城市的隐暗角落看浮世潦草,众生败落,于深山幽谷中寻觅别样的心绪。这种古意诗情和悠裕心境使我们得以重温某个遥远时空的中国文化气息,在缓慢下来的叙事节奏里安顿喧闹的心。对传统文化的心向往之与笔力所及,展现了“70后”对古典精神方式的认同。
我将“70后”视为富有文人情怀的最后一代人,将他们的写作视为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接续。这个结论一方面来自于这一代人所处的“夹缝”时代,他们成长和成熟的20世纪70至90年代,正是中国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迭重合的转型期,与文人写作传统紧密相连的前现代在这一代人身上折射出了最后的余辉。这是历史的遗弃性抉择;另一方面,“70后”以自己的叙事格局、精神气韵、文字趣味、静谧智性、心灵秩序共同建构起了趋向于古典的美学风格。“80后”及其之后,也许会有追随文人风范的个案,但像“70后”这样从不同角度予以群体性的展现与热爱的,将会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代。
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