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像与生命记忆(夏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3月08日10:33 来源:文学报 夏 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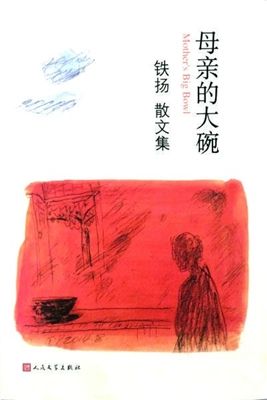
作为读者,我们都有进入文本的方式。
就个人而言,我一直有阅读的习惯。就是不从头至尾顺着看书。而是后进式阅读。从后往前挑拣着看,一本书有没有价值就在这挑拣中显现出来。
阅读是作为读者的经验与作者的经验的相互碰撞和相互映照。
具体而言,就是我在寻找我的个人经验与铁扬先生的人生经验的交集。
我最先读的是这部散文集的“域外记”。莫斯科、丹麦、北欧的艺术、哥本哈根、柏林,这些地域性书写让我怀有兴趣。因为自2005年之后,我有四五年的时间每年都会到北欧,做诺贝尔奖的报道,文学奖、科学奖、和平奖都做过多次,所以对那里的人文景观也算了解。因为了解就对铁扬先生的书写和讲述格外好奇。我看到先生写道:“1991年,我作为中国艺术家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北欧举办个人艺术展。目的地是丹麦,在路上途经正在变革的苏联。”这样的讲述对我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对出现在这本书里的纪年,我怀有个人的兴趣。我想看到书写者的行旅,更想看到他的个人视野。我以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质量,通常是由他的行旅和视野决定的。书写的文本也是。
在“大暑纪事”中,我看到对张爱玲的叙述。我知道的张爱玲热再起是1990年的事情,席卷全社会,它是文青必读。可是铁扬先生的叙述让我觉得有意味,先生阅读张爱玲是在20世纪的五十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阅读张爱玲真正可以被称为是“异端”。
读完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已经约莫了解铁扬先生———作为书写者的个人经验、视野和趣味。有的书,我们愿意信任它的作者,而有的书我们不信任作者。这本散文集的作者,让我有信任感。信任他的人生经验,也信任他的个人品行。
然后我开始认真阅读“人生与艺术”。
由此真正进入铁扬先生的个人历史。我算了一下时间,1935年出生。这刚好是我父亲出生的年月。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饥荒、离乱丛生。那也是个大时代。看到铁扬笔下的那个时代的风云,民国时旧军人、乡间知识分子的生存情态跃然纸上。对逝去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公共化的叙事。包括教科书式和影视化的叙事。残酷、壮烈、血腥、悲伤,这几乎是我们对战乱年代的集体记忆。然而铁扬先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书写提供了异质的经验。它有日常生活的暖意,比如私塾的学习,教堂里的传教士、学唱戏、写标语,这些日常生活的逼真细节充满文本,它提供给我们更为具象的生活。在任何时代,生活都是重要的,人的境况是重要的,人性是重要的。它们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就是这样,经由这种后进式阅读,我了解了这部散文集,也了解了它的书写者。
书写者的心性总能从他的书写中呈现出来。
叙事的简约,文笔的清淡。这是我能从文本中感知到的。
这或许是画家特有的书写风格。但我想更多的还是为人的性情。
一个历经世事沧桑的长者,一个波澜不惊的艺术家。
这是我看到的这本散文集的书写形象。
中国的人文艺术界有一些令人尊敬的长辈作家。比如杨绛、周有光、资中筠、黄永玉。
这些长辈的人生仿佛宽阔的长河,充满奇异风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变迁,他们对于人世真知灼见的书写是宝贵的。这些长辈作家和艺术家我多有接触,现在我看到这个书写谱系里又新出现一位睿智长者,也即《母亲的大碗》的作者铁扬先生。
我最后阅读的是“笨花”之“乡事”。对“笨花”我也不陌生。2006年,第一次做铁凝老师的访问就是缘于她的长篇小说 《笨花》的出版。这也是可以相互映照的阅读经验。一种是历史长卷的文学书写,一种是片段式的印象记,前者浩瀚,后者精巧。
这是不同年代的日常生活的叙事,看似随心所欲,所写之物多是信笔写意,就像绘画中的速写。我对这些文章书写者的好奇在于看到他的个人性。
我以为好作家,包括好的艺术家———要抵御意识形态的侵入和污染,保持艺术感受力和语言的纯粹性。读一部书,我更想看到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经历、见识,他的人生经验,包括世界观,这些特质都能确定一个书写者的品质,也决定书写的价值和意义。
从这本散文集,我看到文本的素朴、沉静、旷达。
它让我想到一个人———孙犁。或许是因为同属一个生活场域———冀中平原。
沉潜、纯粹、淡泊,更为重要的是独立。这是我看到的书写的品质。
我以为这些品质是创造者最珍贵的。
我注意到铁扬先生的个人履历———196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就像我一直注意这本书的纪年。我们知道经历过这些时间的人,也经历过残酷的生活。有很多人是被摧残和毁灭的,比如傅雷夫妇、老舍等等,他们没有活过来。成千上万的人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在这里向铁扬先生致敬,他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镜像,看到生命的记忆,看到日常生活的情致和韵味。也看到人在时间之上的创造。
(《母亲的大碗》 铁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