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知道他的小说在哪儿(毕飞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2月28日10:24 来源:新闻晨报托宾介绍新作《诺拉·韦伯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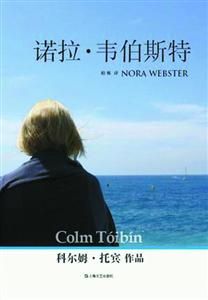 《诺拉·韦伯斯特》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诺拉·韦伯斯特》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7年我12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当时我们家里就是我,我的弟弟以及我的母亲,我和弟弟当时比较年幼,我们非常仔细观察我的母亲,琢磨她的一言一行。当时在我们家里有很多沉默但是也有很多对话,但是这些对话都是为了掩盖情感,而不是为了表达。与此同时,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爱尔兰的一个小镇,当地的风俗和生活的情况把它变成小说的素材,所以这两个事件融合在一起,就是这本新书的缘起。
当时在我居住的小镇上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比如1968年的时候,在我们当地的美容店里就开始使用染发剂,很多中年女士开始学着染发了,不久就会看到很多红头发、蓝头发。你到朋友家里去玩,他的母亲出来突然就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们的母亲也是这样,早上出去的时候头发还是灰白的,回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棕色的头发,所以很多这样的细节我都想编制到关于我出生的小镇的小说当中去。我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我在毕飞宇先生的作品中也觉察到了小说非常擅长的一点,就是刻划描摹人物或者事物非常缓慢的变化,经过几年以后慢慢显现出来的变化,不像电影它可能有爆炸性的连夜之间的转变。我这个小说的跨度是两三年左右,所以我就想通过细节来戏剧化地展现我母亲在这两三年中的变化,我不想让她突然跑到美国去,或者找到一个新的丈夫,再一次进入婚姻,我也不想让她突然有赢得彩票的突然转机。我只想在我的小说中,在小镇的熟悉环境里面,来展现她是如何从巨大的悲痛中克服过来的,在三年的历程中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一个对她来说新的自我的。而且这个发生的背景完全在家庭内部,是在一个非常个人化,有紧密关系相编制起来的一种私人空间。而且我母亲也不是一个圣人,她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面的人物,所以这就是我这个《诺拉·韦伯斯特》小说的主旨,就是爱尔兰小镇上的人物怎么样在三年的时间里面逐渐变成了一个与她原来不同的自我,而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转变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在小说中想探索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我在小说里面主要的事件和场景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但是和整个国家发生的政治风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小说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在看电视,突然大叫起来说我们正在袭击北爱尔兰,我们知道北爱尔兰分成两部分,就是爱兰和北爱尔兰,北爱尔兰目前还是英国的一部分。我在小说里面还是英国的一部分,比如说1968年,就是小说里面的1968年的10月份,在北爱尔兰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然后在1972年的1月份,英国军队又在北爱尔兰射杀了不少无辜的群众,所以这些事件都是在小说里面发生的,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件,它对当地小镇上的人们来说并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事件,但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们觉得他们和北爱尔兰都是爱尔兰民族,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这样的冲突,为什么会有种分裂和矛盾。所以说,像这样的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关系,是我在小说里所讨论的,里面的人物也会对此有所关注。比如其中还有一个女儿,她也参加了1968年10月份发生的游行事件。但是大多数的事件还是在一个家庭内部的亲密空间里面所发生的,虽然它离这个政治背景永远是不遥远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紧密连接,恐怕也是毕飞宇先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吧。
毕飞宇:托宾知道他的小说在哪儿
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近日带着他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访问中国,这本书也为入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书单而大受关注。在由新阅会主办、上海图书馆进行的托宾与毕飞宇对话“小镇,文学的可能与颤栗”中,两位作家深入讨论彼此的作品和写作经验。
托宾的故乡在爱尔兰东南部沿海的小镇恩尼斯科西,在这个人口只有一万人的小镇上,街坊邻居彼此相熟,人们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从《黑水灯塔船》到《布鲁克林》,再到最新小说《诺拉·韦伯斯特》,托宾一再将家乡设定为自己小说的背景。毕飞宇同样来自只有两万多人的苏北小镇,拥有代表作《青衣》、《平原》、《推拿》等。
晨报梳理了本次对话中毕飞宇对托宾作品的解析,尤其是同为创作者对小镇写作和刻画女性的经验对比,其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托宾作为作家的独特存在,也可一窥毕飞宇对什么是好的小说,什么是好的写作的洞见。
毕飞宇
从身体的梳洗开始
托宾先生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起了他在1968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小镇上面女性们开始染头发,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非常触动我,我觉得一个孩子对一个地方的认识首先是从身体的梳洗开始的,你比如说对他来讲一个小镇是什么?首先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颜色进入了小镇的生活,对我来讲也是这样。随着所谓科技的进步,一种全新的气味进入到我的身体激活了我。这个话怎么讲?我生活在苏北的一个叫中堡的小镇子,有两万多人。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强的香味,非常浓,然后我就一下追过去,一看我们镇子里面的理发师,刚刚从大城市里面引进了一个新的理发技术,就是把钳子放在火里面烧,然后给那些女性烫波浪。我不知道那是女性美发用的,可是头发烫了以后那种头发特有的那种香刺激了一个孩子的身体。那是什么?现在回过头去想,那就是小镇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那就是新的生活要素进入了我们小镇的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一个作家的区别是多么巨大,语言和语言的区别是多么巨大,其实每一个人面对生活,感知生活的方式是类似的。否则我们人类就无法交流,否则小说和文学就没有意义,正是由于有一个共通的通道,生活才是可亲的,文学才是可亲的。
就比方说刚才那个头发,因为诺拉的丈夫刚刚去世,她处在一个特别糟糕的生活语境底下,还有两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她决定改换头面,用我们现在的头发叫焗头,她最终选择的是蓝色,我觉得这个蓝色是很考究的。作为一个寡妇她选择红和黄暖色调一定是不对的,她一定是选择一个冷色调,可她的头发就是一个冷色调,黑的,可是黑的对一个人来讲不够强烈对于一个人来讲。她想挽救自己,她又不能用暖色来呈现一个寡妇的身份,所以她非常极端的选择了一种蓝色,我觉得蓝色在这个小镇里面,在这个小说当中就显得特别好。然后在这个部分显示了一个作家捕捉生活的能力。当这个母亲回到家的时候,大儿子和小儿子两个人面对那个完全陌生的妈妈,小儿子看见妈妈的头发变成蓝色的,他用手去摸了摸,就像一个鞋底压在没有头发的脑袋上一样摸了摸里面是什么,孩子很好奇。那个大儿子有点懂了,然后用很鬼祟的眼睛跟母亲对视,当母亲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然后又把眼睛让开。等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又把眼睛挪过去,母亲眼睛回来以后立即又让开。我觉得这种又陌生又家常,又亲昵又有微妙的敌意的那种生活状态,母与子之间的状态在托宾的笔下写的特别好。
我看托宾这本书是在医院里面看的,我觉得人的心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女性。比方说丈夫死了以后有一些遗物,遗孀会处理这些遗物,比方说信件,如果这个遗孀决定嫁人,他一定会把这些信留下来,因为他知道从此以后他属于另外一个男人了。他要让做过自己丈夫的那个男人的笔记,内心独白以物质的形式留在身边。反过来如果这个女人决定不嫁人了,做一生的寡妇,他可能会更加决绝。觉得她和那个已经死去的人像一缕青烟一样可以相互拥有,所以她很可能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把那些信毁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同样是面对遗物,面对丈夫的文字,不同的寄语,不同的未来的走向,会决定这个女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些不同的方式它其实就是日常生活里面很普通的组成部分。对于作家来讲,如何去捕捉,如何去呈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由此判断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内心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特别有意味。
小镇是最难写的
许多作家会去写乡村,许多作家会去写小镇,许多作家会去写大都市。一个作家能把这三个地方都写好固然好,但是在我看来小镇是最难写的。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能把小镇写好,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小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方,也是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地方。比方说村子,上百号人,上海大都市两千万人,可是这两千万人里面到底有几个人和你有关系呢?可别忘了一个小镇有可能是两万人或者三万人,这两三万人对于小镇上的人来讲,差不多都是每个人都要认识的。镇里面社会的关系复杂程度,你不去写,你是很难去想像的。
小镇大,这个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带动性非常大。上海有一个女孩未婚孕,这几乎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可能她妈妈都不一定知道,但是对于小镇来讲几乎牵扯到生活里面的每一个人。我想强调一点是什么呢?虽然托宾先生是欧洲作家,但是我依然要强调他跟英语作家,德语作家,法语作家,西班语作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我说不好,但是我可以打比方,这样我就说的清楚一点,大家也就听的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整个欧洲的文学看成一个时钟的一个面板,上面有三根针,有时针、分针、秒针。如果说法国作家像那个秒针的话,你可以说德国作家或者英国作家像分针,爱尔兰更像时针。你看不到他在动,你看到的仅仅是秒针在动,偶尔你会看到分针在动,你看不到时针在动。尤其你盯着它的时候,你更看不到它动,可是当你回过头去,把一碗米饭吃完了或者说跟朋友聊完了天,你会发现那个不动的东西在顽强地动。所以你要从托宾先生的小说当中寻找那种所谓小说的节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小说都写的50页了怎么还没动。可是等你到100页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了那么多了,刚刚还在故乡怎么都到了布鲁克林了,动和静之间的关系其实特别像小镇,他就是小镇的人,偏远地方的人他所写出来小说的动态跟都市的人一定有区别的。所以,我作为一个乡村出生的人对这个东西要敏感的多。
知道小说在哪儿最重要
托宾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反戏剧性。这个反戏剧性其实从西方的小说来讲经历过一次,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之后,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反戏剧性。到了托宾先生这儿,他的反戏剧性是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儿呢?总体来讲它的小说是写实的,他的小说跟现代主义小说没有线性相比较,他的小说是有线性的。但是有线性的小说放弃了戏剧性,这个是需要一个作家极大的勇气的。我其实可以猜到像托宾先生这样的人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历史,有非常好的,非常全面的阅读历史之后,它可以很安静去做一个选择,我究竟想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这其实是需要定力的,是需要勇气的。
跟《诺拉·韦伯斯特》 比较起来,他的另外一本《布鲁克林》,这个特征显得更加突出,你几乎看不到整块的故事情节,更看不到故事跟故事,事件跟事件,尤其是性格跟性格之间的冲突。冲突丧失了之后,它的戏剧性就没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小说不好看,它依然好看,这就要求着作家对人物比较细微的地方第一你必须要抓得到,第二你必须要表达得出来。有句话我经常引用,就是王安忆赞美迟子建的一句话,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好的,王安忆说迟子建是一个知道小说在哪儿的作家。对一个小说家来讲,知道小说在哪儿太关键了。在一部分作家眼里面,可能小说就在于戏剧性,很可能对于一些更加敏锐的作家来讲,他很可能面对戏剧性视而不见,他能看到更加细微的那些戏剧性。那些地方其实更加动人,只要你耐心读进去,你会发现人生的那个词,汉语里面的说法叫况味。我觉得托宾小说放弃了小说的冲突之后,展现的更加充分的是人生的况味,跟他的小说特别贴。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