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庄到吴镇的梁鸿(刘琼)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20日21:05 来源:文学报 刘琼
观点
作家的乡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面向。阿清离开了吴镇,成为学者梁鸿,又回到了吴镇。寓言式的开篇隐喻了小知识分子在吴镇没有前途的悲剧性。这种命运的设计,暴露了梁鸿对于乡村文化前途的悲观。回到文学内部关系写作,是梁鸿对自己的要求,因此变化对梁鸿是有意义的。至于读者诸君,只要她写得足够好,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接受效果是没有区别的。
从梁庄到吴镇的梁鸿
刘琼
创作中的作家梁鸿正在变化。以新近出版的《神圣家族》(在《上海文学》以“云下吴镇”为名连载)为据,虽然署名“梁鸿”,但与《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的梁鸿,变化显而易见。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怎么评价这种变化?

两个“梁庄”的“冒犯”
首先说两个“梁庄”。
2009年,《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和梁庄迅即被各种文学评论捕获。这不意外。对于文学来说,“2009年”是个什么状况?广大的“底层”(虽然我不倾向于用这个词)凭借坚韧的现实存在,由近十年的“被冷遇”再度成为文学写作的“热情对象”。早在2004年,《天涯》杂志发表一组文章开始讨论“底层”和“关于底层的表述”。“底层写作者”得到支持。2005年,还在流水线上作业的诗人郑小琼获得“年度华语传媒文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2007年,同样是务工出身的王十月加入中国作协。也恰恰因此,2009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和2011年出版的《梁庄在中国》受到关注,有“书写底层”的因素存在,但不是因为底层的梁庄作为文学素材格外新鲜,也不是因为梁庄农民的遭遇格外曲折——显然,梁庄的现实无非是淮河以北村庄的普遍现实,梁庄农民的命运也是历史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普遍命运——从人类学的角度,梁庄既没有环境历史的特殊性,也没有族群形态的独特性,并非一个典型样本。从文学的角度,两个“梁庄”被文学界以及后来的大众传媒广泛关注,正是因为有力地主张了一种文本样式——非虚构写作,重张了一种写作方法——田野考察。文本叙事的独特性和采信的可靠性,使众人在震惊之余,迅速地把它们作为当下现实的一个细节和缝隙接受了。
人类学田野考察在欧美国家被当作基础方法使用是有道理的,文学是人学,由对具体环境里的人类个体进入,才能了解个体和环境、历史传统的关系,理解和思考它们的形成要领。这种田野考察方法,梁鸿之前的当代文学有没有人使用?有。写《黑骏马》和《北方的河》的张承志,写的是小说吗?还是散文随笔?当年有人嘀咕,但没人计较,为什么?作为历史学者的张承志,在行走和调查中写他认知的宗教、历史和族群,强烈的情感代入、深刻的思考和可征信的现实呈现形成了文本的独特价值,作品用哲学厚度、美学深度和情感浓度打倒了大家。
非虚构写作和人类学田野考察这两个名词,作为单独的话题已经议论得很多,此不赘述。通过田野考察,用非虚构叙事法结构文本,把非虚构写作和田野考察关联在一起,是梁鸿写“梁庄”的自觉。梁鸿离开书斋,回到村庄,追到城中村,与亲友们再度在一口锅里搅饭勺,踏着一辆三轮车走街串巷,目的是重新了解和熟悉土地上的人以及暂时离开土地的人的进行时态生活。作为学者的梁鸿,厉害在于,一是有行动能力重新回到乡村,带着情感去介入和观察变化中的乡亲的生活; 二是有眼光看到乡土中国的转型以及转型中的独特文化形态和精神气质,并能占据一个较为宏阔的视野进行思考和判断; 三是有能力把自己的体验和经验凝结成具有冒犯力量的独特文本,而文学文本的魅力正在于这股冒犯力量。两个“梁庄”也使梁鸿的作家身份迅速超越了学者身份。梁庄是真实的梁庄,同时也是梁鸿眼里和笔下的梁庄。梁庄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经过作家文字重构的梁庄。作家梁鸿的重构,使梁庄既熟悉又陌生,从而产生了美感,进入了美学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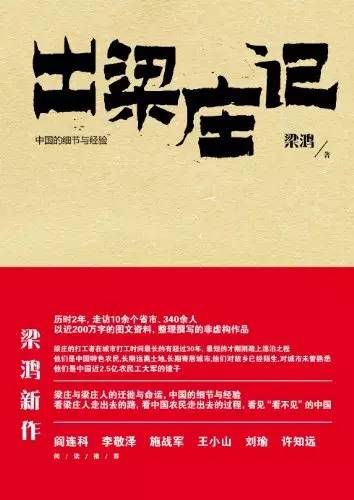
“梁庄”冒犯了什么?
一、它冒犯了非虚构写作的叙事真实原则。
梁庄是真实的存在吗?福伯、五奶奶、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等等,出现在文字中的梁鸿的诸多亲友和生活的村庄,是真实的指代吗?不是!梁鸿首先否认。在中国河南穰县的地图上,我们找不到“梁庄”。梁庄是梁鸿虚构的一个村庄名字,我们为什么就相信这是梁鸿自己的家乡?仅仅因为她写出了艺术真实,符合可然律吗?噢,不,梁庄是梁鸿的家乡,除了物理上的村名不对、人名不对,生活的基本走向和形象细节都没错,原汁原味,却非原型原态。原汁原味是什么?想到了一个字:“豆”。一把黄豆洗净隔火蒸熟,撒上盐油,这是最基础的做法,豆的本质和外形基本没变。一把黄豆粉碎研磨成浆再点卤做成豆腐,黄豆的营养成分没变,形态完全变了,口感也变了。一把黄豆研磨成浆掺加莲蓉、蛋黄、面粉、蜂蜜、黄油烘烤制成莲蓉蛋黄月饼,黄豆成为月饼的诸多配料之一。在这三者中,蒸黄豆需要一把火,做豆腐需要研磨点卤,烘烤月饼需要掺加许多其他食材。前两者讲究原汁原味,豆占据主料。蒸黄豆是原汁原味并原型原态。做成豆腐,还是原汁原味,但型和态已经过“料理”。理论上,这两种“原汁原味”,都被纳入非虚构写作处理素材的筐中。这两种“原汁原味”,对于接受个体来说各有所好,对于写作者,后者的技术要求和时间要求要远甚于前者。研磨和点卤是制作豆腐的技术要领,研磨是对素材的物理形态的处理,点卤则通过添加少量“异物”,形成新的物质形态,是化学处理。在非虚构写作中,从黄豆到豆腐,是从客观素材到非虚构文本需要完成的重构,研磨容易理解,这个点卤如何完成?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卤是什么?仍以两个“梁庄”的写作为例,回乡知识分子梁鸿不是一台简单的照相机,她既怀揣情感,又具有很强的思考能力,这个特点决定了梁鸿对于梁庄的素材处理,既是一台亲切的扫描仪,情感热烈地牵着所有的梁庄的线索往前走,又是一台主旨明确的编辑机,在素材的取舍、剪裁、合成中进行底色设置、细节曝光,同时依据自己的逻辑想象和趣味进行补光、补叙、补白,使主线和主旨更加典型突出。“梁鸿”的在场,既是对梁庄的生产生活常态和乡土固有情感的整理,又是深埋在平凡生活表象之后的中国农村丰满真相的朗读者。整理者的选择,完成的是描述;朗读者的语调,完成的是情感指向。它们结合,最终完成了对乡土梁庄的重构和传播。因此,梁庄是真实的梁庄,同时也是梁鸿眼里和笔下的梁庄。梁庄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经过作家文字重构的梁庄。作家梁鸿的重构,使梁庄既熟悉又陌生,从而产生了美感,进入了美学范畴。非虚构写作也好,虚构写作也好,本质上都是叙事行为。任何一种叙事都具有主观性,虚构叙事的主观性是通过想象试图再现和表现生活,而非虚构叙事的主观性是通过想象,补白、扩大和链接生活的断裂与不足,凸出和显示生活的真相。
二、它冒犯了乡土中国的牧歌化审美惯性。
“解甲归田”“衣锦还乡”……这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满,最终都落实在“田”和“乡”上。“田”和“乡”既指代生产生活的家园,也是精神和情感的家园。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例证。这个例证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反证了文明的发展与人的异化问题。在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由农耕生产生发的乡土精神成为精神本源。在城市化和乡村改造的进程中,个体联系紧密的农耕模式被流水线工业模式篡夺地位,城市对乡村形成空间、能源、劳动力资源的剥削,大规模的劳工迁徙由此产生。每一个离乡者都有乡愁和乡土记忆,在家园被记忆符号化的文学写作中,乡村社会成为现代文化的对立面,被赋予田园牧歌和世外桃源的象征。而现实的中国农村,经济形态变化,生产方式变化,生态环境变化,村庄组织结构变化,人际关系变化,伦理逻辑变化,这还是不是田园?或者这还是不是记忆中的牧歌?谁来讲述变化中的村庄?或者谁来判断村庄的走向?乡土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镇,创作总量不少,但近年来有重大影响者不多,乡土文学遭遇了创作瓶颈。其中,最普遍的问题也是被质疑最多者,是乡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写作技巧的翻新,而是主体认知的“跟上”。
第一,如何认识乡村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把乡村看作独立于现代社会发展之外的桃源,显然是遮蔽现实。把乡村看作从不发达社会到发达社会必须抛弃的一种生产生活形态,更是重大误解。历史的发展是环环有序的链接,解决好乡村发展的历史固有地位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对于农业发展,中央政策已经有所针对,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谈的范围。我想说的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不代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形成,乡村社会发展有其文化自在性。
这就要谈到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不是传统的对立面,它是传统的当下实现。工具的现代化并不必然推动人的现代性。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现代性是社会现代化的判断依据,人的现代性是个复杂问题。具体到乡村社会,人的现代性问题,涉及到对于乡土精神及乡村现代性的认识问题。这个认识直接影响到乡土文学的写作。中国的乡土精神经过二十世纪几次大的思潮的质疑和解构,始终处在不自信状态,一旦外来文化入侵,首先自乱方阵,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两个“梁庄”的写作,既是对田园牧歌真相的揭露,也是对乡土精神旁落的揭露。把儒家文化的“尊者讳”“长者讳”“亲者讳”放在一边,梁鸿带着关切揭开生活的盖子:梁庄既不是牧童横笛的田园牧歌,也不是滞后野蛮的荒村野店,梁庄是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形态并存,人和土地的关系松弛,人和人的联系由紧密的家族血缘姻亲关系过渡到各种生产关系,如雇佣、伙伴、同业、同事,等等。经济关系挑战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妯娌关系等传统伦理关系,新型矛盾出现,生活形态和生命形态丰富芜杂。走出乡村的梁鸿,重新审看乡村社会,既投射不可避免的乡土情感,又不回避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旁观者看来,梁鸿的梁庄具有了相对客观的价值。
三、它冒犯了职业化写作对于现实人生的隔膜和冷漠态度。
心中有,才会笔下有。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对于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最大的问题不是生存问题,而是为赋强作的痛苦。为赋强作的本质原因是,写作者缺乏热切的生命体验和值得分享的经验。经验源自了解、理解。职业化写作容易消磨作家的激情和才华,大量的无病呻吟、顾影自怜和伪装现实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现代文学史上从鲁迅等当年力倡“为人生”的写作基点,到陶行知提出“知行合一”的行动人生,理想其实是一致的———包括文学在内的知识要学以致用,要介入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要进入生活现场,了解民瘼,表现民情民生。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为人生”的写作初心似乎被遗忘、被误读。
“为人生”的写作,主张文学干预社会和人生,也是儒家“兼济天下”思想在文艺领域的衍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梁鸿,不仅文字回到了乡土,身体回到了乡土,眼睛和耳朵也回到了乡土。文学如果不写身处的时代,不写活生生的人,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梁鸿寻觅的写作的意义。两个“梁庄”的成功,也是“为人生”的文艺观的成功。梁鸿是王富仁教授的学生,王富仁教授是鲁迅研究专家,鲁迅“为人生”的文学立场以及鲁迅的作品对于梁鸿这样一位从乡土社会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可想而知,下文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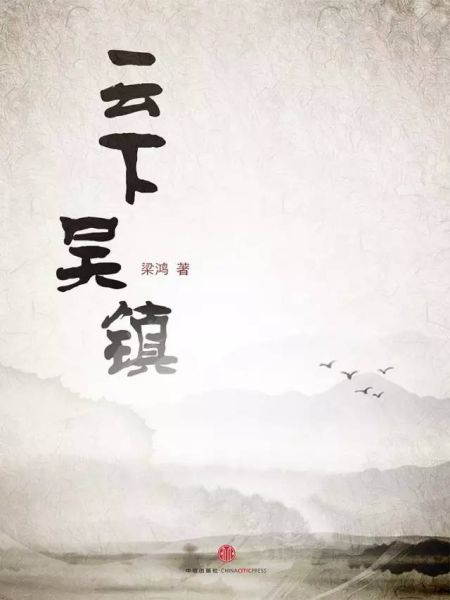 《云下吴镇》将以《神圣家族》之名正式出版
《云下吴镇》将以《神圣家族》之名正式出版 《神圣家族》的局限写作
“为什么写”是问题,“怎么写”也是问题。《神圣家族》应该是在探讨怎么处理生活经验和怎么构建美学形象。
“局限也可以成为平台,也可以成为风格,如果你有足够强大与自由的文心,条条框框可以成为彩绸花棍式的道具”,作家王蒙这段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表达了一个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对于局限写作的理解。“局限”在此不再是泛泛而论,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指通过对写作对象生存环境的刻意限定,在不大的灵魂空间积聚能量,借助对有限现场的放大,厘清对象肌理,催生聚变条件,突破天花板,形成极致呈现,产生爆破美感。局限写作容易产生典型样本,成功范例不胜枚举,苏童、莫言、迟子建、王安忆、池莉等等,都可以算得上通过局限写作而“风格化”。余光中当年说,“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从一个侧面反证了局限写作的深刻性和影响力。从两个“梁庄”到《神圣家族》,梁鸿是在试图进一步发掘自己局限写作的能力。梁鸿说,“我要前进,尽管人们还在看梁庄,但我不能停留在梁庄”。
有评论认为,从梁庄到吴镇,梁鸿是从文学的外部关系写回到文学的内部关系。这话没错,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梁鸿的文艺观也从“为人生”的艺术转变为“为艺术”的艺术?因为“云下吴镇”里的12篇文章,似乎每一篇风格都有变化,作家看来是在写作的技巧上较劲儿。
《神圣家族》是虚构文学吗?许多人要问。文学必然和具体的时间、空间发生关系。这12个故事发生的空间是吴镇,有意思的是,在河南穰县的地图上,吴镇实有其名。现实吴镇的街道布局、房屋户型、集镇风貌,真实地复活在文字中。空间真实的吴镇是不是村名虚构的梁庄的“集镇化表达”?不禁起疑。如果再机械一点,作家梁鸿的家乡其实就是河南穰县吴镇。空间移到了吴镇,人物移动了,时间移动了吗?如果认为吴镇是“梁庄”边上那个集镇,那么发生在吴镇的这些本事,时间在两个“梁庄”前还是在两个“梁庄”后?还是与“梁庄”平行?
神圣家族生活在云下吴镇。“云下”与“吴镇”搭配,是文绉绉加田园。云下吴镇,既是文人化的理想情感的投射,也是大时代下的小空间的聚焦。先来看看吴镇到底是什么样的吴镇?吴镇是梁庄向集镇的蔓延。从梁庄移到吴镇,从乡村移到集镇,土地移走,集市和商贩进入。比较起两个“梁庄”的出出进进、动动荡荡,吴镇过的是相对安稳的岁月。吴镇的安稳,是因为集镇的生产方式相对稳定、经济来源相对固定。集镇是邻近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集镇在文化气质上还是乡土味儿,人、事、物与乡村社会紧密相联,但集镇居民已经脱离土地,生产方式变了,生活方式自然也有别于农民。商贩再小也是商人,集镇再小也有市民,政治文化形态再粗陋也有知识分子,但都需要加上一个“小”字:小商人、小市民、小知识分子。这些个“小”,不是小而精致,而是小而不充分、不纯粹、不满足。“云下吴镇”系列按照主要人物的身份,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以乡镇教师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群体和乡镇里有故事的人物。这两部分着墨最多、形象呈现比较完整的是前者。“云下吴镇”对小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格外关注,与作家的成长经验有关。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学者,梁鸿对于乡村的第一手经验都是离开土地前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作家本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的人生经历。这一经历使她真正接触到了乡土中国的一个特殊群体——乡村教师,对这个群体的生态相对熟悉。这个职业的艰难和尴尬在今天尤显突出,一方面,长期低薪酬,经济状况不好,生活条件恶劣;另一方面,读书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不再被信任,乡村失学儿童增多,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下降,职业荣誉感丧失。受过教育、尚有人生要求的小知识分子既对命运不甘又无力改变,既对现状不满又经不起现实诱惑,投身生活激流又往往水土不服甚至被溺死。对此,作家既怀抱显而易见的同情和怜惜,又对他们性格中的懦弱、犹疑和价值观的不彻底进行解剖和揭批。
《神圣家族》有9篇文章都以一个扩大的小知识分子群体为表现对象,乡镇中小学教师、乡镇医院医生、沦落的老初中毕业生……这些人物具体形态虽异,但在作家的笔下,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 调子起初很淡,有点像汪曾祺的白描,借少年阿清的眼睛扫描吴镇的“隐秘的社会”,少年阿清是“前小知识分子”,他站在树上看清树下的吴镇后,离开了吴镇。这篇文章作为“云下吴镇”系列的开篇意味深长,开放式的结构埋下诸多线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树上的故事——韩少功的《爸爸爸》,树比地面高一点点,树上的视野已是对现实人生的俯视。我们可以发散地想一想,如果阿清不离开,他将过着小镇小知识分子一眼可以看到头的人生。他就是青年的明亮、中年的李风喜、老年的许家亮和德泉:社会和经济转型期被轻视的乡村教师,理想破灭、现实人生失败的失魂落魄者,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许家亮盖屋》里老上访户许家亮,穷困、孤独、落魄、年老力衰后哪怕是退缩和和解也会被碾碎。许家亮的悲剧,不仅仅是制度和人的互塑问题,还有彻头彻尾的无力感,这是12个故事中最令人悲伤的故事。为了调和这个故事的悲伤调子,作家类黑色幽默地写“地下宫殿”建成后乡民的膜拜“盛景”以及色彩、造型和美感的张扬。“文人笔舌武夫刀,抚忧中华气量豪”这副原本荡气回肠的对联,在此因为处境和理想的巨大反差更显荒诞。阿清如果考进中师,当上教师,那就是《明亮的忧伤》里的明亮——青春梦想破灭、职场竞争失败后一蹶不起的小知识分子。这里出现了海红,这个形象的身上有梁鸿的自许,可以看作梁鸿的一种青春祭。《圣徒德泉》具有复杂的表述。小知识分子不彻底的自省,首先让自己找不到世俗的出路,身陷道德伦理危机后德泉疯狂了。“一本书,半卷着边儿,陈旧破烂”,这个孔乙己般的德泉,与受难耶稣相似,都有一个令人抬不起头的风流妈妈,讲着上帝才能听懂的语言,做着拯救弱者和迷途者的事——试图用自认为散发出来的光明“照亮街道、树木、房屋和万物”。圣徒形象,是从小镇医生第三方叙事角度进行的一种讲述。而在多数吴镇人的眼里,德泉早已疯了二十多年。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形成了断裂的语境,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种《狂人日记》。《杨凤喜》里那个日夜在欲望中盘算的小知识分子杨凤喜不过是一个低级的于连,这个人物不值得同情,但这个故事的写法有讲究,生理欲望从杨凤喜的妻子周香兰丰满的胸脯和乳房开始蔓延,写到周香兰、杨凤喜、张晓霞这个三角恋的历史和现在,特别是张晓霞躺在病床上大呼小叫的十段意识流,将小镇小知识分子的婚姻、爱情和职业前途残酷地搅和在一起,成为一潭令人作呕的臭水池,吴镇的小政治大白天下。《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也是梁鸿的青春祭,与《明亮的忧伤》可以对比着看。《肉头》带有传统话本叙事风格——基本是单线叙事,文中主要讲述人也即雪丽,从她的有限角度把乌镇的桃色传闻层层铺开,讲述人间或变化,听众也不断插话,这些都会短暂地改变叙事角度,使故事呈现不至于过于单调。《大操场》其实有志怪传奇味道,写到恐惧和欲望、报应和报复时,中年世故的小知识分子毅志开始了内心反思。
作家的乡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面向。阿清离开了吴镇,成为学者梁鸿,又回到了吴镇。寓言式的开篇隐喻了小知识分子在吴镇没有前途的悲剧性。这种命运的设计,暴露了梁鸿对于乡村文化前途的悲观。作家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好人蓝伟》里,试图要给小知识分子群体重构一个出路:把蓝伟对于现实的“无为”上升到一种主观自觉。“努力淡化失败感”,“无可无不可”,“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美的、对的,妥协也是美的”,等等,这些作家梁鸿忍不住跳出来替蓝伟说的话和想的理,给吴镇小知识分子的人生画出一点精神的亮光。但是,“努力淡化失败感”的蓝伟,在想起没有勇气去探看的女儿时,“眼泪涌了出来”。这些画出来的亮光之虚假不言而喻,小镇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和精神焦虑一目了然。这是梁鸿的矛盾,她不想彻底剥夺亮光,却又给不出理由。
除了小知识分子群体,《神圣家族》的其余三篇,说实话,写得很别致。它们是《美人彩虹》《漂流》和《到第二条河去游泳》。《美人彩虹》写失去青春和梦想的小镇美人,题材不新鲜,但对夫妻关系的本质以及双方在这种关系中的钝化的把握十分精准,人物的体态和内外活动描写得凛冽、生动,既见现实白描功夫,又有后现代虚无感。《飘流》一文有明显的哲学意味。一个坐在轮椅上失去行为和思维能力的老女人,被或盲目或蓄意地推来搡去,最终还是停放在小镇上。这应该是梁鸿对于人生的一种理解。不过,也由于说理意图强,文气反而不够舒畅。比较而言,我当然最喜欢《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女人的故事:嫁了两个丈夫,生了一个孩子,在妈妈喝药自杀后自己也投河自杀。这个短篇前半部分是情感节制,后半部分是意义解构。原本极悲怆的命运却写成了平淡的调性,一个女人人生的最后一天仿佛是在逛街、散步、走亲戚,冷静的动作,零碎的幽怨,小小的不甘,似乎都在撇去悲伤的色彩。漂流在水面这一段,显然是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死去的人集市般地吵闹,争议或纠结令人发笑又伤感,生命尚不足惜,其他的执着、执念有何意义?在漫不经心的死亡面前,生便显得无聊、无趣。这个女人似乎一直在为自己的死找理由。
一个不想变化的作家注定不是个好作家。回到文学内部关系写作,是梁鸿对自己的要求,因此变化对梁鸿是有意义的。至于读者诸君,只要她写得足够好,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接受效果是没有区别的。梁鸿,你写得足够好了吗?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