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吞咽黑暗的动作有如吮吸乳汁(云也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0月13日10:23 来源:北京青年报 云也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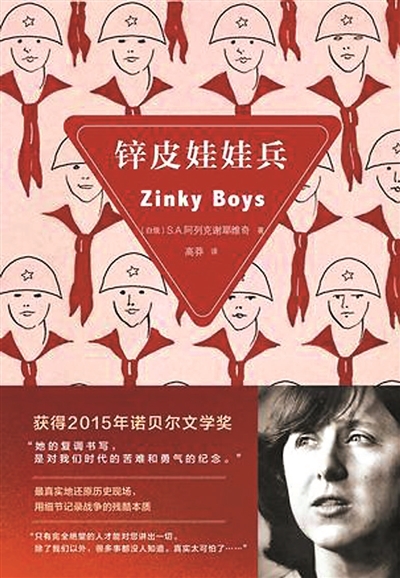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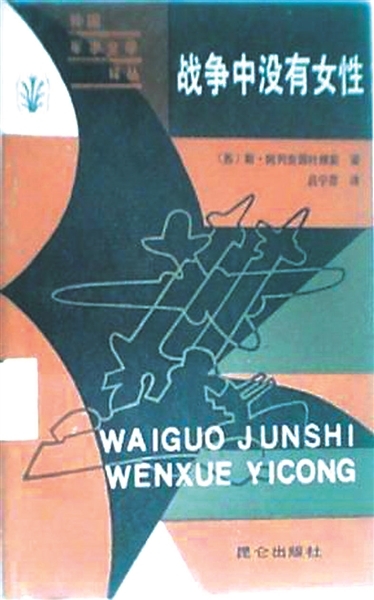 |
活在每个世纪初期的人,多半要比一个世纪的晚期更疲沓一些,更玩世不恭一些,时间视野很开阔,又没有什么动力驱使他们去紧着完成什么事。不过,有一些人无法有意识地放轻松,待在生活的表层:所有孩子,很多老人,生过大病的人,经历过巨大变故和苦难的人。
2 岁的时候,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差点饿死。在如今属于乌克兰的一个叫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的小地方,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只能出去行乞,一日来到了一所 修道院。门打不开,两个同样饥肠辘辘的同伴把他扛起,让他翻墙而入,找到了里面的修女。修女让他赶紧走,这里没有他待的地方,又叮嘱了一句:你老婆可以来 这里干两个月的活,我们每天会给你半升羊奶。
就靠每天喝羊奶,斯维拉娜活了下来。这段苦难的身世并没有旁证,斯维拉娜明白,说多了 会引人反感。在为了揭露被官方隐瞒的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真相而八方走访的过程中,她已经遇到过很多人,不愿讲述自己受过的苦,或者怀疑向他 们打听苦难的人,把自己的故事拿去赚钱。这些经历让她怵惕不安。非虚构写作要顶着道德风险,即便是她本人回忆自己的童年,看上去也是经过仔细权衡裁剪过 的,要排除听众对“贩卖苦难”的怀疑就必须准确、节制,控制音量,细节太突出就会失真。真实的证词是宝贵的,价值不可估量,又很脆弱,常常无法验证。一位 日本导演读了斯维拉娜的书,提议跟她一道去她的家乡,把那所修道院找出来。他们去了,常年遭禁并流亡的斯维拉娜难得回一次家,但修道院已经湮灭不见,原址 只剩一片坟场。
你是不是愿意信任一个专一地书写同一个国家的受难者,并且揭该国政治黑幕的人?这个国家虽然瓦解了,但它已塑造成的 人民气质是不会有大变化的,他们熟悉贫穷和暴戾,情绪化,容易拜倒在强人的脚下。讲真,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替斯维拉娜的诚实背书。如果你先入为主地认 为她是个反苏派,那么大可以把她的书当作别有用心的出版物,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六年前发给罗马尼亚裔异见人士赫塔·米勒一样,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她 的写作要求你的信任,必须翻开《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之声》,让书里的事实淹没自己。它们是有力量的,力量来自让你皱眉的事实。在事实和虚构之间, 斯维兰娜总是习惯迁就前者。她的书里一点点明显的夸大都没有(刚好跟三年前那位中国得奖者的反面),譬若她的奶奶和乡邻说话时的伤感的语调,对她是永生难 灭的心灵重荷,逼使她无力施加增减。她不得不在自己的记述中,寻求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语言的透明:看到文字,就了解事实的全部,毫厘不多,毫厘不少。
比如《锌皮娃娃兵》开头的一段:
城 里,一个车站的候车室,一名军官带着一个半空的提箱。他身边坐了一个瘦瘦的男孩,用一个小叉子在一棵橡胶树的泥土里挖着。两个乡下女人坐在他们身边,开口 打招呼:“你们是谁?”军官说,他送一个小兵回家:“他疯了。”“疯了?”“疯了,从喀布尔回来,他一路上手里拿着什么就挖,铲子,叉子,小棍,自来水 笔。”男孩抬头看了一眼,他的两个瞳孔已经放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球。
这是她引用的一个老兵的话:
“回到 家,我们看到什么?我问一个朋友要五块钱,他不肯,因为他老婆不让。这叫什么朋友?我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得太多了……在这儿,生活就是一个大泥潭,所有人都 只关心他自己的豪宅、汽车,在哪儿能买到一点熏香肠……要不是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十万人呐,他们就把我们挡门外啦……在那边我们都恨死了敌人。但是这里我 得找个人来恨,非得这样我才能重新交到朋友。但是,恨谁呢?”
读两段文字,对阿富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心里就有数了。科波拉根据 越战拍摄的《现代启示录》,也正是阿战的真实写照,在那里,虐待是被正当化的,人跟人的关系不是互为同志就是互相虐待。一旦闻到了血腥味,好端端的人都失 去了理智,唯有以暴对暴,连非战斗人员也不宽恕了。有个士兵对斯维拉娜说:“我们坚信,我们在那里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己的生活。”
似 乎无需刻意地揭露,读者就能看清战争的本质。强力的统治者软硬兼施,把年轻人推进一台他们从未见过的超级绞肉机。铁幕两边,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搅进了一场不 该发生的战争,士兵们的感受也很相似:出发前,上级可是激励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拯救”当地人,等到了那里,他们才惊愕地注意到,当地人一点都没有 欢迎的意思。在亚洲的僻壤穷乡,他们都遇到了手段残忍的游击队,不知道如何利用浑身的顶级武装,“以胜利的方式”应对冷枪冷刀、骇人的咆哮。
然 而与共同之处相比,两场战争的差异更大,最明显的一点,不论官方还是民间,苏联并未救济它所犯下的致命过错。反越战力量在上世纪60、70年代之交奋起, 挽救了美国,美国的主流舆论,面对那些幻灭的老兵都要收敛言辞,任何人,没有参加过越战却想批评美国挑起的这场战争的,都得斟酌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在苏 联,大面积的情绪发泄始终没有发生,更不用说反思,哪怕在战争结束后,伏尸无数的南线战场被阿富汗人迅速攻破,战果付之东流,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帝国苏联人 也无暇处理自己的错误和丧失。
这个结果,斯维拉娜认定是官方刻意造成的。受害者无法接受自己当了炮灰的事实,于是就自欺。于是斯维 拉娜说出她的著名论断:“我们的人民无法为自己负责。这就是苏联人,监狱和幼稚园的混合体。”——他们身陷一个无墙的缧绁,而其头脑和心智的成熟度还不足 以承受系狱之苦。
Too simple to be imprisoned。鲁迅笔下的阿Q不也是这样么?心智于幼年就被扼杀而无 法发育,到日后,脖子上架了屠刀还在琢磨画圈。而活下来的受害者,即使熬到作恶的人已化为尘土,也依然是受害者,甚至适应了这个身份,觉得就这样度日也 罢。斯维拉娜写过,很多永久受创的人,后来宁愿选择自杀,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有一天会得知长辈们过去都干了或者经历了些什么。独裁政权 把责任都转嫁到了恶行之微末的执行者身上,对受害者,则训导他们自行消化苦果。
斯维拉娜是有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总认为披露了真 相,人们就该觉醒,实际上却很难。人们有各种私下的考虑。很多人似乎能忍得了统治者的残害,却不能忍受作家以文字的形式描写这种残害,斯维拉娜的沮丧可想 而知,她能做的都做了,以书写个人记忆来对抗集体性遗忘,用苦难去灼烧相对安逸的人,但面对人们心智上的巨大黑洞,她无能为力。此外还有另一种沮丧。《锌 皮娃娃兵》里写到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她刚刚入睡,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一个男人也不做自我介绍,开口就骂:“听好了,你写的垃圾我都看了,你要是还敢发表 一个字……”
她忙问:“你是谁?”“我是你写到的人里的一个。上帝啊,我恨和平分子!你有没有穿着全套行军服爬上过一座山?你有没有在70度的气温下坐进运兵车里过?你没有。滚你妈的!这是我们的事,跟你有屁关系!”
她又问了一遍你是谁。
“住嘴!我最好的朋友,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我是在一次遇袭之后把他装在塞璐玢袋子里带回来的。他的皮给剥了,脑袋被砍了,胳膊,腿,全断下来了……他能写,但是你不能。真相都在那个塞璐玢袋子里。你给我滚!”
她 无暇舔舐自己的英勇,就要在一个个困境里挣扎。就在她获奖的第三天,南京大屠杀“申遗”成功,立刻想到那位自杀的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阿富汗战 争,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一个个事件刷新人类苦难想象之底线,而冲进其间去吮吸黑暗的奶汁的人,有几个不会想到去死呢。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人普里莫·莱维 曾说,至亲好友化成了灰烬,而自己还活着,单单想到这一点就够一个人自杀了:我的生命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我活下来,就能忍心一直让他一个人留在那边?听 过太多惨无人道的故事,张纯如终于感到无力带着它们活下去。谁知道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是不是也几番动过念头。
她比张纯 如坚强,也许是因为她执着地把“幻想”都视为“希望”。倘然说文字是有改变现实的力量的,这力量也只能来自你的相信,正如读者要相信斯维拉娜不是一个职业 反苏分子,才能从她的作品中汲取到营养一样。斯维拉娜是信的。她总在告诉人们,后苏联时代的白俄罗斯人依旧是无望的一群羊,不敢主张自己的民族身份,不敢 挑战稳固的统治者,否则就会被大学或单位开除,伶仃亡命他乡……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就暗暗相信事情在发生改变。
必须等待。如鲁迅说 的,烧大量的木材,只能出来一小块炭,心智的进步可能落后于最悲观的人的预想,何况是一个在抽屉里培植的、先天不足的心智。俄罗斯不乏文学巨人,想想陀思 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等光辉的姓名,到了斯维拉娜这里,拿她的非虚构同前辈们巨笔如椽的小说相比,简直太寒酸了。为了给她腾 地方,诺贝尔奖不得不扩容文学的范畴,宣称她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她写的绝算不上最好的文学,但可能是最有效用的文学;她的忧虑,她的勇气,有必 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知识分子如果更有力一点,国家会好许多——近几年斯维拉娜获奖的场合多了,就常常这么表示。但她并不讳言,自己的耐心也在一点一滴地散失。2011年回到白俄罗斯,她发现文化精英正大批流失,有点钱的都出去了,剩下的人昏茫如往日,容易动摇,容易被收买。
黑暗成就了她,像修道院的羊乳一样哺养她到现在,可它再有营养,也终究是黑暗。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