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年龄不是问题(李琭璐)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6月11日09:22 来源:光明日报 李琭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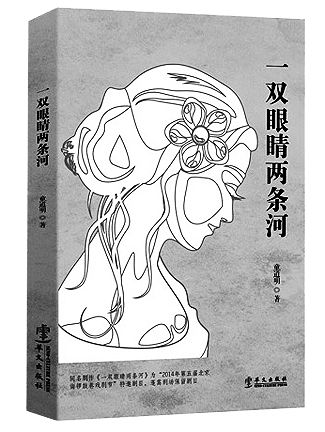
 CFP
CFP 契诃夫家乡为其树立的雕像 CFP
契诃夫家乡为其树立的雕像 CFP这是童道明又一次站在话剧舞台上谢幕。
舞台、灯光、音乐、鲜花,掌声缭绕。有人微笑,有人落泪,有人沉默不语。
2015年1月29日,恰逢契诃夫诞生155周年。一场题为《爱恋·契诃夫》的话剧在国家话剧院上演。镁光灯下,满头白发的童道明登上层层台阶走到舞台中央,深深地向观众鞠躬致谢,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的伊春德轻轻地扶着他。这样的幻妙时刻,他已在梦境里多次邂逅。
在常人眼中,他是一位老人,如此而已;在学生们眼中,他是一位学者,最为知名的头衔是中国著名戏剧评论家;但在戏剧评论家们眼中,他还是一位编剧,60岁开始动笔写戏剧,10年后获得了编剧金狮奖。常常有人追问他的年纪,他粲然一笑:“年龄不是问题。”
年岁增长,随着同时代的文化名人纷纷成就“大师”风采,童道明却渐渐淡出公众视野。直到最近这些年,这个名字才被我们重温,不仅关乎戏剧,还关乎人生。
北京。深冬。冷空气划过脸颊像刀割。那天,距离2015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电梯一开门,童道明迎过来,转身跺了跺脚,漆黑的楼道倏地亮了。
这是位于潘家园的一处老房子,四层,采光不算太好,即使是白天也要开灯。家具是旧的,并不成套,积满岁月风尘。沙发是拼凑的,镜子是老式的,水杯是普通玻璃杯,贴着或明或暗的印花。屋子正中央有张书桌,擦得锃亮,显然还在“服役”。剩下的便是书了。
正如大海上翱翔的海鸥,童道明文弱,但思维敏捷有力。于是你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一切有为法”的世间,总有一些奇迹可以相信,更有一些光亮值得我们细心品味。
热情寒暄,童道明捧着一杯温水坐下。他以为自己的表慢了,连连道歉。终于明白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提前到来,他立刻释然大笑。
他显然是明朗开阔的,不拘小节。然而,亦有距离。思考时神情严峻,眼神锐利,看得到他内心的岛屿,浪涛拍崖,决绝独立。
“年龄大了,真好。”童道明被岁月感动。
——引子
春为发生
起先,是拉克申老师,牵着他的手,走向了契诃夫。
那是1959年,童道明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读三年级,写了篇学年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
论文讲评会开过后,拉克申老师把他留住,说:“童,我给你的论文打‘优秀’,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学生听了老师的话,从而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他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方向——研究契诃夫和戏剧。童道明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从原剧到演出本,从小说到信札,他写下许多与契诃夫有关的著述和文章,然后,他把契诃夫写进自己的戏里,看着他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恰逢冬天,北京盛产的大风,迅疾并且暴烈。这是童道明喜欢的“日子”。日子没有大事,雷打不动的晨起写作、读书看报。这段日子,童道明一头扎进了翻译契诃夫妻子克尼碧尔的回忆录中,为写作《契诃夫与克尼碧尔》做准备。本子是大红色的,封底写着《带阁楼的房子》,随手翻开,是1月16日的日记:如果我不研究、不走近、不喜爱契诃夫,不热爱他的戏剧,大概也不会在六七十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动手写剧本。
日期之后,抄一句中文诗,那是一句近来正在读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并顺手翻译出来,然后,是各种杂感、随想、手机短信记录、提前备好的讲稿等等。
作家高尔基在《论契诃夫》中写道:“我觉得,每一个来到安东·契诃夫身边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是他自己……”
童道明早就读过高尔基的这段话,也相信会是这样,特别是在他结识了于是之老师之后。2014年1月18日,《作家文摘》在首都图书馆召开于是之逝世一周年追思会,童道明在发言中几乎重复了高尔基的这一段话,只是把“安东·契诃夫”改成了“于是之老师”。
于是之帮助他更好地认识了契诃夫。
童道明记不清与于是之有过多少次倾心交谈了。有一次最为刻骨铭心,谈话在紫竹院公园进行,于是之与他说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后来,童道明写了篇谈论“知识分子与戏剧”的文章发在《剧本》月刊上,而在写这篇文章时,童道明的戏剧处女座《我是海鸥》已经成形,以此弥补于是之的遗憾。“尽管于老病了,不知道了。”
《我是海鸥》是1996年写的。这一年恰好是契诃夫名剧《海鸥》问世100周年。向契诃夫致敬,童道明想在他的第一个剧本里,把自己对戏剧精神价值的认识表达出来。
“朋友们!我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是因为这个美丽的《海鸥》,我们在生活中相遇了,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现在都在剧场里,剧场是什么?剧场是一群有共同的精神追求的人团聚的地方,在艺术之神的眷顾下,他们在这里互相交流,互相取暖……”
童道明喜欢爱伦堡的《重读契诃夫》,这本书的结尾一句是:“谢谢你,安东·巴甫洛维奇。”多么简单的一句话,但饱含着多少深情。童道明一直想效仿爱伦堡,在公开的文字里对契诃夫说几句温情的话。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他写了第一篇关于契诃夫的散文《惜别樱桃园》,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
“谢谢契诃夫。他的《樱桃园》同时给予我们心灵的震动与慰藉,他让我们知道,哪怕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为什么站在新世纪门槛前的我们,心中会有这种甜蜜与苦涩同在的复杂感受,他启发我们这些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我是海鸥》2010年在北京蓬蒿剧场首演。这天恰好是契诃夫诞生150周年。有朋友看完戏感慨:“童先生真年轻!”
在写作《我是海鸥》时,童道明把契诃夫的一句话当座右铭写在日记本扉页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的脉搏在我身上跳动得愈加有力。”
那些年,冯至、季羡林等大学者相继去世。童道明很是感慨,他第一部演出的戏——《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的戏剧主人公就是冯至和季羡林。
也许是因为童道明在于是之身上发现了契诃夫,便对这位老艺术家特别敬重。在过去的20年间,每逢大年初三下午两点,童道明会准时去给于是之拜年,直到于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夏为长赢
在聚光灯照耀之前,童道明已然受到过眷顾。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当时,在大学礼堂里“既不靠前也不靠后”的座位上,坐着一位20岁的青年,聆听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一独特的青春祝福。他就是童道明。
时光流逝,当日的青年垂垂老矣,不过很多人都说他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个“苍老的年轻人”。如果检索童道明的作品,有一点大概会令人惊讶,他20世纪80年代做研究、写评论,90年代开始写散文,2005年起全力投入戏剧创作,2012年又开始尝试写诗……人的原创能力通常在青年、中年时最为蓬勃,而他是“衰年变法”,近乎逆生长。
与童道明合作的一位年轻导演说:“童老师的语言干净到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尴尬,这正是其珍贵之处。”是的,如果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真挚而柔软的调子,那种“透着亮光”的忧伤,心中就会泛起悠长的涟漪。
2014年,童道明出版了《一双眼睛两条河》《契诃夫与米齐诺娃》《论契诃夫》等9本书。2015年的第一本书《契诃夫书信选》的书稿也已出版,“笔记本上有记录。我从2013年8月2日开始翻译、注释和解读,11月2日完成,每天做这件事,入迷了。”童道明说,“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需要契诃夫,契诃夫也需要我——因为他已经不在了,而不断有人来找我谈契诃夫……”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童道明不止一次提起留学时的一个故事。那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消息传到大学校园,已是黄昏时分,年轻的学生手挽着手,齐声高喊:“给我月亮!给我月亮!”
这么多年过去了,童道明的笑声,不由得让人想起那轮年轻的、醉人的、浪漫的月亮。
2013年8月8日,红丹丹文化中心出品的盲人朗读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在北京先锋剧场演出,童道明去看了,演完之后还上了台,合了影。他站在中央,旁边是一位盲人演员和两位志愿者。于是他突然想到1953年8月的一天,复南姨妈给他和母亲在北海公园拍过一张照。他把这两张相隔整整60年的照片并排放到一起,嘴里喃喃说出了5个字:道明一甲子。
1953年,童道明16岁,翩翩少年;2013年,他76岁,垂垂老矣。
1953年,童道明上高二。那时的高中还没有实行文理分班,他最爱听的课,是特级语文教师李慕白教的作文课。2013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五中做讲座,说感谢母校教会了他怎样写作文,这让他终身受益,因为此后他一辈子都在写。
留苏时,童道明年纪小,常想家。2001年,童道明出了本随笔集《俄罗斯回声》,开头的一篇文章《静夜思》里写了这样的回忆:
“年轻的时候,住在莫斯科大学的高楼里,也常因为见到月光而思念故乡。特别是在他人都已跳舞去,此地空余宿舍楼的节日之夜,在华尔兹舞的撩人的乐曲声中,对着月亮想家,能想得落泪。”
在北京的母亲也常想他,有一年中秋时节,她给童道明和在安徽工作的哥哥分别写了封信,信里附有一首她写的诗,其中“一家分三处,两地都思娘”这句,让童道明感动与感伤了好一阵。
1960年冬,童道明因病辍学归国。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每月给他25元生活费,嘱咐他自己寻找工作单位。1962年,中国剧坛出现布莱希特热,经过留苏老同学郭家申的推荐,他为《文汇报》写了篇《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这篇文章成为一块帮他打开工作之门的敲门砖。那年童道明25岁。
十年“文革”,不堪回首。童道明痛苦地回忆:在河南干校时,曾利用去信阳看病的机会,翻译了一个俄罗斯剧本《工厂姑娘》。后来,他写了篇散文《一份译稿的诞生》,描述了那时的情境与心境:
“我一边翻译着,一边陶醉着。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6年中,我第一次动笔翻译,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躺在床上一时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了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是更难的。”
“文革”结束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童道明征稿,他把这份特殊环境下完成的译稿交给了他们,中译本《工厂姑娘》在1981年出版。这是童道明出版的第一本书。
为了说明在河南干校时的心境,有一个情景也值得一提:童道明常常独自一人在田野上痴痴地吟诵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句诗:“时光在流逝,那是最好的时光。”
1972年从干校回京,为了追回白白流逝的最好时光,童道明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他用了整整5年时间到那里看书,每日去半天,读的全是与戏剧或契诃夫相关的书。“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那5年的苦读,就不会有5年之后井喷式的写作。”
童道明认为自己的人生转折点是1972年。
他珍藏着两样1972年留下的纪念物。一件是《工厂姑娘》最后一幕的译稿。上边注明,他是1972年5月16日下午3时坐在河南信阳一家冷饮店里开始翻译的。最后的文字记录是:“72年5月17日下午3点44分于信阳第三招待所第67号房间译完。”另一件是他1972年10月19日领到的北京图书馆阅览证。
1977年,童道明的生命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他得了一个来势汹汹的怪病,协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都匆匆地赶来医院探望,但童道明那时脑子非常清醒,他在病床上暗下决心,如果闯过鬼门关,将一门心思写文章,把脑子里的全部积累统统形诸文字发表出去。
1978年养病一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童道明人生的一个新节点——1979年,那年他42岁。
从1979年在《外国戏剧》上发表2万余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起,童道明的一篇又一篇文章鱼贯般地出笼,到1983年出版了30余万字的论文集《他山集》,童道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一位相当活跃的戏剧评论人。
秋为收成
2004年,迎来了一个更大的纪念日——契诃夫逝世100周年。
这一年,北京破天荒地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口号的国际戏剧节。戏剧节的开幕戏是王晓鹰执导的《普拉东诺夫》,闭幕戏是林兆华执导的《樱桃园》,两个演出都用了童道明的译本。
也是在难忘的2004年,童道明和王晓鹰到北京图书馆去做了一次讲座。主持人说:“50年前,我们请汝龙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小说,今天我们请童道明先生和王晓鹰先生在这里讲契诃夫的戏剧。”童道明听了,心里真有点感动。
让童道明感动的事还有很多。
譬如采访时,我念出了他在2014年年底参加奥林匹克戏剧节时的演讲稿,他笑得眯起了眼。
他也记得北师大读博士的米慧,毕业后她回东北教书。2013年10月18日那天,童道明意外接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童老师,我正在‘全国高校俄语大赛开幕式’现场,正在致辞的是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他讲到了您,大段引用您的《阅读俄罗斯》和《道明随笔》。我感到好亲切啊!”
最令人难忘的演出,发生在1992年7月16日。这一天,于是之等人艺第一代演员作《茶馆》告别演出。有感于这场演出催人泪下的悲壮谢幕,童道明写了篇题为《这可能是绝唱》的文章,由此他也开始了散文创作。1996年,童道明的第一本散文集《惜别樱桃园》问世,这一年他59岁。
这本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责编让童道明在书勒上写一句最想说的话,他写了“喜欢联想与善良”这7个字。“写散文需要心脑并用。脑子应该成为一个由敏锐感应力的‘联想集团’,而心呢?应该是一颗善良的心。”
2009年,童道明的剧本首次刊登在了杂志上,也第一次登上了舞台。他终于走出戏剧的书斋进入了戏剧的现场。那一年,他72岁。
但这个剧本并不是童道明的戏剧处女作《我是海鸥》,而是他2005年动笔写的《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刊登这个剧本的杂志是《剧本》月刊,那时主持日常编务的是黎纪德先生,他幽默地称童道明是“编剧新秀”。
后来,王育生写了篇《为“破门而出”叫好!》的文章发在《剧本》上,为童道明打气。“在我作为编剧走向剧坛的道路上,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而王育生也对童道明赞赏有加:童道明有一定积累,他用自己的作品发声,他的戏剧是真正的“人文戏剧”,值得关注和研究。
在一次两人对话中,王育生提到“文艺作品应该有愤怒”,童道明却回应:“让别人去愤怒吧。”王育生戏言:“这着实是一位婉约派剧作家。”
《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是两出没有笑声的戏。他的学生苏玲说,其实童老师是个爱幽默的人,1994年外文所建所30周年的庆典上,主持人点名让童道明上台说个幽默。那当然得说个不伤大雅的,于是他说了个有关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幽默。几个月后,华东师范大学倪蕊琴教授写信告诉童道明,她在课堂上把这则幽默说给了学生听。
《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演出之后,童道明一鼓作气又写了3个剧本——《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蓦然回首》。
观众带给他的信息,则常有知音天降的意外——
有一次在蓬蒿剧场演完《我是海鸥》后,一位女士走到童道明的跟前说:“我是从东京来的,我翻译了你的《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另一位名叫晓岚的观众,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生,她看完《歌声从哪里来》的那天深夜,给童道明发来七八百字的短信,说她的观剧体会,第二天她把包括她母亲在内的16位亲朋好友带到蓬蒿剧场看戏。
任何一个编剧都会为拥有这样杰出的观众而感到幸福。2009年之后到剧场看戏,与童道明打招呼的陌生人多了起来。
有一次到国家话剧院看戏,在剧场门口,见一位女士微笑着走过去,说“童老师,您好!”童道明问:“您是?”女士微笑着说:“您不认得我的,您不需要认得我。”然后,微笑着走开了。“我想,如果我戏写得越多,一定会有更多的陌生人带着微笑向我问好。也就是说,你做得越多,你就越会感到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温暖。”童道明目送着她走进剧场,心里生出了这样的感慨。
冬为安宁
童道明写的第一首诗是《我梦见》。
我梦见/树上那个落下来/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被乔布斯咬了一口。
诗歌一直是童道明的一个神秘憧憬。母亲爱好诗歌,看妈妈在灯下写诗,是他童年最温馨的回忆。在写了几个剧本之后,他开始真正有了写诗的冲动。这是因为在写剧本的过程中,他慢慢感悟到戏剧与诗挨得很近。就如同他常说的,契诃夫的戏剧比契诃夫的小说更接近于诗。
1955年,童道明高中毕业,因为有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用幼稚的文字写起了幼稚的诗。他所上的高中常与一所女中学校联谊,有一次攀登了北京的最高峰——鹫峰,回到市里又组织了联欢晚会。晚会上一位女生站起来当众朗读了童道明的一首诗:“看见你了,庄丽的鹫峰/你像武士一样/耸立在群山之中/……”
童道明由此想到了1949年,想到在故乡小学毕业时的一幕:我们在教室里最后一次齐声唱一支名叫《我家在江南》的歌。它的最后一句是:“别你时,我们都还青青年少,再见时,你又将是何等模样?”我离开家乡后,特别是到了异国他乡后,常常吟唱与玩味这句唱词,它曾勾起过无尽的乡愁。从课堂出来,他跨出校门在前面走,听到几位老师在背后议论他,有一位老师说:“不管童道明将来走到哪里,都不会给我们丢脸的。”
60多年过去了,童道明一直没有忘记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其实并不是说给他听的话。
想起2014年是契诃夫逝世110周年,童道明从2013年8月2日起,就开始翻译契诃夫书信,每天都要译一封信,或两封信,10月3日那天,童道明翻译出了契诃夫1898年11月13日从雅尔塔写给妹妹玛利雅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告诉妈妈,不管狗和茶饮怎么闹腾,夏天过后还会有冬天,青春过后还会有衰老,幸福后边跟着不幸,或是相反;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健康和欢乐,总有什么不幸的事在等着他,他不可能逃避死亡,尽管曾经有过马其顿王朝的亚历山大大帝——应该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对一切所发生的都看成不可避免的,不管这是多么令人伤心。需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
翻译到这里,童道明掷笔沉思,好像觉得这是契诃夫在对他隔空喊话,在指教他用更理性、更达观、更从容、更谦卑的心态来对待人生,服从命运。“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
童道明写剧本有两个领路人,一个是契诃夫,一个是曹禺。他牢记契诃夫戏剧的基本经验:“戏剧表现人的精神生活。”曹禺在《雷雨》的序言里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的争执。”童道明也把这句话牢记在心。
最要紧的当然还是写戏。2014年春节,童道明投入到《契诃夫和米奇诺娃》的写作中,这是他创作的第八个剧本,也是第二个有契诃夫登场的剧本。剧本的初稿完成于2014年2月7日,写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他长吁了一口气。心想,他的“一年写一个剧本”的计划没有落空。
于是,童道明乐观地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天,他的读者和观众将有机会与这个剧本相遇,能从剧本里读到,或从舞台上听到契诃夫的一句台词:“我刚刚写完一篇小说,我就把小说里的一段话念出来,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而这个愿望,在2015年伊始实现了。
耄耋之年的童道明常常要与时间赛跑。母亲和哥哥不幸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用超强的脑力劳动来抗拒衰老,不知是不是能侥幸地躲过这一关。”他的眼睛里有悲悯,然而毋宁说是自怜,因为生而为人。
因为采访,与童道明约了数次见面。而促膝长谈,只有两次。但印象最深的碰面,却是在首都剧场。那晚,作为《万尼亚舅舅》的译者之一,童道明早早地站在剧院门口静候着那些或熟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他的身旁,是契诃夫的大幅宣传图。有那么一秒钟,他深情地望着画中的契诃夫,嘴角上扬,眼神温存且饱含敬意,像是穿越了百年的一次隔空对话——
他说:“作家蒲宁在回忆录里说您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人。我不同意他这个看法。我认为您一生至少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您的恋人米奇诺娃,一个是您的妻子克尼碧尔。”
他答:“两个就不少了,为什么说至少呢?”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