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与他的《南方》(晓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25日11:10 来源:深圳晚报 晓依 当小说生成,隐匿在作品之后的小说家,早已变得面目模糊。兰米·昆德拉说,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想必这话,对艾伟管用。
当小说生成,隐匿在作品之后的小说家,早已变得面目模糊。兰米·昆德拉说,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想必这话,对艾伟管用。 《南方》 艾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南方》 艾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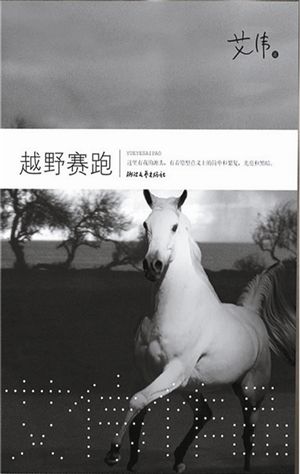

特别庆幸,艾伟把小说的名称改为《南方》,这一改,气势顿然磅礴起来。正是这种模糊的定位,为读者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事情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列车便由此呼啸而来。“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这是《南方》的开头。灵光一现的这句话,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支点,像飞出去的鸟儿,有巢可回;射出的箭,落到了准确的靶心。很多人在这句话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历史的包袱,积重的过往,不是一句“俱往矣”可以回避或隐匿的。
2009年,艾伟写完《风和日丽》,他想歇一歇,长篇太累了。这种想法与阿来一致,阿来认为“写作相当于这一湖水决堤而出,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下一本书,得修好堤坝,等水再次慢慢盈满,再次破堤。一部长篇的写作,特别如此。”经过半年的休整,艾伟想消遣地划拉一个过渡性作品,此时,邻居家一个傻瓜的故事浮现于他眼前。“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于是大哭一场。”艾伟把傻瓜写进了小说,这便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傻子好人杜天宝。天宝在小说中的确是艾伟的偏爱,他非正常人,却心地善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只有他,还不行。艾伟脑子里一片黑暗。“必须从头来过。”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天之前已经死了。”当艾伟写下这句话时,他找到泄洪的河口——罗忆苦成了整部小说的中心。
杜天宝从主角的位置上开始隐去,代之而来的是,杜天宝的三轮车上坐着一对双胞胎美女罗忆苦罗思甜……故事大幕由此拉开。艾伟开始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
马尔克斯的“百年”足以孤独艾伟一生
刚开始,艾伟不过想雕刻一个短篇或中篇,谁知这一触碰,便是五年,他不知不觉又埋头创作了一个长篇;正如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的他,原本只想搞搞建筑,当个艺术家,某瞬间一不小心拿起了笔,人生从此不被自己主宰。
说不小心,当然是笑谈。如果不是大学时期饥饿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启了干涸的心灵,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让青年艾伟从中看到了小说的自由以及创造的巨大可能性,他也不至于傻到弃艺从文。毛尖把《刀锋》的毛姆当做她“叔叔”,好吧,我们且把马尔克斯当成艾伟的“舅舅”,毕竟,老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百年”足以孤独了艾伟的一生。1996年艾伟开始发表小说,《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盛夏》等长篇以迅猛的速度产出,他的笔下,各种罗忆苦似的人物无以复加地流淌着,比如《风和日丽》中的杨小翼,她坚强、忍耐、勇敢、干干净净……艾伟解释,到了一定年纪,女性的美来源于内心,内心的安宁就会渗透到面容的安详,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在写女性方面,艾伟无私地暴露了自己的性别特征——男性作家,对女性主角无缘由袒护及偏爱。
正当艾伟没日没夜沉浸于他的七天破案小说中,时间忽悠过去了。这中间他也抬起头来,却看到了余华的《第七天》。天呵,山中一日,世上千年。要知道,艾同学2010年开始着笔时,小说便命名为《第七日》——一起凶杀案,从第一日写到第七日,第七日谜底揭晓。而如今?他着实紧张了一下,所幸发现内容完全不同。
改名。“在中国,南方的历史确实很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这是他对最后小说名称《南方》的解释。
不得不说,理由很笨,名称很好。
为写作,艾伟曾到过监狱采访,听各种各样杀人犯的故事。一位朋友无意中讲了一个发生在宁海的真实故事。一个父亲,孩子患了种奇怪的病,到处求医,因被骗而杀了人。这成了《南方》中须南国携病孩求医途中被罗忆苦骗财的故事,有了这一出,铺垫了罗忆苦最后被害的结果。
是的,《南方》中,罗忆苦一开始就死了,她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何致死?是谁杀死了她?她的死又与谁有关?……一系列问号贯穿小说全文。艾伟以这样一种牵肠挂肚的方式,自鸣得意地引领着剧情有节有制地向前发展,然后,告诉你——罗忆苦被杀的充分的理由。所有人都跟着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艾伟作品
好的小说总比它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
实际上这是一篇倒序方式的线状小说,它以一具夺人眼球的美丽女尸开始,在七天内展开了破案,叙事结构又从头开始,按时间的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状延展,由始而终,由头至尾,由开端到结局,一步步向前发展,时而穿插倒叙、插叙、补叙,作者设置了三个人称:你、我、他。我——美女逝者罗忆苦,你——政委肖长春,他——杜天宝、须南国、肖俊杰、夏小恽、罗思甜、杨美丽、赵三手、夏泽宗……主副线交叉共进,故事就跨越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饥荒、“文革”;七十年代“拨乱反正”、招工、进城;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改革开放;直至九十年代城镇快速发展……由几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折射中国大地三十年的社会变迁。
艾伟在小说中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写作方式,以心理分析、独白旁白、感官印象以至幻觉、梦境等表现手法展开叙述。罗忆苦死了,却以一个灵魂之口说话:“我一天之前已经死了。我从西门街杜天宝家里出来,那个人就一直跟着我。我知道他是谁。他一直在找我……”活人肖长春与死人夏泽宗的精神偶遇,“你看到夏泽宗在那头等着你。近一个多月来,每次你来医院看望周兰,他都会在那儿等,极有耐心……他向你投来的目光就像一个债主,不,简直像个索魂鬼。”
《南方》似是典型的象征结构作品,作者在赋予小说象征涵义时,仍然致力于形象完整性和生动性的描写。这些影子我们在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都能找到相似的痕迹。只是艾伟增强了故事行进过程中的传奇性、戏剧性和紧凑性,以营构因果相扣的严密精致的情节,使作品更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
画面描绘是《南方》一大特点,“他们寻遍沿江三百三十三个村庄,一无所获。到了晚上,一望无际的大海出现在眼前。他们到了大陆的尽头。难道那小孩漂到大海里去了吗?”“那是个美丽的村庄,靠江有一座小山,小山古木参天,山顶上有一块巨石,状似拇指。村庄就在山脚下,小河环流,几百户人家的房舍都掩映在树丛中。四周阒然无声,好像他们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朱光潜曾评论废名的小说《桥》:“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南方》翻开,一节又是一节,类似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品,组画和群像交替,使得画面之间的关系有了多义性,叙述的整体意向有了不确定性,正因此,情节推动中实现了意义的衔接。
第七天,凶杀案破了,各个角色都给了合理的归位,各种线头有了起承转合的呼应,前一秒闪现的,后一秒必定落地,没有多余的枝节,或是一去不复返的镜头或道具,作者俨然成了精算师,时间以分秒争,空间以厘米计。大家不约而同吁了一口气。可谓“圆满”,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命的感悟,形成了所谓圆形思维。终极,回到原点。
至此,我们且把《南方》当做一部情节小说,一部细节小说,或是一部隐喻小说。“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飞翔和写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在《南方》写作中,我尽可能地淡化历史——当然它依旧在,我更多地让小说按其自身的时间而生长。在写作中,我不但在时光里看清小说人物的表情,我也看清了时间温情而残酷的面容。”
当小说生成,隐匿在作品之后的小说家,早已变得面目模糊。兰米·昆德拉对此有精彩的阐述,他以托尔斯泰做例子,“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时,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她的思想道德。我更愿意说,他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仰,而是另一个声音。他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昆德拉的说法,印证了福楼拜的话,福老早期就说过“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
想必这话,对艾伟管用。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