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或者不说(向以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11日10:28 来源:羊城晚报 向以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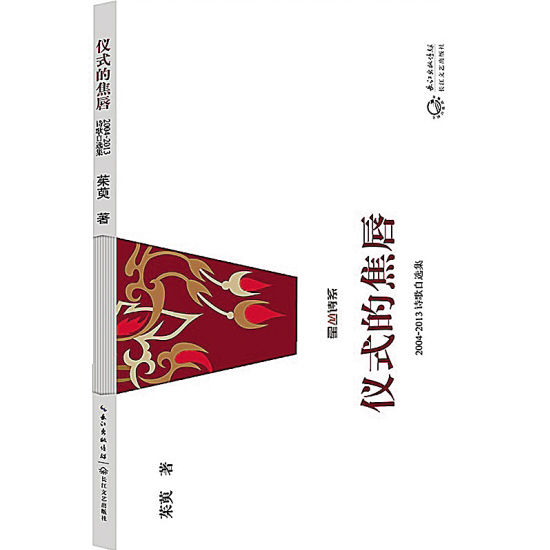
试图解读茱萸是徒劳的。虽然茱萸的《仪式的焦唇》,99首诗作,现在就翻开在我的案几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抓住茱萸和他的诗歌。实际上,就像茱萸的名字一样,这种神秘又充满感伤情调的植物,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挚热的怀念和恒久的缺席之间,茱萸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构的。
这儿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弦外之音:说,或者不说。于茱萸而言,这正是一个问题,仿佛哈姆雷特一般: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诗歌之痛,也正在于说与不说。有时候,不说比说,或更接近于诗的本质。瞽者说:一个神,一生只应该说一句话,而这句话则是完整的。它发出的那个声音不能低于宇宙、或者少于宇宙的总和。这个声音的影子或者幻影,令所有的诗人为之耗尽生命,曲曲折折,千变万化,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辰。
我注意到,茱萸在选录诗作时,曾有一个类似于古人焚稿的行为——删诗——他将二十岁前的旧作几乎全部删除了,最后只留下了余烬中的十首。南宋江湖诗人刘克庄(后村),也曾干过这样的事情:刘克庄三十三岁时,亦即嘉定己卯(公元1219年)时,因政治见解与金陵幕府的李珏发生分歧而被放归,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把之前呕心沥血所创作的数千首诗作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百首诗歌作为纪念,名之曰《南岳旧稿》。这样的焚稿行为,其情形大抵与政治或艺术梦想相关——在熊熊的火焰中,诗人以一种绝决的方式告别过去。黑夜中的火焰,火焰中的稿纸,化着蝴蝶般飞散的诗屑,随风而逝。茱萸的删诗行为,多少与此有些类似吧。艰辛地写作,这是说;残忍地删除,这是不说。
这儿饱含敬畏之心,同时充满绝望的宿命感。茱萸在诗中多次写到嘴唇,我甚至在他删余的幸存者中,也找到了“嘴唇”的魅影:“说出秘密的那部分,谁知道它最先被称为什么”(《词语通道》)。五年之后,茱萸再次写到:“那个早慧者,躲在暗处,贴上死神阴晴不定的嘴唇”(《叶小鸾:汾湖午梦》)。茱萸甚至忍不住要引用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在长诗《阴影的重量》中提到的那张焦灼的嘴唇:“雨在唇间洒落,很久以前,雨就扑向烤焦了阴影的石头。”这个意象或许对于茱萸有着隐秘的启示:仪式的焦唇。茱萸告诉我们:“说出,便等于自完满处打开缺口。”
那不说又如何呢?茱萸在长诗《仪式的焦唇》结尾处写道: “实际上,橘园内的那只逆反的昆虫/最终死于明亮的胁迫和仪式的干渴。/春天的深致处倾倒于时间,它的焦灼/拐弯之后,所有的无意义都将被照亮”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