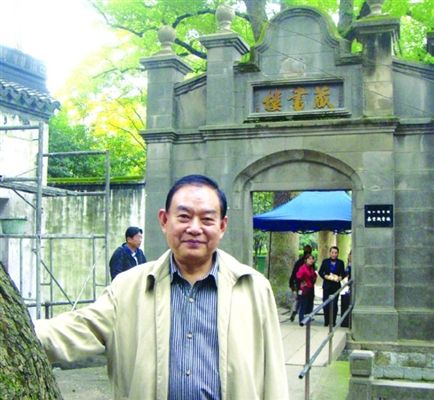 王幅明
王幅明 河南有散文诗的传统。徐玉诺(1894-1958)和于赓虞(1902-1963)均为中国散文诗的早期开拓者。闻一多认为徐玉诺的一些新诗和散文诗属于上等或“超等的作品”。于赓虞是现代派诗风的先驱,他受波德莱尔等西方诗人影响,有“恶魔诗人”的名声,一生遭受厄运。
2008年12月,河南省散文诗学会成立。这是河南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是因为共同热爱而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编辑出版一部彰显河南几代散文诗作家创作业绩的大型选集。经过一年多准备,长达64万字的《河,是时间的故乡———河南散文诗选》 于2010年4月问世,受到广泛好评。学会成立五年来,通过举办活动、创办网站、相互交流,最终以创作成果赢得了同好们的尊敬。从2010年起,学会坚持每年举办年会,至今已举办四届。几年来,其成员出版的散文诗集已近20种,每年都有作品在各地报刊发表,或被收入年度选本。《散文诗世界》、《河南作家》、《星星·散文诗》,曾先后集中刊发河南散文诗群体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有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区域文化个性。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滋养、影响和成就了一代代作家。散文诗作为文学样式之一,有着同样历史基因的遗传,因而在作品里清晰可见遗传的胎记。本文以10位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为例,浅析河南散文诗的地域特色和作家们不同的艺术追求。
乡土是河南文学恒久的主题。从收入《诗经》创作于河南境内的“国风”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徐玉诺、苏金伞等诗人,两千多年间有大量表现乡土的优秀作品传世。当下河南散文诗,乡土仍是其最具特色的表现内容和形式。首先提到一位后起之秀,生于豫东的“80后”诗人马东旭。他的散文诗大多表现乡土。《豫东偏东》的篇名是一个地理词汇:河南东部的东部。那里有他的家乡,亲人,更有给予他不尽灵感、生命力和诗情的精神原乡。这是一篇荡气回肠的佳作,用词之大胆、酣畅,少见。三百字之中连用24个“很美”,令人读之难忘。马东旭的散文诗,除了“豫东”这个区域标识,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几乎无处不在的符号:申家沟。如:“深深的灰色的申家沟,是不是天空———广而黑,掉下的一条水长虫?押解着我,和我溃散的灵魂。押解着马匹、草甸、麦子与神赐的辽阔。令万物停歇赞美。令屋宇向一旁滚动。”(《平原》)“申家沟,我要把你升起。与你身上的青岗寺,棘古城、汤斌墓、闪烁磷光的张迁碑。甚至那些在黑夜里咳嗽的人,诅咒的人,用白皙的手指摸索着绝望的灵魂。它柔软的骨头里充满了荒莽的命运的羽毛。我情愿:丰饶的祷词席卷我———于云之彼端,种下一生的辽阔。”(《我的世界》)它令我们想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徐俊国的“鹅塘村”等作家的文学符号。它们之中应该存在着某种相通的东西,但又各有差异。它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有着神秘的魅力。它既是一个地理性的文学坐标,更是一个精神密码。作为真实的申家沟,它是作者故乡附近的一条水沟,可作为作者故乡的代称;作为虚构的申家沟,它是一个意象,承载了乡土的豫东的历史的民族的宗教的神性的特殊内涵,是诗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马东旭的语言简洁、干练、飘逸,极富诗性和美感。诗人极言家乡之美,又直面生活中的苦与痛,写出了豫东特有的民风民情,也写出了深受儒释道浸润的民族性格,痛并快乐着的看似矛盾的生活本质。2014年是马东旭的而立之年,愿他的申家沟系列收获更多的成果。
李俊功和曼畅都参加过 《散文诗》刊组织的全国散文诗笔会,且都以乡土诗受到赞誉。近些年他们在艺术上都有新的开拓,但不少作品仍与乡土有关。李俊功的组章《未着彩的祈祷书》,以多姿的艺术表现,带给我们温暖的心灵信息。作者笔下的骏马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在骏马的奔驰中昂然抬头。———时间充盈着无限的热度。原野仿佛跟紧它的脚步,迅跑。迅跑。迅跑。谁将埋葬最后的忧伤、苦痛,从贫穷而致的自卑中出脱?鼓翼的信念,乘着一匹奋蹄的骏马迎面而来。”(《一匹骏马迎面而来》)骏马与原野,在同一个时代的节拍上飞奔,寄寓着作者对故乡尽快埋葬贫穷的深情期盼。显然,骏马的意象来自马年,但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本意,具有艺术的久远性。“后闫台村注定是一座世俗村庄,有着涡河水流淌的世俗的爱。迷路的蜜蜂找到花朵的小巢,尥蹶子的黑叫驴听命于柔软的沙土。把冷风般的苦痛压下去,泡桐树不言,带着病痛坚持微笑的乡邻不言。竖立的棉柴篱笆,高举着一炷炷香。”(《热爱是很实际的事情》)作者告诉我们,什么才配叫世间真爱。他视这种最世俗最朴素的爱为他的最高教义。作者用“祈祷书”一词来命名他的散文诗,让人感知他的宗教情怀。“未着彩”,可以理解为不加修饰的本真。曼畅的《小风景》是一组精致典雅的短章。用语极简,有宋词余韵,诗味悠长。均为有乡土背景的风景,但乡土在此仅仅作为背景出现。表面都是描摹自然,欲言却止,留下了大片的艺术空白,细品,物象全是意象,多为耐人玩味的心灵风景。
胡亚才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近年来创作成果颇丰。南湾湖是信阳著名的风景区。常人到此多是看,胡亚才是读。一遍遍地默读之后,发现了风景之中微妙的秘密。湖与鱼的秘密:“多少年了,鱼只把许多温暖的纪念留在湖中,忘记了天空与大地,超世的安宁像水,静静流入鱼的心中,与鱼的日子融为一体。”(《抒情的鱼》)湖与岛的秘密:“岛是南湾湖真实的纹理,是一种事物的形态,抑或独立不二的意象。哪里有狭窄,这里就有宽敞;哪里有枯燥,这里就有繁茂;哪里有喧嚣逼仄,这里就有淡定从容。所以,岛是南湾湖集中的才华。”(《岛》)湖与鸟、人与鸟的秘密:“沿着缓慢的湖水,路径在那里汇合,人与鸟,全都通往丰饶植物的始端。湖中岛异常肥沃,种满鸟的许多种声音。……常常人与鸟,或鸟与人,一步又一步,一步比一步,更接近更接近。”(《接近》)作者写出了湖的灵性,写出了湖与人与船与岛与鱼与鸟的相依与相通,从而揭示了湖的魅力之源。
唐朝是一位已有近30年诗龄的诗人,硕果累累。近年加盟散文诗,不断有佳作问世。《阳光下的河流》是一曲深情歌咏母亲河反思现实生活的诗章。黄河被历代诗人写过无数次,但由于她内涵丰厚,诗人之间阅历与审美的差异,每位诗人总能找到新的视角来表现。“借着月光,我将故乡慢慢寻找;荧光灯下,我将曾经浮躁的影子捉拿。我要用反思去抚慰昔日心中奔涌的河流,用简单的笔墨洗刷它背上的尘埃,重新点燃那条光亮。阳光下,我和心中的河流默默相向,温暖疼痛,相互疗伤。”(《阳光下的河流·七》)作品不仅写出了黄河与一个民族的发展、与一个人成长的精神渊源,更可贵的是写出了由黄河当下的处境而引发的反思和忧患。
张绍金生活在豫南大别山的金刚台,朝夕与大山对视,且又是一个玩石者,因而对山对石有着特殊的理解。《石头,延伸的目光》便是一篇对石头的诗意解读。石来自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因博大而朴素:“浸润海水的枯叶把礁石的颜色贴于脸上,绽开成初春的花朵。动心于你完成生命历程辉煌后悄然放下的姿态,收放自如。”作者对石头的解读是全方位的,到处都能看到石头生命的延伸:“石头,拒绝虚无的许诺,仅想用自己的存在去惊奇一些目光。”篇中佳句颇多,诸如:“石头开花就是一幢村庄,让梦和想念恒久居住”,“像阳光跨越一切障碍,石头浇筑我的灵魂”。作者对石的生命现象的深度解读,开阔了我们的心智,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启示。
在豫南乡间长大的青年诗人蒋戈天,虽生活在城市,但儿时的记忆刻骨铭心,时时跳入他的灵感,成为他诗歌创作不竭的动力。一组表现乡情乡音乡愁的乡土散文诗,读之如饮信阳的江米甜酒,味纯且能养人。“乡下的日子,旺旺的炉火,暖着寒夜,暖着静静打盹的人们。乡下的日子有些苦,那是衣服上多出的汗碱。乡下的日子更多甜,像是新酿的小米酒,加了蜂蜜和青梅,从嘴角一直甜到心尖。”(《乡下的日子》)仅有豫南乡土生活的经历,不能从平凡生活中酿出诗意的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你降生的巢,晾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树上,成为个人档案,成为渺小与卑微的标签。眼含热泪,飞向城市,瞬间的快乐让你眩晕,让你失去方向感。你的翅膀,承载不了酸楚沉重的天空。身披异乡的月光,有乡愁在眼底汹涌,你知道,已丢失了回家的路。”(《乡下的麻雀》)这是在写麻雀吗?也许只有感同身受,才会有如此跨界的惺惺相惜。
王剑是评论家兼诗人。他的散文诗《刀锋上的温度》具有情理兼融的特色。四位历史人物都是光照汗青的爱国诗人。因为大家熟知,写起来较有难度。王剑写出了新意。他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标志特征的词汇,化为意象,展开联想,穿越时空,最终做出诗意的评价。比如《屈原》,他用了“江”(汨罗江)、“刀锋”(以笔为刀)、“橘树”(屈原最爱的树)等意象,最后由橘联想到蕾,再到灯:“像独自醒着的灯,一盏盏伸向时间的深处。把黑夜一遍遍擦亮,把一个国家的命运一点点擦亮。”完成诗意的升华。又如《李清照》,通篇用“酒”的意象贯穿,把她作品中大家熟知的“菊花”、“海棠”、“绿蚁”、“梅花”连成一串,“最擅长的是把国破家亡的惨痛,酿成一坛千年的苦酒。”“喝着喝着,人就瘦成了一阕《声声慢》。如一根刺,卡在南宋的咽喉里。火辣辣地疼。”巧妙的构思,加上精准的用词,抽象出李清照词意与思想的高超。读后,不能不让人叫绝。
扶桑是豫南才女,分行诗独具一格,散文诗亦不容轻看。读系列散文诗《黑黑》,引起我类似的阅读经验,想起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不同的是,小银是一头银色的西班牙驴子,而黑黑,则是一只黑色的中国小狗。相同的是,都是一篇篇朴素优雅的素描,都是人和动物间平等纯洁的友谊。这是能够让人找回童心的读物。这类童话体的散文诗目前因稀缺而显得珍贵。
韩冰也是一位分行诗和散文诗兼写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擅于捕捉意识中充满诗意但又稍纵即逝的一刹那。比如:“一个花未开放的夜晚,我的一盏灯亮着,我的另一盏灯也亮着。它们是匆忙的,像一辆呼啸的小火车,突然地来,突然地去。而我遥望的眼睛刚刚够得着它的船舷,无论有多么的远,多么的高,都会被月亮的翅膀带回来。”(《一个花未开放的夜晚》)这种瞬间的捕捉,是技巧,更是功力。古今无数人写过月亮,但韩冰笔下的月亮版权独有:“荡漾的水,是多么的焦急。它们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小月亮,那么的美:薄的,厚的,方的,长的,扁的,圆的,仿佛天空一下开出了那么多的花。只有远远的一个,在我恍惚的时候,用灿烂的野菊花,抱住了臂膀上疼痛的故乡。”(《月亮》)读这样的句子,心会发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会长,湖州师范学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