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顾随——品读《顾随诗词讲记》(鲁钟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17日13:59 来源:青海日报 鲁钟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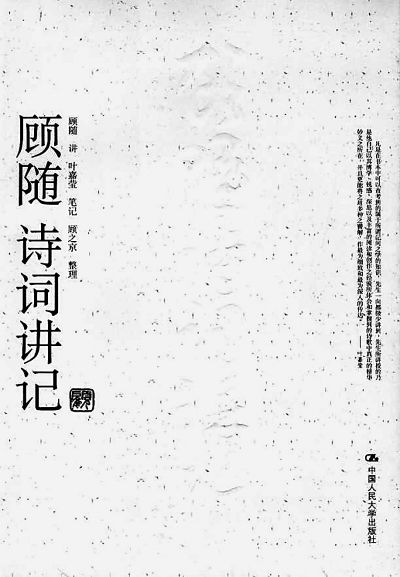
文学史上有许多“失踪者”,如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人,如果不是若干年后研究者们将他们的著作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何时“重见天日”还是个谜。同样,在学术史上也有许多“失踪者”,顾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不是他的学生们蜚声海内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们的授业恩师——顾随。
顾随本名顾宝随,河北省清河县人,生于一八九七年。赴北京大学英文系求学时遂改为顾随,取字羡季。一九二〇年从北大毕业后,顾随即投身教育工作。他教授《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唐宋诗、词选等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等科目。
顾随学贯中西,讲起课来旁征博引,给听课者极深的审美感受与启迪。叶嘉莹曾经多次聆听顾随讲授的课程,每次都受益匪浅。她曾说:“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这样的称赞实不为过。从这本由叶嘉莹笔记,顾之京(顾随女儿)整理的《顾随诗词讲记》中就可见顾随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深造诣。它可以算作是一本由学生悉心记录的笔记。翻开书,随处可见顾随的治学之光闪现,处处充盈着一番灵妙之气,真知灼见随意拈来。其中往往凝结着顾随本人的人生大智慧、大感悟。
现在各类诗词鉴赏的书籍层出不穷,良莠不齐,但顾随先生的这本《顾随诗词讲记》无疑站在了一个高处。作者的才华由诗词起,转而引申到形而上的高度,字里行间都凝聚着作者深沉的哲思与丰沛的情感。顾随先生在授课时,从不吝啬自己的好恶评价,任由自己的性情挥洒,一褒一贬中,戥秤可见。顾随先生说,“伤感最没用。诗中伤感便如嗜好中之大烟,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人做事便当努力去做事,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伤感!见花落而哭,于花何补,于人何益!”
这真是一语道破人生世相的许多真谛。
古者伤春悲秋大已有之,或若黛玉葬花早已有之。顾随先生却能从另一角度戳破这其中的假道义。又比如,王羲之写字便将自己一生的愤懑不平之气、失败的悲哀都集中在写字上,顾随先生说,这可以说是一种“报复”心理。“在哲学伦理学上讲,报复不见得好;但若善于利用,则不但可一艺成名,甚且近乎道矣。”对小李杜中的李义山,顾随不吝啬溢美之词,“若举一人为中国诗代表,必举义山,举《锦瑟》。”但顾随也同样客观地说这并非是诗的最高境界,“境界世界甚小”。顾随先生还对李义山的朦胧之美有如下见解:他将日常生活中的艰难苦恨转化为欣赏,然后用一种从容委婉的情绪,表而达之。就这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顾随先生还认为,曹孟德若事业上失败了,那么他的诗一定会更成功。更饶有趣味的是,顾随先生还从文学修养的角度打个比方,“凡写情书写得好的,多不可靠。”联想到胡兰成写给张爱玲情真意切的书信,让人忍俊不禁。凡此种种,在书中不胜枚举。
一蹴而就自是品不到书中的神韵之美。慢慢品读,仿佛在聆听顾随先生谈笑风生、博古论今的课堂讲课。从容与美感,怎不让人钦佩。正如周汝昌所言,“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至美,一音一字至妙……”所以,雅文、好书、好的讲义自是当细细揣摩,鉴赏。开卷有益,阖卷后也能在脑海中翻腾出书中的精髓,为我所用。
我们今天能够品读到顾随先生的高论妙语,大半要归功于叶嘉莹先生当年的听课笔记。在滴滴墨香与修改涂抹的笔记中,均可见师生情谊的一种“古典”式学术传承。薄薄的一册笔记,往小了说,是一段师生情谊的见证;往大了说,未尝不是一种文化的薪火传承。近年来,画家陈丹青也将老师木心的讲课笔记整理成《木心回忆录》出版,引起不小的关注。这些点滴的鼓励,或许能让那些隐匿在历史深处的才子们重新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让我们与他们“相遇”。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