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迭出的李东阳研究——读《李东阳诗学新探》(马大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07日11:14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马大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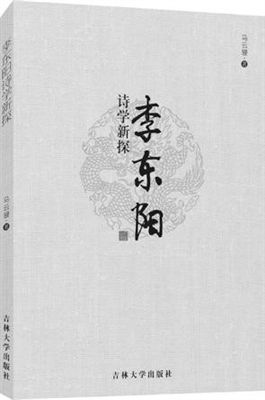 《李东阳诗学新探》马云骎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东阳诗学新探》马云骎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前我为学生刘坡的新著《李梦阳与明代诗坛》作序,曾有语云:“李梦阳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目。大与难都表现在他与明代诗坛的密切关联上面,某种意义上来说,抓住了李梦阳,就等于抓住了一部明代诗史。或者反过来,心里没有一部明代诗史,就不要去碰李梦阳。”其实,明代至少还有一位诗坛人物具有这样的分量,那就是与李梦阳关系微妙的前辈李东阳。正如马云骎博士所云:“作为明代权力———文章一体化的人物,李东阳对明诗复兴起了激发与倡导的积极作用,堪称有起衰之功。他以台阁身份润泽、充实了‘台阁体’,论诗有批判,有继承,包涵广泛,具有温和主义的色彩。不过,在与异军突起的复古派的竞争中,李氏诗学的影响遭到严重削弱,蹶而不振。这场‘比拼’的结果决定了此后百年诗坛的基本走势,意义极为重大。”(《李东阳诗学新探》前言)
马云骎的这本 《李东阳诗学新探》 是在学界近年对李氏较为关注、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的背景下完成并推出的。文章、论著之自称“新探”者不知凡几,其中不乏故作新奇、禁不住推敲的无根游谈,也多内胎仍旧、仅打蜡上光的“翻新”之见,但马云骎的这本论著却着实在坚炼的考证基础上迭出新意,读之令人惊喜。
首先当然是对有关重要文学史实的考索和廓清。如李东阳之“茶陵派”为明代文学史之成说,作者却以精详的考辨告诉我们:李东阳身边“甚至未曾凝聚一批真正的诗人”,茶陵派“既不是这些人的自我标榜,也不是时人的比拟称呼,直到 《列朝诗集》流布前都无 ‘派’ 之一语,直到《四库全书》 纂修前都无 ‘诗派’之一说”。作者指出,是钱谦益出于自身的门户之见,经营造作出一个以李东阳为核心的诗歌流派,用与前七子对立,从而为“茶陵派”的提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历经纪昀 《四库全书》 中进一步衍为“茶陵一派”或“诗派”,这一概念始得成立并被引为定论。对于明代诗文史研究而言,这样的结论可谓极具颠覆性,是石破天惊之说,而作者考辨凿凿有据,亦确乎值得信服。
又如李东阳与前七子交往诸事,以往之文学史叙述常予人“代兴”之印象,即七子崛起于李东阳身后。作者仍然是以文献依据划定了李东阳与前七子关系的基本时间坐标:两者相重叠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其诗学有竞争,也有排斥,虽李氏“论诗远比七子为涵容老练,但显然缺乏后者那种截断众流、唯我独尊的锐气和霸气; 其次李氏本人的诗歌创作较之诗论无疑存在着一定落差,被复古派讥为‘萎弱’,并不尽是门户之见”,于是,李东阳最终没有能够缔造一个诗派,“他的影响所以迅速为七子派廓除,就在于他其实没有一个足以与之鸣和的同道,没有一个足以传其衣钵的弟子。在被列入所谓茶陵派的一二十人之中,试问有谁能同复古派的群彦争衡?”这也是很有冲击力的反问,但同样是可以接受,至少值得认真思索的。
书中类此之新见不少,诸如李氏对于唐宋元诗歌的微妙立场、理论参照下的李氏诗歌创作等,其中“序章 《麓堂诗话》的文本研究”是很专业的文献研究,但对这部重要诗学论著的文献清理是全文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之一,因而也是格外具有“新”意而足为“新探”的关键部分的。
对于李东阳及明代诗学我是外行,只是因为治清诗的关系上溯联及而已,所以并不具备评骘这部著作的资格。但对于马博士在这本书中体现出的“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良好学风,则还觉得有必要啰嗦几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创新永远是学术葆有活性、不沦为一潭死水的最大动力之所在。当今学界竞相趋新当然是符合这一良性态势的,但趋新不是哗众取宠,不能没有底线。我以为,趋新至少要有这样的资本:第一,要知“旧”,在充分了解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新创才是真正的“新”,否则即是坐井观天、徒劳无功; 第二,要有一分“新”创一分“新”,而不能任意夸大生造,以求炫人眼目。三、对于文献,尤其是常见文献,要有能看深、看透、看宽的能力,也就是说,能窥见实质,并整合提升,否则就会一掠而过、因循破碎。
当然,书中有些问题还可以再论说得深细一些,例如李东阳不甚刚决、略有依违的性格特征与他的政治表现、文学立场之间的同一性等,但也无妨,且可俟于来日。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