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思的诗意——关于任林举《上帝的蓖麻》(陈晓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21日10:22 来源:吉林日报 陈晓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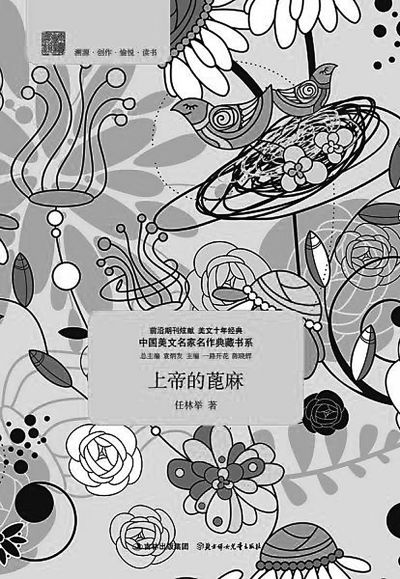
这本《上帝的蓖麻》,是作家任林举两年来出版的第三本散文专著,所不同的前两部作品《粮道》、《松漠往事》是长篇散文,而新出版的这部散文集却是生活短章,是林举在生活和旅途中的新发现、新感悟、新思考。其物我相融、且行且思的笔致,表达了他对社会的认知、对自然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全书风格是:文思瑰丽,哲理深邃——斯是前几部作品审美意蕴表达的渐次延伸和深化,可称之谓行进人生的诗意思考。
早年任林举以散文《玉米大地》引发文坛关注,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称这本书是“东北的土地诗篇”,此前我尚未看到过任何一位作家对东北大地的玉米,有如此凝重的挖掘、有如此诗意深邃的发现,他所开凿的尚未发现的意向深度,是我读过的即萧红之后,最具语境创意的全新表达,就东北黑土地散文创作而言,此书具有开先河之意义。
如果把《玉米大地》称作北方大地的深情长歌,那么《上帝的蓖麻》,就是浓烈、真诚的民谣,其文字平实、激情内敛、发现俏奇,如暗夜的一串流星,瞬间闪烁,炫目且引人回味。在阅读中,我不知不觉被其平实的文字,带入一个飞翔的地界——先由思考的“魔变”,再到哲思的顿悟——在“不觉”中度过的阅读快感,其实就是“共鸣”,即共享了作家的新发现,饱飨了作家最新创作之“鲜果”。这支看似不炫耀的笔,却凝结着积极、真实、善良、提示,甚至鞭挞与预警。运笔有责,在其文字间体现得淋漓尽致,正能量的发掘,都在“善”的根基下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林举馈赠读者的“慧眼”;这来自作家心灵深处的收获,具有同化读者的功能和魅力,因此这种被“虏获”的愉悦,就变得越加绵长、越加美好了。
本书首篇《枸杞》一文,不足两千字,写他当年在湿地向海创作《粮道》休息散步的瞬间,由看到湖畔木障下的几粒枸杞,而睹物思乡,再到与小鸟争食枸杞的情绪转换,写出了观鸟生情的发现,想到自然、想到人生、想到自由,想到更深层的人生境界,这时文章由“记”转而升华为思想了,他有感而发地写道:“突然觉得那鸟儿与我们人类相比,自由而又独特。它们也许从来不受什么逼迫,用不着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赶到某处,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毫无牵绊与阻碍。它们完全有权利以守候或守望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对某一事物的依恋;而我却只能经常以告别的方式,对某一事物展开另一种的思念。”表面看,情深尚无呐喊,而内里却饱含熔化的火焰。
当下的中国散文写作,不知何时染上一种抹不掉的脂粉气,用文字粉饰生活固然不可提倡,那么总找小视角、写窃窃小情调、描枯花病草,就是一种很好的路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文章没有大小之分,更没有高矮明显界定,但散文写作的确有个境界问题,谁能说鲁迅先生的《秋夜》、巴金先生的《废园外》是“小散文”?谁又能说普列什文露珠闪闪的短句《林中水滴》意境小、史铁生写平凡小人生的《我与地坛》不是“大”散文呢?其实好与劣散文的区别,重点在其精神含量的丰厚与浅薄上,崇高而深邃——这即是作家们毕生追求的目标。
我在林举散文中看到了这样的探索,请看《当水行至绝路》,“虚”写白水河到“跌”成了黄果树瀑布的自然奇观过程,其文字没有走常规笔法,写瀑布雄奇、壮观,还有秀美等等,而是在“悬河为瀑”的“决绝一跌”上大做文章,这一声“跌”,“旧”白水河消失了,“新”黄果树瀑布诞生了,作者抓住时机立刻推而演之,由写自然现象转化为写人生的规律,他描述河与瀑的辩证关系是:“水确实是不灭的,白水河跌成黄果树瀑布之后,散而再聚,待重新流淌下去的时候,仍然叫白水河。但不管它以后还会不会再跌成瀑布,也不管它是缓是急,我却一直认为,那已经是一条河的来生了。”这类哲思的描写,让我想到佛家那句著名的梵语:要让自己的一滴水永不干涸,就把它放入大海中……这篇散文告诉我们,自然和人生的“行”是相通的,高风险、大起伏就可能是创新的前奏,走极限、大跌落的失却自我,还意味着走向涅槃、走向再生——无疑这是作者代我们传递的人生哲理。
其实作家的才气,就是其艺术技巧包装思想的角度问题,其灵敏度表现在他对世界瞬间万变的感受感觉上,所谓“透视凡尘发掘真谛”,就是作家创作的一个审美过程,每次创作的新发掘,都是作家区别与他人的独特感受。在这点上,林举散文写的“巧”,就在他无修饰的、白描式的文字间深藏着,不在文字表面故作高深,而他的哲思却让人能一路跟读下去,很快就会自然认同和接受了,这是让人不得不叹服的写作技巧,这样的潜质让我隐约感到了大家风范的传承或诞生。我相信自己阅读的感悟。不信夜深人静的时候,朋友们去读读《婷婷》《来生还是父女》《穆西德拉》《往事如刀》《奇异的分裂》等散文,这类深藏爱意的短散文,很快就会让我们忘记幽暗,周身的温暖孕化于人间、心灵的湿润来源于本真,悲悯的情怀融汇于世界……
在这样阅读情致的相伴下,我们来读《上帝的蓖麻》,就会感到了生命的无限瑰丽,世界的无垠广袤——这样的阅读审美过程,怎能不让人心醉?
我们知道读书是快乐的,那么让我们一道来参与作家的行思人生,岂不正是巧遇上一个提升自我审视世界的好机会么?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