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童年和成长叙事(王雪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20日09:54 来源:新闻晚报 王雪瑛毕飞宇推出纪实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回望童年和成长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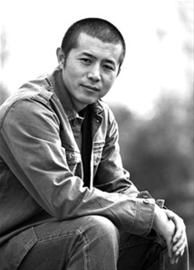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毕飞宇 著 明天出版社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毕飞宇 著 明天出版社毕飞宇是一个很扎实很稳定的作家,每次读他的作品,从他的文字中,我都会感受到他的天赋,他的认真,他的驾驭,就像我会从大地和泥土中感受朴实、力量、神奇。简而言之,他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他是一个值得以阅读的方式追随的作家。
最近毕飞宇给我们带来了他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以记叙的方式,非虚构文体讲述了毕飞宇在兴化街头长大的童年生活,“红领巾泳裤”、“奶奶的蚕豆”等情节感人至深。全书庄重与诙谐并存,情感与记忆交织,可以说,这是一部毕飞宇的成长叙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童年“老照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纪实性作品。
毕飞宇形容早年的自己是“一个黑色的、皮包骨头的、壮怀激烈的少年”,是一个“年少的、远东的‘堂吉诃德’”。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村’,我的父母亲则是杨家庄小学的乡村教师。”毕飞宇的童年故事从这句话开始徐徐讲述:他小时候的衣食住行,玩过的东西,身边的动物,到村子里的手艺人和乡亲们,当然,还有大地。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描写了许多趣味盎然的童年片段,比如他和小伙伴们下河游泳、爬树、撑船、放牛、掏鸟窝、爬到麦垛上看云,吃甘蔗、捉蛐蛐;他还满怀情感地记录了许多以前常见、现在却已渐渐消失的人和事,比如衣服上的补丁、杀猪、纳鞋底、盖草房子、村子里的篾匠、锡匠、剃头匠、弹棉花的人……对父母来说,这些熟悉又温暖;对今天的孩子来说,这些新鲜而有趣。毕飞宇说,他幻想“读这本书的是一位父亲或者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在膝头,讲一个爸爸妈妈小时候的事情,告诉小家伙:‘嘿,孩子,爸妈小时候就这样。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有一代人的成长资源,也有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尽管毕飞宇没有按照自传的 “体例”来书写这本书,但他仍然在散文集中,诚实地回溯了许多童年与成长片段,“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诚实一些,再诚实一些。”
评论家汪政先生读过这部作品后分析道,“我们可以将这部有趣的关于作者往事的纪实性作品看成作家的成长叙事,当然也可以看作一部教育叙事……毕飞宇也许没有认真地去盘点他的家庭,也没有刻意回忆他的长辈是如何教育他的,他又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多少,但他写了他的少年生活,这种生活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种延展。 ”
由家庭,毕飞宇开始走进村庄,慢慢地小心地拓展着他的生活半径,这样的拓展如同积墨法一样不断渲染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一个孩子基本的人生意识,他的好奇,他的怀疑,他对生活的兴趣,他对劳动的理解和参与……这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必须遵循的精神。 ”
对毕飞宇而言,童年物质相对贫乏的日子,“帮我建立起了对大自然的敏锐,帮我认识了人的复杂性。人,都是有好有坏的,在‘好’与‘坏’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对我来说,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的开阔性就有了很充分的认识,这个空间里有无限复杂的内部动机,也有无限复杂的外部能量。它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好处。 ”
读过毕飞宇的不少作品,再拿起这本诚实回忆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纪实文学,我往往会有这样的阅读动机或者说有兴趣追问:他的童年生活和他现在成为优秀作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他的虚构的文学写作和他真实的童年生活有怎样的关系呢?
毕飞宇从小在乡村长大,他对农村和农业文明有着最质感的认识,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
毕飞宇回忆他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五分钟的激情之后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他,“要一下一下地”,这几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
现在有人问他,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毕飞宇回答,坚持写三十年,不要停止,“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以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它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
而评论家汪政先生凭着对毕飞宇作品的熟悉,分析出他的小说创作和他的童年生活经历的关联,从他的小说的风筝中看到了与苏北大地的一线联系,“我们确实从毕飞宇的往事中看到他作品的许多原型,虚构的生活与实体的生活在这儿得到了草蛇灰线样的印证。故乡与童年是那么强大,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系在苏北的那块洼地上。我们不难从飞宇的回忆中寻找到他小说的蛛丝马迹。《写字》中在操场上以地作纸的男孩显然有着作者童年的影子,而蛐蛐让作者如此难忘,以至直接用其作为小说的篇名。 《枸杞子》中的手电也可能就是作家童年的家电……如果不是故乡特殊的地理地貌,那一望无际的大水,也许他少年时对空间的想象不会那么深刻和强烈,直到成年还会以《地球上的王家庄》顽强地挣扎出来。毫无疑问,毕飞宇的知识是丰富驳杂的,但乡土系列始终是他知识谱系中的强项。 ”
有记者向他提问,他日后的写作与他童年乡村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毕飞宇回答:“乡村生活为写作打了一个底子,可是我的灵魂和内心真正被打开,乡村是做不到的。帮助我完成内心重大转换的,是城市。也就是说19岁那年我不进城读大学,没有后来那么多年的城市生活,我想我的笔也许仅仅只能还原那个乡村生活而已,最关键的是,我会失去思想能力。 ”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