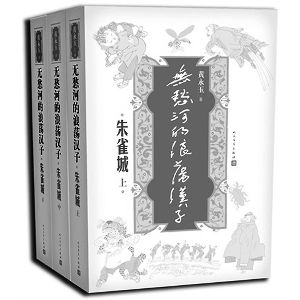 ■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全3册) ■ 黄永玉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全3册) ■ 黄永玉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提起湘西,无法忽略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没有人不知道他笔下的“边城”风情,而他的表侄黄永玉一篇《这些忧郁的碎屑》,让沈从文在历史重重迷雾中的背影清晰如昨。其实,湘西凤凰除了滋养有沈从文,还出过民国总理熊希龄、南北大侠杜心五、抗英名将郑国鸿……曾将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行当”的黄永玉,在90高龄时通过自己的笔,让民国时期的湘西凤凰,以“朱雀城”之名,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再度复活。黄永玉坦言:一个老头到了90岁,脸上、身上都长了“青苔”的时候才来出这部书,可谓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按照黄永玉计划,整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将分三部。这次出版的第一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年代设定在1926年到1937年前后10年。他计划在未来5年,写完关于“抗战八年”的第二部,在95岁到100岁间继续创作第三部。
诚然,80万字、带有“喜忧参半人生书写”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确实是一趟“无愁河”之旅。小说以黄永玉幼年在故乡经历的人和事为原型,原汁原味地还原了20世纪20—30年代湘西边城活泼多彩的生活景象,极其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作为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朱雀城的各个侧面,它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生活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黄埔军校回来休假的军校生、在河边野餐的朱雀城年轻子弟、老师、保姆、苗族小伙伴、民间艺人……种种欢乐与悲苦、呼吸与悸动,构成一座古城的勃勃生机。
所有细节都是原生态的,亦是永恒的:“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爷爷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从北京回来,见到这个长孙,当着全家人说,这孩子‘近乎丑’!”吊诡的是,这个“近乎丑”的孩子,在小说里名叫“狗狗”,原型正是黄永玉,朱雀城也就是凤凰城。为了删繁就简,《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使用了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纪传体的写法,从而使其内容既有集中,又能大开大合。
以“太婆”为引子,小说共涉及93个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是一部可观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它在追忆自我成长经历的同时,不断追问历史深处的沉重与诡异。不过,说其“可观”,倒不在于作者经历的坎坷跌宕,或者是此书彩页丰富、印制精良(这部书的确印得好,插页也选得精),这些是理由。而这里要说的是小说笔法看似十分随意,实则取材极为严谨,细节准确;语言尤其值得称叹,“平日不欣赏发馊的‘传统成语’,更讨厌邪恶的‘现代成语’。它麻木观感,了无生趣。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故乡思维”似乎被黄永玉装在一支宝葫芦瓶里,永世也用不完。
譬如,小说里写到刘三老的死、古椿书屋也就是幼麟的家毁于大火和田老三的死等细节最为生动有趣。其中,“刘三老的死”更是被作者“重墨渲染”——这个刚刚为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开追悼会的趣人,死了也让人拍案:“写了好几行大人字,顺手点燃了长烟袋锅,靠回到老躺椅上,唱高腔《赵五娘》,唱着唱着,嗓子越唱越小,就没有了……”难怪黄永玉说:“别了,匆忙的世纪,难再的忘年温暖。”又如,小说还写透了凤凰古城的各种大菜、小吃,色香味一一纷呈,读之像是在看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让人简直按捺不住。
小说虽然曾经在文学期刊《收获》上刊出过,但有不少删节,直到现在的全本才能读到这种流畅和一气呵成的感觉。若将“无愁河”仅仅看作是黄永玉对湘西老家的地方性回忆录,那也许大大缩小了它的意义。作者少年时代就离开故乡湘西,此后漂泊的脚步走过厦门、泉州、赣州、上海、台湾、香港,驻足北京,中年之后又从北京出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意大利)”,自己却坦言“不喜欢游山玩水”,一路都在工作……可是他却是爱家乡爱得罕见的极少数人之一。要懂他,需要明白这个世界性背景,能走得出去,才能看出其中打破隔断的转回来——这个游子带着征服了世界的全部信息,带着对百年来文化故乡危机的承担,带动着你我他这百年来莫辨家乡异乡的起起落落动荡情感,强大地归来——由此,小说中竭力呈现的,与其说是“传奇”,不如说是“本事”。而以“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为书名,或许是以“狂”著称的黄永玉想跟莎士比亚名剧《温莎的风流娘们》配个谑对。
沈从文当年是在北京写作《边城》,如今黄永玉也在北京书写他的“无愁河”,他对湘西方言的运筹帷幄,对语言和色彩的调动游刃有余,都让人们想起那灵动的凤凰城、沱江水和吊脚楼来……生活在间接性越来越强的现代都市,故乡永远只能在内心向我们敞开。而小说言辞间的犀利和迷茫、多情和无情更是令人时不时愣在故事的停顿处,发现作者说出了包括“朱雀城”在内众多乡村社会变流的某种真谛。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