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罪人?(袁伟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30日10:05 来源:新闻晨报 袁伟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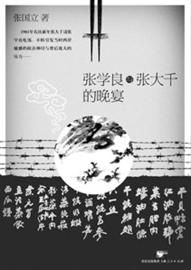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晚宴》张国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晚宴》张国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元月二日,蒋经国带着他的十一位民间友人“微服私访”,光顾花莲液香扁食店。这是台湾民众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地区领导人如此富有人情味,一扫过往蒋中正时代的政风。小蒋在他上任后,台湾气象一新,密不透风的戒严似乎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但是情治单位却并没有因为蒋“总统”这场做秀意味十足的“晚宴”,而放弃对另一场晚宴的监控。
那就是台湾作家张国立的新作的中的“张学良与张大千的晚宴”。此时的张学良已被前后幽禁了43个年头,称其为英雄者有之,骂其为罪人者亦有之。这场恰逢敏感时期并且早已牵动情治单位神经的晚宴,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呢?
张国立说,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这一场传奇式的晚宴,也是为了献给他自己心中的张学良。可他的落笔之处却并不是张学良本人,而是晚宴之外的群像——鲁台生、梁父还有李主任,梁如雪则是作者用来梳理故事线索的镜头。那些随着国民党一同转进台湾的外省人,早就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张学良发生了交集。没有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兴许就不会有梁如雪,更不会有“鲁台生”这样一个名字。而这四人却以这场晚宴为契机,一起走进了张学良被囚禁的晚年。
是英雄?还是罪人?这是一个问题。对梁如雪而言,两个象征父系权威的人物——父亲和上司李主任,代表了对张学良评价的两极。
梁父是孙立人旧部。孙立人素来有“被囚禁的第二个张学良”之称。梁父很自然地把自己对孙立人将军的崇拜投射到了张学良身上,认为少帅“当初上了蒋介石的当”,全面抗战没错,只是行动上有瑕疵。不论是在东北还是在西北,比起那些见风转舵的禄蠹,张学良是圣人。书上写的不过是被国民党改写的秽史。
而另一边的李主任,则是戴老板的学生。在他的眼里,张学良“阴谋推动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如果不是张学良破坏了蒋公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布局,他们决不可能至于转进台湾。张学良的义气,不过是“小人小义,竖子不足以成大事”。
曾几何时,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张学良也面临过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抉择。当时张学良究竟经历过一番怎样的挣扎,我们无法读到;那张令情治单位踏破铁鞋苦苦追寻的电报究竟是否存在,现在也已不可考。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张学良做出的决定,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轨迹。小说中,自从被软禁之后就开始研究明史的张汉卿,则在晚宴的尾声,以这样一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老人的神态宛如在一部活着的历史书上,写满了无尽的自嘲。
另一边的鲁台生则是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有着和鲁台生相似的经历,更因为鲁台生向张学良提出的那些问题,在作者多年之后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得到了回答。小说中梁如雪的男友赵岗与鲁台生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不想问西安事变的真相?不想问共产党怎么策动他犯下这滔天大罪?还有,像是日本军入侵东北时,他到底在干什么?”“问那些要做什么?都过去了,当然要问现在的事情,采访才有意义。”
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答案的是与非、对与错,而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这也许就是作者想借鲁台生之口告诉我们的吧。是英雄?还是罪人?人们总是执著于问:是什么?为什么?可这样的问题又有多大的意义?如果日本人没有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也许后来的张学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出国学医,从此这世上多了一位医师,少了一位军人。然而,历史却容不下这样的假设,人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去挖掘、解释它,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如果真有一双上帝之手在书写人类的命运,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冥冥之中的不可捉摸,那是对人类理智的嘲讽。“这是一本小说”,作者在序言里如是写道。这就意味着,对于张学良的功过、西安事变前后的种种内情……这部小说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张学良已经过世,老人留给我们的只有历史的迷思。
张学良晚年的缄口不言,注定会将历史的真相与他自己一起带进坟墓。当这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人坐在木制躺椅上观海听涛,看着夏威夷的海滩日出日落时,背负赞誉与骂名的他心中正作何感想呢?
想必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吧。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