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了却人间是与非(宋希於)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3日10:59 来源:北青网 宋希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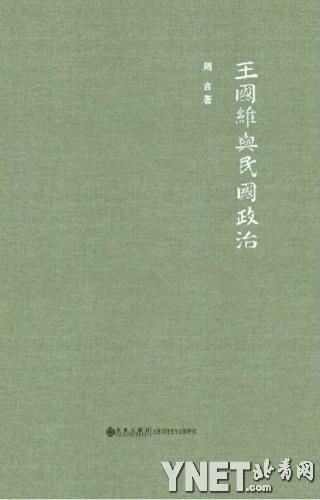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周言 著 九州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周言 著 九州出版社 2013年5月版在众多的青年学者之中,周言是非常用功的一位,他近年撰述与编著的书籍数量不少,在青年学人中亦可算学术成果丰厚。最近读到他的新作《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亦感受益良多。这本新作从王国维一生中较为人所知的部分入手,却具体爬梳到了长期为学界忽视的脉络和史料,努力想要达到弥补“王学”空白的目的。这样一来,一个作为旧知识分子、带有遗老身份的王国维,就从历史的通常叙述体系下走了出来,他关心政治这不为人所注意的另一面,也就渐渐浮出了水面。
书名既叫做《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王国维和民国政治当然是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本书既是写一个裹挟在新时代政治体系下的旧知识分子样板,又是写和知识分子发生交集和碰撞的那个典型的政治体系。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用辛亥革命作一分野。他早年热衷着的是西方哲学及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研究上多有成就。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突然改变了学术方向,一心转向国学研究。其中缘由究竟如何,罗振玉等人多有解说。周言则引证了王国维当年所作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作出了更进一步的确解。这首诗里有这样的话:“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周言阐述说,这里的“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当然指的是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间的矛盾,而“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则是辛亥革命风暴的席卷,“始知斯道齐衡嵩”即可与此年王国维写毕《宋元戏曲考》后转向国学研究的学术动向相印证。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具体影响,这段“夫子自道”可为明证。由诗释志,周言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本书既是写“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重点想必会放在民国时期的王国维。而纵览这个时期的王国维,人们总是会嗟叹不已的:一方面,王国维在新时代仍以保守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自居,政治思想上的落伍,一定程度上使他沦为了时代的绊脚石。但在另一方面,王国维实在是一位悲观的哲人,他凭借顽强的旧文化信念,在行为处事及学术研究上,还坚持着他自己固有的文化诉求,终于应了他三十岁时所写的诗句——“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他的死实在是令人惋惜。
因为辛亥革命,王国维改变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又避地东渡,更哀悼了端方、直詈了袁世凯、祭奠了隆裕太后,用周言的话来说,这是完成了他“遗老身份的自我确认”。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王国维对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次自我确认。这表明学术研究旨趣的变化往往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而王国维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最受影响的遗老群体里的一员,整个遗老群体的整体形象就在他身后时隐时现。
深受西学影响的王国维,却逐渐向遗老转型,在他的这个看似悖逆的思想进程中,实是所谓遗民心态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时期他的交友范围,就完全以遗老群体为主。他与罗振玉的关系甚笃,这其中有学术上切磋的相投志趣,但更有政治上引为同道的意义在。他又热心与沈曾植往来,这也与当时复辟浪潮再起的政局有着明显的关系。他关心政局,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常常讨论到时局的变化,常有精准的预言;但落实到行动上,又谨小慎微,不敢太逾越本分。周言在本书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及变幻莫测的政局所给予王国维学术上的刺激:如他的研究礼制,就不免与对重建道德礼制的考虑有关;而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与他“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是等等。
周言写王国维的死,他希冀用详尽的史料来还原导致王国维之死的全部原貌。而从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则很能令人从中感悟到一种死亡的不可超越感。前面曾经说到过,王国维实在是一位悲观的哲人,而这悲观的极致就是对死亡的领悟。为死而生,为生而死,王国维的死,某种程度上,又可算是践行了他人生哲学的终极思考。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令我瞩目的是作者并未避开一些人为划定的“禁区”,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秉笔直书,努力探索了真相。比如说,关于清遗老对共产主义及苏联的观感问题,学界一向讨论得比较少,但它却确确实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周言将本书的下限扩展到伪满洲国时期,这显示了周言在清遗老问题研究方面,已接受并发挥了台湾学者林志宏的观点,开始重视伪满洲国的建立与遗老敌视共产革命的态度之间的关系。这是王国维研究和清遗老研究的新动向。
总而言之,作为王国维研究的最新力作,周言的这本新作深入探讨了王国维不为人知的一面,梳理了他与民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作为青年学者,周言则证明了中国的年轻人并不缺少历史感。可以这样说:《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是一部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年轻一代学人锐意进取和思想解放的作品,值得一读。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