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上偶然留指爪”——《陈漱渝讲胡适》后记(陈漱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22日10:48 来源:人民政协报 陈漱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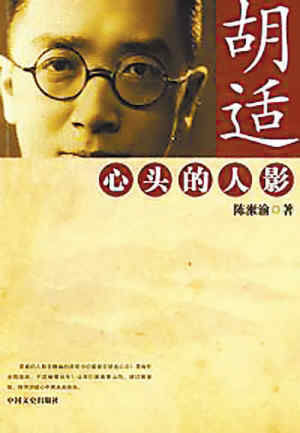
■阅读提示:
胡先生的人格学识极具魅力,既有男性崇拜者,也有诸多女性崇拜者。但胡先生是谦谦君子,也可以说是一位中性人。“中性人”这个提法,我当时听来颇觉新鲜。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胡先生并不是什么“中性人”,而是一个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汉,只不过他的学术魅力非一般人可以比拟。
我对胡适作品既谈不上有阅读兴趣,更谈不上有研究心得,但如今居然又出版了一本谈胡适的书。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掌控着。
那是在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到台湾探亲访学。几乎在同一时间,台湾陈宏正先生在社科院近史所耿云志先生陪同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探访我,结果失之交臂。陈先生后来见到我谈及此事。我问他找我有何见教?他说:“你出过一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历史读物,书中提到胡适是买办文人。胡先生一生从未经商,怎么能称他做买办呢?”当时海峡两岸存在的这种隔膜使我不禁发笑。我耐心解释说:“买办文人是胡适在大陆的通行头衔。并不是真指他做生意,而是说他一生执着于引进西方文化,尤其想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是一个政治文化方面的掮客。1955年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对胡适都是这样称呼的。”陈先生似乎也苦笑了一下,不知他对我的话听懂了多少?也就是在这次会见时,陈先生说,1990年冬台北将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纪念胡适诞生100周年(按虚岁计算),将由著名艺人凌峰先生主持的民族文化交流基金会出面邀请我参加。我答复说可以,但并不入心,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我有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凡对别人承诺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去兑现,而别人对自己的承诺千万不能当真;因为别人的想法和态度可能变化,别人的处境也可能发生变化。如果认真,自己很容易受伤。
然而,1990年秋天,我真的接到了在台北举行的胡适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邀请:东道主负责提供往返机票,安排一周的食宿;要求与会学者提交一篇学术论文。我当时正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便赶鸭子上架似的写了一篇文章:《同途殊归两巨人——胡适与鲁迅》,权当参会的入场券。
我记得开会时间是当年12月15日至16日,地点在台北政治大学的“公企中心”,议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境外学者的食宿安排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ymca”,大概是青年会的一家宾馆。在这里,我初识了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和唐德刚先生。此前我读过周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他也是我的老乡——湖南人,所以在餐桌上聊得很亲近。唐先生是安徽人,我读过他的《胡适杂忆》和他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获益良多;因此老作家苏雪林把他比喻为背叛耶稣的犹大,骂他背叛了老师胡适,我极为反感。唐先生学识渊博,会上会下侃侃而谈,幽默风趣,丝毫也不摆大学者的架子。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以下记忆:一、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言,好像是Jerome B·Grieder,中文译名叫贾祖麟,我记得读过他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当时用英语发言,主持人问需不需要翻译?除我之外的与会者几乎同声表示:不用!这令我对台湾学者的英语水平十分叹服。不懂外语能不能当大学者?我觉得研究民族特色十分鲜明的学科也许可以,如文物鉴定之类,但研究像胡适这种脚踏中西文化的双语作家,不懂英语,不了解西方文化,学问的格局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大的。二、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反响颇佳,全文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会后从100多个与会者的论文和讲演中遴选出14篇编为一书,其中就有我的论文。这着实超过了我的预想。三、我发言后有一位听众提问:“请问陈先生,如果鲁迅活到今天,将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假设是个伪命题。回答者的政治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借题发挥,可以有不同答案。比如,胡适的假设是: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的假设是:鲁迅假如活到今天,不会用他那支犀利的笔讽刺新社会,攻击共产党。”万没想到十余年后,有人请我作一场以《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为主题的讲演,竟招来一场横祸。有些人只许我按照他们的政治理念来进行“假设”,而不允许我按自己立场来进行“假设”,可见“文化专制主义”有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如果胡适活到今天,仍然会主张容纳异议吧。四、我发言之后,有一位中年学者主动跟我打招呼,夸奖我的文笔不错。他同时签名送我一本书,书名是“延安的”什么什么。因当时我觉得书名罕见,所以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这位先生叫陈永发,如今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成为了台湾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五、会上还有一位胖胖的老人讲演,他就是胡适的朋友傅安明。他说,胡先生的人格学识极具魅力,既有男性崇拜者,也有诸多女性崇拜者。但胡先生是谦谦君子,也可以说是一位中性人。“中性人”这个提法,我当时听来颇觉新鲜。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胡先生并不是什么“中性人”,而是一个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汉,只不过他的学术魅力非一般人可以比拟。
会议休息时的情况也颇为有趣。那次会议由于得到台湾时报文教基金会的资助,经费颇为充足,每位论文提交者得到了1000美金的稿费——这在当时的台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领到这笔稿费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酒友中有一位刘绍唐先生,他创办的《传记文学》刊登了不少珍贵史料,因而在史学界赢得美誉,被戏称为台湾“国史馆”兼“野史馆”的“馆长”。刘先生的海量无人能敌。他未尽兴,提出要到希尔顿酒店去喝二遍酒,无人响应。为免他扫兴,我于是奋不顾身,单独作陪。到希尔顿之后,刘先生以酒兴助谈兴,话变得更多,主动跟我讲了一些他在美国的艳遇。由于我当时也有些“醉眼陶然”,所以他说的那些细节听完就付诸东流,至今没有作为“野史”流传。
要而言之,回忆起来,这次胡适研讨会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政党、政治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等等。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主要分歧是: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对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曾经担任过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认为,“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余英时《序〈胡适与近代中国〉》)。如今,我看到大陆的胡适研究日渐摆脱了单一的政治模式,而在学术上日趋多元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对胡适都能进行具体分析,倍感欣慰。
这次赴台湾,我除开发表了以《胡适与鲁迅》为题的论文之外,还在《中国时报》发表了《胡适与毛泽东》。因为同时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发表两篇文章,所以后文换了一个笔名“沉鱼”,取“陈”“渝”的谐音。我又在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整版的有关胡适的史料,在台湾《历史月刊》发表了《胡适与周作人》的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今天看来真知灼见并不多,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增添了我研究胡适的自信。从台湾返京后,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等文,也受到了广泛好评。由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学人对胡适在海外的情况并不清楚。1992年1月26日,《新文学史料》的顾问楼适夷特别写信给王元化先生推荐我的文章,说这些文章的内容“皆前所未闻”。多年后看到楼老的遗札,我因这位老作家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而深受感动!1991年,我又有幸到胡适的故乡参加了在胡适故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说的话都忘记了,只留下了一篇游记:《胡适故乡行》。
在去参观胡适故居的途中,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处极小的坟茔,拨开杂草,露出了一个矮小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曹诚英之墓”几个漫漶的字。这引起了我研究胡适女友的兴趣,后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胡适心头的人影》。当时自认为多少有些新资料,有助于用“以史解诗”的方法解读胡适的诗歌。近年读到江勇振先生的大著《星星·月亮·太阳》,才感到拙作资料的欠缺;同时也印证了我上文提及的一个观点:不懂英文,就不能在胡适研究领域有大的作为。也就是在参加境内外有关胡适研讨会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批新朋友,他们是欧阳哲生、胡明、沈卫威、闻黎明等。他们的共同点是博学而宽厚,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起了积极影响。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时光飞驶,从1990年至今不觉已有23年,而我在胡适研究界还只取得了一个“票友”的身份,距离胡适研究的殿堂十分遥远。即使天假我年,能再活上23个春秋,我也不可能在胡适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因为得到中国文史出版社王文运主任的鼓励,现将这些有关胡适的零散文字结集出版,作为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纪念,也希望同时能对于研究胡适的初入门者多少有些帮助。是为跋。
▲陈漱渝先生所撰关于胡适的一本著作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