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文学写作(季红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11日09:43 来源:北京日报 季红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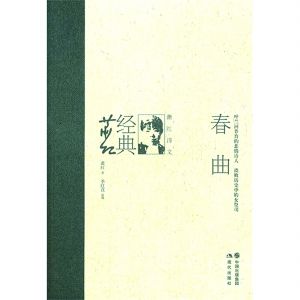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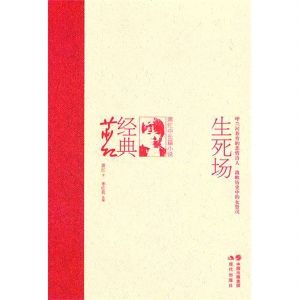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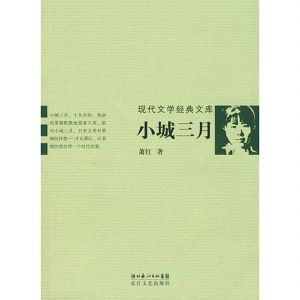
一部名为《萧红》的电影,将这位从北国偏远小城走出,一生漂泊干戈,生活情感均际遇坎坷的女作家,带到我们的面前。关于影片的种种得失并非是这里要探讨的话题,然而,从影片上映后听到的议论声中,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作家,她的作品,现在的人究竟知道多少?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这里刊发季红真教授的文章的原因所在。要了解一个作家,读她的作品是最好的途径。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篇文章,能为今天的读者,做一个有益的导引。
萧红生前一共出版了10本书,短短10年写下近百万字,文体遍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评论。纪念她的文字则有上千万字,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传记至今新作迭出。《生死场》在世纪之交搬上首都的话剧舞台,轰动海内外。她承袭了宿命的苦难,在错动的历史中艰难跋涉,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与左翼的意识形态,使她从民间的历史视角叙述现代性劫掠中的溃败、变革与抗争,一开始就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思潮,以“对着人类的愚昧”为自己的文学使命,文化人类学是其基本的学科基础,天命的原始思想是她阐释民间精神的泛文本背景。
溃败与重建
萧红生长在中国历史急剧动荡的时代,现代性劫掠的外族入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迅速崩溃,民族危亡一开始就是她成长的意义空间中最严峻的问题。而维新的乡绅之家的特殊文化环境,又使她得以进入应对溃败的新文化潮流。由于神秘婚约的束缚,她与家庭的关系由紧张到彻底决裂,更前卫的新派知识者的思想启蒙,使她天然地易于接受激进的左翼思潮。她中学的历史教师姜寿山毕业于北京大学,美术教师高仰山是刘海粟的学生,而她出入的哈尔滨左翼文化沙龙牵牛坊中多有革命志士。她的创作一开始就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引人瞩目,而且是从民间的视角、以民间的记忆与民间的方式叙述。溃败是萧红历史意识的基本主题——家族的溃败、乡土的溃败与文明的溃败。她以各种溃败的生命故事为焦点,连缀起大跨度时间中的历史图景,表现了现代性劫掠中整个民族所经历的巨大苦难,特别是在外族入侵的危难情境中,历史时间倏然断裂所带给乡土社会的急剧震荡。《生死场》以一组人物的命运故事,表现了在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乡土人生从失败的变革到奋起抗争的完整过程,为断裂的历史留下了最初的遗照。萧红因此而成为民族历史的书写者,她的创作和其他作家的创作一起,成为全民抗战的先声,带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特殊意义。
身为女性,萧红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诅咒,被认为是不祥的孩子,在升学、婚恋等一系列问题上阻力重重,而且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仅仅23岁就已经经历了一个女人可能经历的所有苦难。这使她对女性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敏感,女儿性与母性的精神从始至终涵盖了她所有题材的写作,取材最多的就是女人以及鳏寡孤独们的命运故事。展示女性的特殊经验,是萧红民间的历史视角中最令人触目的景观,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叙述的就是失去丈夫的孕妇与孤儿的悲惨命运。而女性的文化处境也是她洞察历史的基点,《生死场》中未婚先孕的金枝被男性同胞所强暴,种族立场和性别立场发生了抵牾。而女性生物学的局限又使她以赤裸裸的笔触表现生殖的种种苦难,她先后写了六起生殖的事件,在融合着痛苦与欢欣的自我凝视中,把拉伯雷食与性的身体狂欢推进到人类延续生命的基本情境,也把托尔斯泰和巴金们对于生殖无奈的厌烦与恐惧转变为繁衍生命的泛人类学主题。这是两性共同的伦理命题,因此萧红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咏生殖的悲情诗人。
萧红处于多种话语体系当中,却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许多次濒临崩溃的时候,都能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她在和外部世界抗争的同时,也坚持不懈地和自我角力。萧红对“人生何如”的价值追问接近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的思维深度,而悲凉的诗性情感基调则是整个民族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下在溃败中共同体验的历史情绪。她以病弱的身躯承担着个人、女性、种族乃至人类的所有苦难。“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是萧红对人类情感价值的顽强坚守。《呼兰河传》在一片萧条冷寂的氛围中,借助乌鸦的叫声与孩子的歌谣,呼应着逐渐转暗的火烧云,寄托了人类微茫的希望。萧红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在艰难跋涉中,终于借助一个贫穷磨倌儿的生命故事,建构了再生的女性——母性的自我。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她写作的《后花园》赞美了超越于所有文化制度之上的基本的两性之爱,认同了普通人承受命运打击的泰然与坚韧,也表达了对地母一样的女性安详精神的激赏,以及对人类专注于工作的永恒伦理价值的认同。
流亡与回家的向往
萧红少小和祖父学古诗打下了音韵的良好基础,也开启了对宇宙人生的感悟。她在中小学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以古文为主,刚刚能够阅读,就遍览家中的唐诗宋词,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典小说;中学期间学习书法篆刻,一度迷恋郑板桥的书法;这些都影响了她的创作,她晚期小说对人生无奈的慨叹,明显渗透着古代的时空观念。生前最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明显地受到宝黛爱情悲剧的启发,但是表现文化震动中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乡土女性无奈的情感悲剧,翻出了新意。传统文化为她的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观物方式与时间形式,用以容纳溃败历史中多种文化犬牙交错中的空间形式与混乱的心灵感受。《呼兰河传》第一章从冬天的早晨开始,结束于秋天的傍晚,呈现为时空同体的无限流转,心灵感应着宇宙自然生命与人生的万古循环,因此比音韵更集中地体现着古代诗歌的精神。民间文化则是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文学的思潮中获得的启蒙。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在对民间思想的关注中,就包括对民间艺术的激赏,叙事中有多首民谣;《呼兰河传》第二章中,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民俗,有价值的批判,也有艺术形式与精神的心仪。民间艺术使她的乡土经验与现代艺术彼此交集,和传统诗文的精神一起,构成她的诗性生长的深厚土壤。
此外,萧红一生学过4种外语。除了中学主修英语之外,在哈尔滨期间和萧军一起学了俄文,在上海学过世界语,到日本又学了日文。各种语言构成多维的参照,使她对汉语细微奥妙的感悟更加敏锐细腻。她的文字渗透着感觉,或许是受感觉主义美学潮流的启发。她的叙事节奏感很强,而且根据人物与情节的需要而富于变化,儿童主人公的叙述语言单纯而简短,老年妇女则频率快而语气强烈,《生死场》中倒反天戈的王婆说话斩钉截铁,《梧桐》中流亡四川的东北老太太则节奏紊乱,表现出絮叨的言语特征。萧红创造性地继承了汉语的诗文传统,对现代汉语的艺术写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以语言的神奇魅力增加着整个族群的情感凝聚力,成为新文学的传统。
萧红身处国破家亡的动荡时代,她短暂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流亡中度过,无论是抗婚出走求学,还是躲避情感困扰,乃至逃离战争的威胁,最终还是死于战火倾城的香港,精神的抗争也以渴望回家作为失败的象征。因此对于失去家园的流亡者,她有着情感的深刻共鸣。这使她笔下的人物多是流亡者,分布于各个阶层、各个种族、各种党派、各种年龄段和性别。身为最早沦陷的东北地区的作家,萧红对于流亡异乡的东北同胞有着不言而喻的情感,发表的两篇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文章,都是以书信的方式致东北流亡者。近代中国革命与战争频繁交替,导致了几代人的动荡人生,流亡是民族历史命运的艺术折射。现代性带来的种族的频繁迁徙与全球性交往,使流亡也成为一部分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且,在任何时代也都会有因为各种原因自愿或者被迫的流亡者,因此这个主题也超越了所有的时代。萧红文学最基本的行动元叙事模式就是流亡,而且在具体的情节设计中,经常是与死亡两相对立。《生死场》的下半部基本就是各种逃离死地的故事叙事,《马伯乐》则是以逃离开始以回归与失败轮番交替的游记式结构,其他如《索菲亚的愁苦》中客居哈尔滨的高加索移民、《亚丽》中流亡的朝鲜族革命者等都是以流亡开始、以流亡结束。流亡的生涯是溃败人生挣扎循环的基本曲线,涵盖了所有流亡者的人生轨迹,这样的行动元叙事模式使萧红文学带有了泛人类学的普遍形式特征。
“回家”实在是人类永恒的梦想,不仅是地理的家园,还有精神的家园。但是,萧红无家可回,关山阻隔,战火纷飞,家园已经被割裂为异国。“回家”更多是她的想象,象征的意义也由此而生,对于所有没有家园的人来说,“回家”只是一种伦理的诗情。基督徒们面对残酷的现代性生存,询问的是“上帝在哪里”;而无神论者们,询问的是“何处是家园”。萧红以哀祭的文体,为自己,也为所有寻找灵魂栖息地的现代人招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起象征的心灵桥梁。“回家”是最朴素,也是最永恒的祭文。
萧红主要作品
《生死场》(中篇小说)、《牛车上》(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呼兰河传》(长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散文《小黑狗》、《祖父死了的时候》、《三个无聊人》、《初冬》、《访问》等。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