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邓晓芒)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01日10:10 来源:解放日报 邓晓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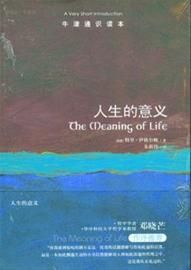
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前几年写了一本哲学书《人生的意义》。
他在书中坦承,自己不是哲学家,他是以“喜剧演员”的轻松明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崇高的主题的。的确,我们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到处遇到的是英国式的幽默和无伤大雅的调侃,但话题却是严肃而深沉的。
使我感到惊叹的倒不是这一沉重的话题能够写得如此通俗活泼,而是一本如此飘逸生动的小书居然能够切入到如此深邃的哲理之中。可以看出,作者虽然身为英国作家,而且研究的是最具感性色彩的文学理论,但明显深受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和解释学的熏陶。
我们只要看看伊格尔顿对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语义学分析就会发现,虽然他广泛运用了对词和意义的分析技术,但他不是用分析来消灭这个问题(比如,断言这个问题“无意义”),而是用分析来从语义层面的问题引向更深的存在层面的问题,亦即人生的悲剧处境的问题。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悲剧最彻底、最坚定地直面人生的意义问题,大胆思考那些最恐怖的答案。最好的悲剧是对人类存在之本质的英勇反思,其源流可追溯至古希腊文化……最有力的悲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句,刻意撕掉所有观念形态上的安慰。如果悲剧千方百计告诉我们,人类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它是在激励我们去搜寻解决人类生存之苦的真正方案。”伊格尔顿对悲剧的这种解释很新颖。悲剧并不像黑格尔的经典定义所说的那样,意味着两种同样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得到调解;相反,悲剧是对人的存在的一个提问,这个提问的答案是开放的。
“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 ”不言而喻,人生的意义更不是由别人规定好让你去实现的。我们现在通常的做法是,颁布一种人生的意义,写在教科书里灌输给孩子,以为只有这样孩子长大了才不会失去人生的意义,不会感到“空虚”。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做法。曾经有不少受过这种教育的青年满怀困惑地来问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一般回答说,人生的意义需要你自己去寻求,别人给的都不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学生,一涉及到人生意义的问题就很自信地背出从小学到的一套教条来,流露出不少得意,我却为此感到悲哀。
伊格尔顿在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人生意义的两个着眼点,一个是死亡哲学,一个是实践哲学。首先,伊格尔顿批评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以“幸福”作为人生的意义基础的传统,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他说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即不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迫切想要把苦难扫到地毯下面”。其实,西方文化正视死亡也是一个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巨大传统,柏拉图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但伊格尔顿在批评了各种幸福的涵义之后,也提出了一个真正富有洞见的命题:“人生若不包含人们准备好为之赴死的东西,这种人生就不可能富有成就。 ”他认为,“人生即是死亡的预期。我们只有心怀死亡才能活下去。 ”
伊格尔顿提出的第二个着眼点就是立足于实践:“如果人生有意义,那个意义肯定不是这种沉思性的。人生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它不是深奥的真理,而是某种生活形式。 ”所以,“人生的意义便是人生本身”。他并没有无条件地接受“爱”为人生的意义,而是对它进行了一番沉思性的解释:“我们称为‘爱’的东西,即我们调和个体实现与社会性动物之本性的方式。因为,爱表示为别人创造发展的空间,同时,别人也为你这么做。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成为他人的实现的基础。一旦以这种方式意识到我们的本性,我们便处于最好的状态。 ”不仅如此,这种沉思肯定也包含对死的沉思: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人生必有一死,我们才能为自己规划出和为别人创造出发展的空间。所以实践与沉思实际上应该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着眼点,即由沉思准备好的实践或者对实践的沉思。它既是 “深奥的道理”,同时也是某种经过反思的“生活形式”,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
伊格尔顿最后以爵士乐队的即兴演奏作为自己所推崇的“人生意象”。在爵士乐队中,每个人任意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但又随时保持着一种接纳性的敏感,与其他队员互相激励和呼应。在这种演奏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毫无目的的生活”,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有趣地接近于无意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这种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的,这些人必须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必须思考过爱与死这样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各自表达虽然没有明确的主题,但都以各自的个性和特有的方式发表着爱与死的宣言,并从同伴们那里得到应和。人生的意义之所以“接近于无意义”,是因为这个意义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在物我两忘中享受着人生的意义。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绝非一日之功,在日常生活中这甚至常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但正是这一理想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要将自己个人的人生意义实现在群体或社会的认同之中。
(《人生的意义》,[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朱新伟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