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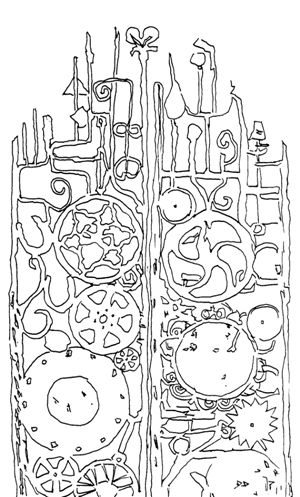 插画:杨续
插画:杨续摘要
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然而莫言的出现却是一个特例,他似乎让中国文学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曙光:地方生活、地方思想、地方语言开始在汉语文学中发光,汉语现代文学由此走向对20世纪启蒙及其代表的西化传统的背离,开始展示自身的更深层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走向民间话语等,但无论哪一种,都不能算是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整体困境,它们本质上依然属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困局范围之内,尽管它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对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反思,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反背。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然而莫言的出现却是一个特例,他似乎让中国文学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曙光:地方生活、地方思想、地方语言开始在汉语文学中发光,汉语现代文学由此走向对20世纪启蒙及其代表的西化传统的背离,开始展示自身的更深层的可能性。本文试图讨论的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到底抛弃了什么?知道我们丢了什么,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回头要找什么。
“传统”回溯式寻找者的稻草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也许应该从两个人及其两部作品开始:贾平凹《废都》、余秋雨《文化苦旅》。
贾平凹是一个具有极高敏感度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他写作了《浮躁》,小说名此后成为整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的代名词。《废都》的出场,也有同样的效应,这是一部在语言上模仿《金瓶梅》,在意识上也承接了中国明末《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长篇小说)文脉的小说,为什么《废都》突然接回了这个中国小说久已尘封的传统?《废都》某种程度上告别了理想主义风尚而转向世俗人生,告别了国家主义思潮而转向市井个人,告别了某种人文高蹈而转向物欲情欲,小说描写精神的幻灭、肉体的堕落、生命的毁灭。污浊的社会和扭曲的人性构成了小说世界观的一体两面。今天看来,《废都》展示的一切,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后来的世纪末“狂欢”,在中国还只是苗头,歌颂理想和礼赞未来转化为描摹黑暗和顺从丑恶,作者似乎突然之间丧失了用普通话叙述的兴趣,他突然改为俚俗化的文白口语,他是厌倦了什么吗?这种深层的颓唐和失望,也许不是来自对实有的观察,而是来自对心相的体验。这样体验里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赏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种论断用在《废都》上,可能也适用。
余秋雨的写作策略却和贾平凹恰恰相反。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上海学者,带着他的具有考据癖、历史癖散文集《文化苦旅》登上文坛,这个戏剧史学者,突然在散文上一举成名,并且市场传言他受到钦点好评。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收藏昨天》)。”因对大事业产生怀疑而回到小人生,因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而回到古代文明,余秋雨和贾平凹,这两个看起来极端不同的人,其实在思绪上是一致的。
余秋雨“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的“苦旅”,看起来比贾平凹振作许多,愉悦许多,似乎没有贾平凹的失望和颓靡。
看起来,余秋雨和贾平凹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两个人,向着某种中国古代文化回归和问询的路向又是极其巧合地一致。难道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反传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的“向西方”,让他们在大乱之后,突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传统文化?这个传统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儒家的兼济天下也有道家的退而为隐。余秋雨上下求索的苦旅形象和贾平凹笔下庄之蝶理想破灭后的人我不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正好代表了这种向传统回归的心态的一体两面——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和20世纪80年代那种崇鲁、崇五四的风尚告别了。
“身体”新生代的皈依与尖叫
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整体性失望,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它并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大症候:多数时候,人们在反对什么上可以取得一致,但在支持什么上,人们却总是莫衷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没有完成一种争取共识的体制建构。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新生代的出场,在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否定和失望上与贾平凹、余秋雨是一致的。没有余秋雨和贾平凹的顾忌及持重,他们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但却还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加入作协,成为体制内作家,也没有成为什么教授,获得什么有意味的文化资源。因而,多数在童年经历了文革,而在青年求学阶段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教育对文革的否定,思想否定加上童年黯淡的现实体验,让他们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否定,显得更加决绝,他们不像余秋雨、贾平凹等长一辈那样,对鲁迅有感情,不愿意再借鲁迅说话,他们要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告别,要把鲁迅这块“老石头”扔进垃圾堆——他们和以“革命”为核心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联系非常脆弱,让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显得更为决绝,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刚刚冲上文坛,和文化上任何传统及既得利益没有联系,他们甚至表现得和20世纪初创造社作家冲上文坛时一样的冲动:要和现有文坛体制“断裂”。他们成了一些文坛坏小子,一些不守规矩、以反秩序为乐的写作者。有论者认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世纪末反思与文学的功利化生产。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身体这个新的“神”。
事实上,新生代问题,至今为止,远没有得到澄清。首先被包括在新生代中的作家实际上包含好几个批次的人:比如女作家中从196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就有陈染、林白、棉棉、卫慧、朱文颖、尹丽川等为代表的至少三个批次的人,男作家也包括韩东、朱文、李洱、李冯、李修文、王艾等为代表的三个批次的人,男女作家有不同的特点,每个批次的人又有不同特点,甚至他们相互间也不能互相承认,后一批次的可能对前一批次的非常不满,通过革前一批次人的命出道,比如尹丽川就痛斥过葛红兵的“身体写作”不彻底,与沈浩波等人主张“下半身”写作,把葛红兵等的“身体写作”概念发展到极致——要求诗歌“追求的是一种肉体在场感”,那些被传统、知识、文化、承担、使命等异化了的东西,“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初的、原始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让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
现在回头来看,新生代作家可能是中国的嬉皮士运动群体。他们不屑于20世纪80年代那种追求富裕生活、民主生活的理想,或者对这种理想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屑于实际参加左派或者右派的社会民主或者社会反抗运动,对机制化的社会和生活充满厌倦,进而他们极端绝望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彻底否定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成就,从而走向文化和生活上的双重反主潮,这种情况下,他们皈依于身体(极端化之后又把身体归结为“性”),把身体作为反抗的武器,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如此,时过十年,新生代创作在长篇小说上成绩不高,卫慧、棉棉、葛红兵、安妮宝贝、雪漠等相继转向佛教,也显示了新生代身体写作思潮的衰微。他们的文学性成就是如此,在市场人气上的成绩也不佳,他们没有跟上韩寒、郭敬明等后起之秀的市场步骤,这群更年轻的作者抓住了青年读者群,而另一批网上崛起的真正的网络作家们,如南派三叔、当年明月、唐家三少、天下霸唱等的市场成就他们就更是无法企及。正如尹丽川在2011年的一个采访中所说:“以前大家都特穷,在那儿谈理想。等我再回来(2000年——笔者注),大家都在谈市场。”但是,显然,那个时候,新生代作家都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力量,他们没有想过要在个人的个性、自由之外尊重民族叙事陈规、国家叙事伦理,或者,更加直接一点儿说,他们是一些个人趣味主义者,没有想过要真正尊重文学传统和读者接受。
民间 没有例外,但有相对较好的探索
如何整体性地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呢?它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好的十年,但是,绝对是相对较好的十年。在这个年份里,大家的确不再那么关心政治,不再一心为了政治写作——这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其实,任何政治,即使是所谓进步政治都是经不住文学的考量的,政治考量的无非是人间的功利,而文学要考量的却是超历史的真理。这使得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某种更深度切入民族历史的底层,询问民族根性的可能,他们尝试跳出现有知识模式,到“民间”,去开掘用民族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可能空间。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莫言。
莫言的《檀香刑》,对这样的小说,如果我们用启蒙叙事的大逻辑去理解,一定会不知所云,或者给出反面的评价,因为我们不能深入山东这个“地方性知识”的情景,不能理解“猫腔”的文化逻辑,不能理解把死亡当做一种“仪式”的文化意味,不知道《檀香刑》中“猫腔”式的唱和“普通话”的说之间存在的作为“异文化”的对比关系,就不能理解鲁迅笔下的看和被看的关系、杀和被杀的关系为什么在这里被颠倒了过来,人物的“猫腔”式狂欢其内在的行为逻辑,为什么和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的逻辑、“看客”逻辑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需要指认《檀香刑》所呈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小说类型,这个独特的小说类型和某种既定的地方知识深度联系,和我们今天的普遍知识构成相对的异文化对照,没有这种小说类型观,没有建立这种地方文化类型的特殊性视域,没有这种由地方知识类型而小说类型的观念,我们就无法真正解释这些小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真正的反鲁迅,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标志:《檀香刑》是对鲁迅启蒙主义写作逻辑的悖逆,看客、刽子手、被杀者的身份意义及关系逻辑完全颠覆了鲁迅《阿Q正传》的描写。深入地阅读需要我们将自己设定为小说情境中的有机分子,同其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地共享其文化的内部意义,我们相信,在小说的世界里,研究者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到被研究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进而体验和理解其所在文化和特定的意义世界。《檀香刑》在语言和叙事态度上的尝试,具有先驱的意味,它开启了用地方性语言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的小说创作线路。
换而言之,莫言的小说,给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启蒙逻辑、用革命逻辑解释小说的方案已经行不通了。在莫言的小说中,小说家成了真正的“本地人”,小说成了一套符号体系,它不仅提供作为具体事件的符号,还提供事件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大小背景,它呈现文化形态静态图景,也呈现其形态及其联系,它自身就在避免孤立和静止,并且呈现或者隐含地呈现着某种自我理解和解释,因而构成着一个互相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体系。在莫言这里,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现代小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要义并且诞生了自己的典范作品,这多少让人欣慰。小说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他们有义务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深处,至今尚未被文人语汇污染的词语,这些语词比现时代的任何一种文人思想都要更靠近思想的本源,比当今任何一个文人语汇都接近真理的源头,将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在原始意义上发光放彩,而不要修饰它们,遮蔽它们,让它们赤裸裸地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够了(关于民间问题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王光东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
本文简单地勾勒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走向民间话语等。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症结是“农耕文明主导”,启蒙的假想敌是农耕文明,但是鲁迅等最后落入的恰恰是乡土写作用反乡土来眷恋乡土的怪圈,这个逻辑值得我们深刻玩味,而中国现代革命意识的核心价值却都是来自中国农耕文明,好在王安忆的创作对此有了反拨,她的作品逐渐开启了都市书写的大门,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问题的范围。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还应该提起海子这个人。海子的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海子是一个同时具有世界眼光和地方知识视野的诗人、文学家。如果海子不死,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也许需要重写。
作者简介
葛红兵 1968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意写作与创意产业研究专家,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文学代表作有《沙床》、《财道》、《上海地王》、《未来战士三部曲》等,编著有《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创意写作丛书》、《类型小说研究丛书》等。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