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邓一光:写作是建构“我的城市”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2日15:06 来源:深圳商报 魏沛娜《文化广场》对话邓一光
写作是建构“我的城市”
 邓一光的三部“深圳人系列小说”,包括《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和新作《深圳蓝》。 (资料图片)
邓一光的三部“深圳人系列小说”,包括《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和新作《深圳蓝》。 (资料图片)  人物名片 邓一光,当代作家,1956年出生于重庆,蒙古族,现居深圳。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想起草原》《亲爱的敌人》《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说集《远离稼穑》《狼行成双》等30余种、《邓一光文集》(14卷)。最新作品是“深圳人系列小说”三部,包括《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作品被各种选�
人物名片 邓一光,当代作家,1956年出生于重庆,蒙古族,现居深圳。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想起草原》《亲爱的敌人》《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说集《远离稼穑》《狼行成双》等30余种、《邓一光文集》(14卷)。最新作品是“深圳人系列小说”三部,包括《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作品被各种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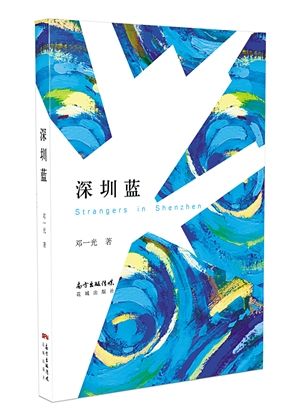

邓一光曾说过,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远方主义者,出生地不是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只要它能容纳我,都可能成为我的家乡。”而深圳,被他当成“一座森林”。“我不可能走遍这座森林,甚至连了解它都是困难的。好在我是这样一个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也因此,他通过不断的写作完成一次次对“我的深圳”的建构。
此外,小说之外的邓一光还是一位编剧,在深圳成立“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带领由一帮年轻作家组成的团队陆续推出电视剧和电影作品。同时,他也积极介入参与一些公共文化活动,策划或主编一些丛书,让人不得不敬佩他澎湃的生命热情。
“深圳书写”带有粗略的普遍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您迁居深圳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深圳蓝》这本新集子反映了您对深圳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
邓一光: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艺术作品的所作所为是让人们看到或理解独一无二之物,而不是判断或概括,这是艺术作品惟一可取的目标和惟一充足的理由。通常情况下,文本比阐释宽广和复杂,即使学者也做不到用概括和归纳代替无限的阐释,对作品的阐释权利还是交给读者吧,这是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最好方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蓝》依旧带有一个重要符号,就是“深圳书写”,几乎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在深圳的生活气味,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是这个时代的深圳“纪实小说”,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邓一光:不清楚你说的“纪实小说”指什么,所以没法同意。如果你提到的“生活气味”指人们生活的现象,或者别的概念信息或知识,我的回答是,小说在情感世界中与故事的主人公遭遇,提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审美经验,这个工作恐怕和记录式的传媒人工作相去甚远。
“深圳书写”这个说法带有粗略的普遍性,你在这里提到的“深圳书写”,或者别的什么人提到的“深圳书写”,和我认知上的“深圳书写”未必一样。人们习惯于从外部看待事物,以水济水,附影附声,试图使用流行于世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或者精神分析找到一条公共标识指导下的通道,以便解释事物的全部面貌,却疏离了自身经验在阅读作品中的自主阐释,而后者才是创造和解读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手段。
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镶嵌了不同的深圳地名,这些地名却不仅仅只是一种摆饰,而是各有用心,比如住在西乡和住在华侨城的人物设置特点就很不一样。那么,当初您是怎么想着把它们运用到小说里?
邓一光:地名包含地理、历史、民俗、语言等文化学概念,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以人为主体与地域有关的社会生活。但这不够,好故事不会被动地呈现地名,而是会对包括地名在内的故事元素做拆分和重构,生出新的意义,以表现人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受其支配的生活。比如这部集子中的《别把爱你的人送去香港》,周思爱杀了人,准备逃往香港避风头,她的前爱梁鼎和梁鼎的现女友包爱君为到底要不要送她去香港展开了一场争论。“香港”这个地名作为主人公的预设目的地在故事中反复出现,随着故事的发展,预设目的地开始由庇护转化为危险,然后是拒绝,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地名的本源意义消失,不再是地图上的地理符号和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化符号,延宕为主人公的生活被碾碎后,逃亡之地永远不存在,拒绝之地却无所不在的新的意义,于是读者恍然大悟,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香港”,作为实体它自始至终没有现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然,您的初衷并不是要做“城市地理学”的探索。可是至今距离您来深居住不过6年,我在小说里却看到您像是一个深圳土著,对这座城市的脉动和气息非常熟悉。平时在这方面是否有做特意的观察和记录?
邓一光:小说创作、解读和欣赏的困难,在于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对多数人来说,大部分经验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指涉,所以,主体意识不自觉的小说家,会下意识地守护住与现实生活相连的那根脐带,忽略文学的自觉主张,而与世俯仰的读者,会习惯性地放弃对文学作品丰富性的要求,只关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度。但小说之小,不妨碍它在整体性上的表达野心,其基础是小说家对表达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于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稔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小说家的本能——小说家像一条鱼游进新的水域,他会熟悉这片水域:水的来源、流向、成分、密度、膨胀度、热容、蒸发量、结冰期,以及水中的生物和食物链构成,滩涂和周遭的生活圈情况,本能决定他会这么做,不然他很可能会在下一分钟丢掉小命,不配做一条鱼。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我一生都在迁徙,带着我的家人,这使我不得不平添一份小心和责任,我对生活地的观察和融入企图,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警惕。
“他生命”是我小说的重要角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也插置了近年来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焦点和新闻,比如会以深圳居民赴港限行政策收紧、深圳高房价等为背景。在您看来,这种叙事快感与深层思考如何获得有机的融合?
邓一光:前面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一切人类活动都是文学创作素材的来源,这其中包涵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民俗和时事事件等等诸多文化,它们是文学价值属性的重要构成,是文学的DNA,其生发出的精神创造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最重要的自由创造部分。社会焦点和新闻本身不是小说家最重要的叙事快感源头,通常它只是故事的借口,小说家要在其中寻找到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新闻事件遮蔽甚至取代的那些内容,惟其如此,叙事才得以建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从您的小说里发现您似乎很喜欢深圳的花草昆虫。
邓一光:不是深圳,也不是花草昆虫,我能接触到,联想到,或者想象到的一切“他生命”,都是我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苏格拉底说,田野和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里的人们给了我这一切。我和他的回答不同,人们给了我教益,但人们之外的那些生命,它们给我的教益更多。
在想象中解析和重建城市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拜读您的小说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您总是在克制冷静地呈现人生活于深圳这座城市里的精神挣扎困境。但“深圳”最后又不能单纯视为现实的“深圳”,您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不知这种理解对吗?
邓一光:卡洛尔·奥茨分析过小说的写作动因,她认为,小说是对现实世界问题无能为力,对此又深抱怀疑的人们的一种优越感所为,他们用想象力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她说出了小说这一体裁的两个特点,人们对现实世界问题的不满足,以及想象力的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有着现实与现实之外两个层面,通过小说,人们能对现实世界丰富性内部的意义进行前所未有的梳理,这是别的手段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们习惯说城市,城市是什么?建筑、交通、工业商业住宅区、行政管理机制?不,没有人,它什么都不是,它连文化都没有。城市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你提到的精神挣扎困境,指的也是人的精神困境和挣扎。我们不妨把深圳是什么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想想另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他们的肉身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他们崇尚自然神论、泛神论、一神论还是无神论,对这些,我们知道一些什么?这些内容才构成城市的有机活力,是城市故事的真实内容,最终演化成文化,再形成城市历史。至于小说,在小说家的叙事之后,故事会产生全新的想象空间和情感能量,它不再等同于现实生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尽管您平时处事低调,可读过您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现实的态度描写现实,这体现出您对当下深圳怎样的思考?或者说,激荡您的是怎样的城市内核?
邓一光:城市是文明的集中体现,但它的辉煌史是靠着野蛮建筑起来的,你无法做到完全依靠抒情来完成对它的讲述,而简单的怀旧和忧伤更无法让你得以释放。如此,对城市的想象力就成了小说家必须面对的考验,小说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叙述和建构,使其成为个人意识中的这一座城市。
写作本身就是寓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笔下的人物或直接参与或见证了深圳的发展,而您的描述视角却是日常的,针脚非常细密。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用一种全景式的写法去描写深圳的城市生活?对于您来讲,又是否有这种野心?
邓一光:小说家对如下内容确信不疑:一整座海洋是海洋,一滴海水也是;海面上风浪大作时,海底水静无波。我现在从事着收集海水的工作,然后研究它们。这项工作让我所获匪浅,它几乎与我的现实生活并行。我喜欢这种日常的、需要耐心陪伴的工作,不排除有一天——也许明天早上,也许一百年后——我会对自己说,好了,为什么我不去遭遇那座海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1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上海作了一场题为《都市中的作家》的主题演讲,他讲到“文学对于都市生活方式在过去看来都表现了一种痴迷,因为在文学身上具有属于一种未来的效果,这一点尤其在小说当中可以感受出来,也许未来就是一种主要的构成成分之一,一部分是真实,大概有60%—70%,一部分是回忆,大概15%,还有一部分欲望,14%左右,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大胆预测那就是寓言。”您认为自己的深圳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寓言的力量?
邓一光:克莱齐奥表现了一位概率论者的“痴迷”,用统计学分析文学要素显然是件蠢事。15%的回忆和14%的欲望是怎么测算出的?决定论、量子论和混沌理论是否更有用武之地?寓言作为文体学或风格学实践,起始于人类早期的叙事经验,在缺乏对外部世界和精神无限性了解的前提下,通过寓言,人神共处的现实秩序和精神世界更容易被幼年阶段的智人理解和接受,西方对荷马史诗的解读,东方对《诗经》的解读,都是这一经验的运用。在现代语境下,寓言的使用更为自觉,也更为多变,借寓、隐寓和暗寓手段还在,却往往打破索绪尔结构主义经验,通过怯魅和重构,让所指和能指出现裂痕,使认知和救赎成为可能,这在现代小说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我认为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寓言,至少在现实存在与特殊性的关系上它是。至于我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寓言力量,我已经举过克莱齐奥的例子,就不把自己装进去了。
提供人们肉体和灵魂生活的秘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些年一直流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讲“中国故事”,深圳作家就要用“深圳故事”为“中国故事”提供重要的书写经验。而前阵子作家陈希我指出“讲故事,描摹生活,是文学的最低层面”,“我们不应该迁就这种趣味,不能再满足于讲什么中国故事,使中国文学继续处在低端”。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邓一光:我了解到的情况和你有所不同,“中国故事”只是一种理论提法,很大程度上这个提法缘于母语话语权焦虑,这在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中都存在,这也是作家叙事行为的驱动之一。问题是,如果把“中国故事”建立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表述上,在这一立场上完成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学实践,这会使文学不堪重负,很少有作家会欣然领受如此宏观架构下的个人写作工作,除非他们找到了那条通道。所以,我宁愿把它看做多元文化构成下主流文学讲述的吁请和例证期待,并等待视野中出现令人信服的文本。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随着“深圳书写”继续下去,您会否感觉到叙事难度也在增加?在自己想象力的固有边界上,突然蹦出缺口?如果有,您又是如何处理这种焦虑?
邓一光:如果小说家作为知道分子而存在,把写作建立在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之上,那与想象力无关,你的担忧会发生;如果小说家把写作当成一件诸如打井这样的工作,一条道走到黑,你的担忧也会发生,但这都是拙劣的小说家的结局。卡尔维诺说,城市犹如梦境,凡可想象的都可梦见,尽管二者之间只有秘密的交流、荒谬的规律和虚假的比例。写作的难度不在时间的推移和故事的积累,而在你能不能持续寻找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那个事物。小说家提供的不是现实生活的事实,而是人们肉体和灵魂生活的秘密,纵深不是在道路的前端出现的,而是在每一次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在你周遭的每一个角落、你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没有边界,想象力也不该有。
喜欢这座城市才来这里生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的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深圳的关系?您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生活于城市之中?
邓一光:深圳是我和家人现在的居住地,我是两千万居民中的一个,现实生活和人们没有什么太多不同,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也算不上密切。我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才来到这座城市生活,我希望它美丽而不冷漠,热情而不疯狂,智慧而不算计,富裕而不贪婪,公正而不平庸。这当然只是我的理想,但我不会等待,在回南天开足抽湿器抽去满屋潮气的时候,在告诫家人管住嘴少吃金枪鱼和牡蛎防止嘌呤的时候,在等待台风“茉莉”或者“韦森特”经过头顶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建构一座城市。我猜在我之外,这座城市有两千万个理想,如果它们一起升上天空,这座城市会有多么丰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武汉来到深圳写作,对您来说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邓一光:离开武汉我失去过去,来到深圳我得到现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后记提到今年到南欧旅行,介绍了在意大利一个中部城市卢卡的游荡见闻,平时您是否喜欢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并以此帮助建构自己的城市诗学理念?
邓一光:我的确经常外出,但没有数据帮助,所以很难证明旅行与我的写作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去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然后是南欧。比较麻烦的是,每次都要办理手续繁复的出境签证,我是不是能成行,和城市诗学没有半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签证官那一刻的情绪是否正常,以及我是否要临时动用旅行资费去填补突然发生的家庭开支。我不知道别人的理由是什么,我旅行的目的并不来自任何形而上理念的驱使,我只是有一种行走的欲望,然后开始收拾行囊,就是说,我的行动来自生物采集、狩猎、逃亡本能,我很庆幸这个欲望冲动没有退化。
参与公共事务全凭个人旨趣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与作家一般只关心自身写作不同,您在深圳平时积极参与了诸多公共事务,提携青年作家,给予帮忙让他们的创作之路走得平坦一些,低调主编或主持策划了不少文学图书。我非常喜欢张执浩对您的一句评价:“像一块磁石,迅速吸附四周散佚的铁片。”可以请您具体谈谈这些事情的原因吗?
邓一光:我参加公共事务不多,介入了一些公共文化活动、帮助过一些文化和文学机构,这些事情本不在我的工作计划里,实际上我一直在回避这类事。策划或主编的几套书,主要是观察了几年,觉得这座城市的文学在整体提供和有效梳理方面做得不够,可以说没有什么想法,外界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缺乏整体了解,评价完全建立在经验主义认知上,而这座城市又习惯性地依赖外界言说,挺荒诞的,这样就开始策划选题,和朋友一起做了上述事情,但总的来说,这个工作做得很不够,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来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事实上一个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也面临不少挑战。如果按照“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说法,作家在当中可能难免陷入“圆滑”、“老到”的危险。您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忧吗?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让自己的写作保持纯粹性?
邓一光:我在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和社会经济机构中没有任何职务,无职务动机、职能考核和收益,不拿干股,不参与分红,不买股票和石油基金,在社会上不进圈子,用不着顾忌集团利益,平衡关系,委屈自己去讨好谁,参与公共事务全凭个人旨趣,所以谈不上挑战,也用不着麻烦圆滑和老到二位仁兄来帮衬。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