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发掘埋在现实深处的诗性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26日13:55 来源:深圳特区报 王俊 梁婷 刘莎莎 尹春芳 孟迷 杨媚 刘永新
 陈先发
陈先发 李元胜
李元胜 何小竹
何小竹 潘红莉
潘红莉 刘春
刘春 古马
古马 余怒
余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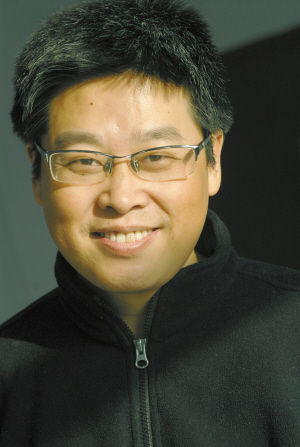 桑克
桑克 朱燕玲
朱燕玲 潘维
潘维■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俊 梁婷 刘莎莎 尹春芳 孟迷 杨媚 刘永新
●潘维:
诗歌在慢节奏里生存
在本届“诗歌人间”朗诵会上,第一个登场的将是一位来自浙江杭州的诗人——潘维。这位以鲜明的江南诗风享誉诗坛的诗人,将在一首名为《今夜,我请你睡觉》的诗中发出这样的诘问“我/潘维/汉语的丧家犬/是否只能对着全人类孤独地吠叫”,词锋大胆犀利。然而,潘维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却表示:“我喜欢在整体偏慢的节奏里写作,这是诗歌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潘维诗歌描写的视野基本放在江南,在风格上也体现出了独辟蹊径的个人色彩。他理想中的诗歌写作方式是为自己的心声构筑一条汉语道路,既能和伟大的灵魂交流,又能体察人性的复杂,同时,在诗歌中勇于承受时代问题。
最近,潘维让自己的精神触角向古典诗歌回溯,开始细读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和姜夔等人的诗词,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对于此次“诗歌人间”所纪念的陆游,潘维认为他是“诗言志”的代表诗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一生把为国雪耻、恢复疆土的理想作为他诗歌主题,是中华“民族魂”的锻造者之一。当然,陆游写日常生活与情感的那部分诗词更打动他,譬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对于体量如此庞大的古典诗歌传统,潘维认为,只要用汉语写作,就拒绝不了汉语传统。但如何自觉地承接,则取决于个体的认识和力量。对于他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努力,潘维最后都归结为一句话:把古典诗歌语言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要让诗歌面对现实中的生命和灵魂,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诗歌不是逃避现实的企图,而是相反,使现实更具生命。”
此次来深,是潘维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他对深圳的印象非常好。潘维说:“这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干净,充满健康和活力。”潘维认为,经过“诗歌人生”这种活动的多年历练,深圳完全有条件设立一个纯粹意义诗歌大奖,不妨建立终身评委制,因为“只有评委独立了,奖项才有创造意义和价值的可能”。
●古马:
每个诗人都在进行语言实验
读古马的诗,像在读着古代民谣,短促、灵动,又有着西北大地喷张出的血性。本周末,他将从西北兰州来到南海之滨深圳参加“诗歌人间”,并朗诵自己的名作《巴丹吉林》。在他启程之前,接受了记者的邮件采访。
古马的诗大多是短诗。在古马看来,诗歌是以少胜多的艺术,言简意繁。“对于语言的敬畏,就是对于生命和神灵的敬畏。许多时候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些杰出的文字后面会有生命的呼吸和神灵居住与走动的痕迹。所以,字斟句酌或者说惜墨如金,只表明我不敢也不愿对艺术造次而已。其实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在进行语言实验。”
而《巴丹吉林》,却是古马的一首长诗。虽是长诗,依旧是让你欲罢不能,浓重的气场直冲胸臆,逼得你落泪。而这首诗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次心灵的旅途。2006年8月他的母亲因癌症不治去世,9月写诗的朋友请他去巴丹吉林沙漠散心。沙漠中有一百多个美轮美奂的湖泊,瞬间让他想起了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中的一句话:“沙漠这么美,是因为有个地方藏着一口井”。他感觉好像第一次读懂了沙漠。特别是母丧给他的巨大的刺激和伤痛,让他回想起许多往事……旅行结束后,他写下了这首长诗。
后来这首诗和他的另外九首短诗发表在2007年《人民文学》第1期上,并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奖。对于这个让许多写作者趋之若鹜的荣誉,他只是平淡地说:“我的老朋友人邻理解我,他曾在《关于古马:诗人的秘密花园》中说过:诗人的内心在那一刻是多么的痛楚,而我们诗人所有的‘幸福’也只不过借着母亲的离去,撰写了那些所谓的重要诗篇。比起母亲的逝去,那一切我们宁愿不要,即便那是杰出的诗篇。”
诗人群体在当今大众眼中是很边缘的,但古马认为当今诗人的存在依然有意义:在于拒绝人类的心灵被一律地格式化,这是诗人的宿命,也是今天更艰难更珍贵的贡献。
●陈先发:
诗歌是“最终的话语”
都说诗人是寂寞的,但陈先发似乎是例外。他的诗,不仅在诗坛享负盛名,在读者群中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因此“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等数十种荣誉加身便不足为奇了。本周末,他将来到深圳参加“诗歌人间”活动,并且在朗诵会上带来一首《前世》。在他启程前,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去年来,程光炜、张立群、赵金钟等十位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撰文对陈先发诗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在他们的文章中,多处提到了“汉语传统”的问题。陈先发告诉记者,即便是在诗人内部,他听到的许多关于汉语传统的论述也是浅薄与可笑的。一些人把传统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比如雕梁画栋的建筑,或戏剧等等。其实,一个诗人需要面对的是“语言的传统”。陈先发对汉诗的传统特质概括为:“重视形体的,音律的;重视隐喻和寓言的;以意象诠注生存状态的;重视生存状态而轻视生活状态的;重胸怀而轻反省的;个体生命隐性在场的;对自然与人世持适应性立场的;依存闲适性而轻视批判性立场的;重视修辞的。”
在许多人心目中,在中国历史上,“诗人”曾是一种顶着光环的身份,而今诗歌与诗人的社会影响力却受到很大局限,“被边缘化”了。但陈先发却告诉记者,虽然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偶像多为屈原、李白一类的诗人或老子、庄子一类诗化的哲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当时就代表着主流。相反,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诗人,在当时就是“被边缘化”的人,离今人臆想中的诗人形象相距甚远。
陈先发说:“历史自会形成一套汰劣存优的机制,许多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因其天赋而在死后名声得以急剧放大,‘会在死后执掌话语权’,诗歌远非最热闹的话语,却是最终的话语!所以,我觉得对诗人而言,被边缘化毫不足惧,要相信埋在历史深处的理性。”
●何小竹:
当一座城市愿意为诗歌买单
这一年多,刚完成了两个商业写作、准备春节后进入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诗人何小竹确实累惨了。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写诗不受任何事务的影响,一直在写。”
何小竹的诗一直以平和的状态呈现,所作也多为短诗,很少见到他的诗作中有气势磅礴的冲击和激烈昂扬的叙述,但他的诗作却能予人最新鲜最持久的感动。就好像一杯温度恰恰好的花雕,它不浓烈,却隽永,放置时间越久,味道越浓郁,并不适合觥筹间拼酒力劝,但一旦饮尽却能在心窝久驻不散,慢慢可以把泪逼出来。
本次他带来的《一团毛线》就属此类。“这首诗是在梦中得到的灵感,梦中的感觉还要好一些,醒来后依稀记得些意象,然后写成了这首诗。诗歌写成后,就跟梦境没什么关系了,因为语言会自动生出某种意义。至于是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而诗歌的妙处在于,读者完全能够凭借自身的经验,激发起对这首诗歌的全新想象。”
对于深圳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何小竹不算最熟悉的面孔,但他对深圳众多诗友来说,何小竹却是一个不能不来的人。何小竹本次是第二次参加“诗歌人间”活动,一回生二回熟,对于深圳这座愿意吟咏诗歌的城市,何小竹言谈间很有相看两喜的感觉。“深圳能够连续举办这样的诗歌活动,没有一定经济实力是做不下来的。但其实,现在很多城市也都不差钱,但为什么就没有‘诗歌人间’这样的高品质活动呢?所以更深切的感受是,深圳愿意为诗歌买单。当一座城市愿意为诗歌买单,这就意味着这座城市在钢筋水泥之外,多了一个精神的向度。”
●余怒:
古诗是永远涂刮不了的烙印
同样是写诗,但是对不同诗人,诗歌创作这件事却有着不同的分量。对诗人余怒而言,诗歌仅仅是一种爱好,它关乎生存,但不是生存的全部。“在写作中,我时常感到一种隐秘的个人体验被道出的快感。这种体验是我的,往往也是同处于这个时代的人所共有的,大家都体验到了,别人没说出,我说出了,这使我很快活。”余怒说“我将此视为写作的惟一乐趣。”
生于1966年的余怒既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盛世,也经历90年代的低谷,以及当下的诗歌回归。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潮是不正常的,那时人民没有娱乐,便全民娱乐起诗歌。90年代有了卡拉OK,有了舞厅、高尔夫球、足球、股票,便将诗歌忘到了九霄云外。现在人民富裕了,要提高自身艺术修为,诗歌便又用一种新的方式回归了。
“我不反对人们将诗歌看作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也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诗歌,但是大众的好为人师的指点,我们这些写作者只能无话可说。”余怒说。今年是陆游逝世800周年,对于古典诗歌和当代诗人的关系,余怒也做了解读。他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强烈影响,我也是。古典诗歌已经成了我们身上永远涂刮不了的烙印。”
但是,余怒认为,当下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摆脱古典诗歌所给予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精神气质。“古典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我们的文明变得灿烂夺目,但它毕竟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使用那么一套语言和形式已经无以呈现这个都市文明下人们的感觉、想法,意识和潜意识了。新诗更加自由,没有韵律及形式的束缚,使自由无羁的想象力有了合适的载体。”
●朱燕玲:
从写诗到发掘诗坛新人
就像21世纪,人们无法逃避网络一样,在荡漾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上世纪80年代,想要逃避诗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当时校园里的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花城》杂志的副主编朱燕玲女士1981年念大学,而她的诗歌之旅却早在迈入中学校门时就已悄然开启。“那真是一个诗情激荡的年代。”朱燕玲回忆说“我甚至会因为读了几句美丽的诗而激动得睡不着觉。”
看诗,读诗,然后是写诗。朱燕玲坦言,自己的“诗途”其实和别人没有两样。自从中学时代与诗歌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朱燕玲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并陆续发表作品。不过,她却自谦说自己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大学毕业后就很少创作了。”朱燕玲说。作为一名文学杂志的编辑,朱艳玲表示,这些年来,自己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新诗的发展。
如果在深圳设立一个诗歌传媒大奖,朱燕玲则建议,一要对诗有所要求,二要对人有所要求,三要警惕“小圈子主义”。“要把握好诗歌评选的审美尺度,同时考量诗人的人品修为”,朱燕玲说。
●刘春:
诗歌成就生活照亮生命
“一个诗人以何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诗歌风格,与个人的生活阅历、才华、文化积累有很大的关系。最开始写诗是靠的是才华,随着年龄、阅历、生活经验的增长,才会发现什么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也才会洗去那些虚幻的肥皂泡,留下对生活的感悟和洞察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春这样说道。
供职于新闻媒体的刘春,在新闻的“硬”和诗歌的“软”之间游刃有余。诗歌对于刘春来说,是“幸福像花儿开放”的姿态,是对生活的感受的复杂与微妙感慨。刘春的诗歌里洋溢着一种温和而强大的力量以及捕捉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事物的能力。在他的诗中,最平凡的语言也能组织为强大的力量,冲击读者的心,比如《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比如《草民》,比如《坡上的草垛》。
在刘春的著作中,《朦胧诗以后》和《一个人的诗歌史》反响最大。《朦胧诗以后》以诗人、出版物、事件等多角度、多侧面展示了1986年以来的先锋诗歌状况;《一个人的诗歌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具体诗人为切入点,反映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诗歌生态和一代诗坛精英的命运。刘春说,《一个人的诗歌史》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专著,计划写4-6本,现已出版了前2本,第三本正在创作之中。
刘春不仅评点优秀的诗歌,也向往高贵的人生,在他的博客里,有一篇创作于11月18日的短文《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吵嚷,我也身在其中,要想遗世独立,几乎不可能,更何况我不是那种能够完全静下来的人。但我无时不在提醒自己:拥有独立人格,保持做人底线。”这是刘春心底的声音,在对生活的一次次感悟和思考中,他让诗歌照亮了生命,微笑着收获一颗宁静的心。
●桑克:
敏感是我的风格
“这就是命,这就是必须发生的诗。”诗人桑克将在《诗歌人间》朗诵这首个人新作《这棵树》。“它比较明朗,比较容易让人接受。通过写树,来写一些相关联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清晰,但同时关联的内容很丰富,容易引起比较广泛的联想。”
桑克曾自称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诗歌的写实却透出哲理性。“诗歌的本质是感性的,但是我用了理性的手段来表现感性,让诗歌更有逻辑。”不过桑克不太喜欢“哲理诗”这个词,他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哲理诗这种东西。“我觉得哲学就是哲学,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中的哲学不是哲学。”桑克说,“比如陶渊明写自然,是对于自然本身的描绘,里头包含了他的认识;但不能因为诗歌中掺杂了哲学观念,就取名哲理诗。”
写诗的时候,既感性又理性的桑克常在“修辞”与“写实”中徘徊。他说,“徘徊”其实就是一种修辞。“不必把它们对立起来,主要看这首诗需要什么。它需要复杂的反讽,可以;但有人就想直接说出来,也可以。我所有方法都不排斥。”
很多诗人都说无法定位个人风格,因为自己还处在无限的变化中,但桑克却不这么认为。“你骨子里的东西,属于你的独特烙印,是不管你怎么花样百出都不会变的。自己可能不便说,但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桑克说,“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风格是固定的。比如说敏感,就是我的风格。”
此次来深圳参加《诗歌人间》的主题是纪念陆游逝世800周年。桑克认为陆游有两点值得当代诗人学习,一是勤奋,二是至死不忘国家复兴与统一。“作为当代诗人,国家和民生的东西也要能够关注,起码要在诗歌里有一些反映,只是这种反映可以更个人化一些。”
●李元胜:
有一种创作叫特立独行
诗人李元胜是四川人。他的身上,散发出“巴蜀鬼才”的特有气息。他直言,自己是一位边缘诗人。这是因为,无论是最早的诗缘,还是创作诗歌的风格,他都和同时代的诗人不一样。李元胜是工科出身,他告诉记者,他在念大学时,偶然翻阅到一本外国文学作品选集里面有里尔克的诗。“当时就有电击的感觉,语言竟然还能有这样完全不同的表达法。”
自从被里尔克“电”到之后,工科生李元胜就开始写诗。“同时代的诗人,多是受到朦胧诗的影响。我却是根本没看过。”李元胜说“直到后来,我参加一些诗歌研讨会,发现诗友们谈论的话题我都不懂。这才开始补中国新诗发展史的课。那时,我写诗都好几年了。”不仅如此,李元胜的诗歌也是“自成一家”,他直言,自己和所有的当代诗歌流派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独立诗人,一个边缘诗人。”李元胜说。而正是独立和“非主流”,让李元胜更完整地保有了自己独特的色彩。“写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存在。诗歌是我个人的精神标本。”李元胜说。李元胜不光写诗特例独行,他对当代诗歌的观点同样是别具一格。对媒体诟病的“梨花体”和“羊羔体”,李元胜没有批判,反倒认为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产物。
“这至少表明了新诗创作题材上的无禁区。”李元胜说,“再者,我也不认为,媒体发表的那几首诗代表了诗人诗歌创作水平。”李元胜同时指出,这类诗歌中显现出的放松和从容,正是孕育优秀诗歌的温床。“都说这不是一个读诗的年代。但是,我却认为恰恰相反,中国人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躲开诗歌。流行歌曲里有诗,电影对白里有诗,就连房地产广告里都有诗。”
对于在深圳设一个诗歌传媒大奖的假设,李元胜举双手赞成。他表示,国外有很多诗歌大奖都是由传媒颁出的。诗歌是先驱的符号,举办诗歌传媒大奖与特区的先锋城市气质十分匹配。他建议,这个诗歌奖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坚守第三方立场。“要致力于挖掘和发现中国诗歌界的新人、新作。”李元胜说“那么,这个奖项就将是新鲜的,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
●潘红莉:
诗人应拿起笔来记录时代
作为国内“老字号”诗歌期刊《诗林》的常务副主编,诗人潘红莉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由写诗和编诗构成。虽身居北国冰城数十年,但谈起远在南方的深圳以及深圳诗歌群落,潘红莉的言语间难掩“老熟人”般的钟爱与热情。
“这是我第三次来深圳,每次深圳行都与诗歌有关”,潘红莉说,前两次来深圳是在去年春天,她和哈尔滨市作协的其他同事一起,为哈、深两地的诗歌“联姻”——《诗林》双月号落户深圳而来。“今年我们的另一个老字号期刊《小说林》双月号也落户深圳了,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合作伙伴,看中的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深圳有很强的文化愿望与理想,连续4届的‘诗歌人间’活动也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潘红莉说,深圳的政府关心文化事业,其决定以文化包围城市、提升城市品位的诚意明显,同时深圳的媒体、企业家也非常支持文化事业,深圳的优秀青年诗人倍出,都给人以清风扑面之感,印象至深。
很多读者有这样的感觉,明亮、温暖是潘红莉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但她自己说:“其实我有时候也有会小小的忧伤埋藏在诗行下面。”潘红莉认为,自己的创作多半是听从心灵的呼唤,而不会刻意压抑自己的欢乐或者忧伤。也许是与自身率真、直爽的性格有关,潘红莉诗歌中的热爱、发现以及心灵细小的触动随处可见,两次来深圳,潘红莉都有诗作留下,如《深南大道》、《红树林》等,她坦言,很难抑止自己对这座年轻城市的喜欢,每次来深圳都有创作的冲动。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