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田耳:我不要“名气越来越大,写得越来越差”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9日11:09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县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小说,2000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杂志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天体悬浮》、《风蚀地带》、《夏天糖》,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张灯结彩》、《衣钵》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等。现就职于广西大学。
田耳,本名田永,湖南凤凰县人,1976年生。1999年开始写小说,2000年开始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杂志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天体悬浮》、《风蚀地带》、《夏天糖》,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张灯结彩》、《衣钵》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等。现就职于广西大学。最近,花城出版社推出“锐·小说”丛书第一辑,包括徐则臣《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田耳《长寿碑》、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蔡东《我想要的一天》等四本。上个周末,田耳、王威廉、蔡东分别在广州购书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处与读者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
丛书的责任编辑文珍说,以这样的组合结成的阵容,是借助70后、80后与之后将要推出的第二辑90后作者一起,凸显不同时代的新锐小说家,反映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段各色人物的心态和生活细节,以求勾勒中国小说创作的轨迹和亮点。
1999年,田耳大专毕业,一度以推销电器为生,夜里写小说。从2000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发表一篇,产量不高,但质量高,每篇都不自我重复。仅有的几篇小说让他迅速进入评论家视野,成为《芙蓉》杂志社2005年力推的“新湘军五少将”之一。
那两年他没有工作,已近而立之年,被人嘲笑在家啃老。但他还是爱写,写出了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随即获得2007年鲁迅文学奖。此后,作家田耳正式踏入文坛。
“在《衣钵》中,一个大学生回乡当了村长兼道士,其中有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之乡愁;而《郑子善供单》如出知识分子之手,把弄个人叙述与官方的法定叙述之间的断裂反讽;《姓田的树们》讽喻性地描绘了县城与乡村的风俗画,几乎是一份巴尔扎克式的社会考察;《坐摇椅的男人》和《围猎》却像是卡夫卡的梦魇;《狗日的狗》和《远方来信》,在某些批评家手里,必是关于‘底层’、关于‘道德’的证词;《重叠影像》和《一个人张灯结彩》则因为扣人心弦的探案叙述大受期刊编辑的赞赏,后者更因为显见的宽厚和正派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田耳仍是难以界定和难以把握的,他的作品中各种趣味和路径杂然交陈。”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如此评论田耳的写作。
田耳则说,最初让他对小说留恋有加的,是小学时偷偷读完的《射雕英雄传》。“我至今记得读完以后,有近一月时间回不过神,回不到现实,家庭与学校有如地狱困住了我。另外促使我写作的,还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和余华的《活着》。金庸展示了故事具有使人致幻的效果,而王朔、余华则让我明白,‘叙述’就是小说的第一性。”
新书《长寿碑》收录了田耳三个中篇小说,均创作于2013至2014年,书中小说的排列先后与写作顺序恰好相反。在代跋中,田耳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写小说已是向死而生,这也没什么好抱怨,因为我确乎还有一部分过剩的感觉,要给没有感觉的人们匀一匀。”
对谈
1、安全感:以阅读累积的能力去处理生活
羊城晚报:2007年你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可在这之前,你一直没工作在家写小说,有过焦虑感吗?
田耳:如果真有焦虑感肯定也就过不来了,我其实比较有安全感,不太焦虑。1996年我考了一个大专文凭,1999年毕业,从那时到2002年陆续干了一些小活。2003年开始我在家一直写,到2007年获奖,2008年县里面给我解决了工作。在家写作那几年,我觉得比现在还要舒服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操心的,也没有人认识、关注你,蛮自由的。写作状态一开始肯定会好,但写作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名气越来越大,写得越来越差,基本上是这样。
羊城晚报:现在你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也这么看自己的作品吗?
田耳:我希望自己不要这样,因为我还在努力,但是能不能成功得别人说了算。但我看越写越好的,没有几个,这不是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格就可以的,是一个状态,还得听天由命。
羊城晚报:从阅读中获得的复杂性和从生活经验中的复杂性,哪一个能对你的写作产生更大的作用?
田耳:阅读经验和自己的经历,其实是统一的。我的生活经验并不多,但看书特别多,带着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体验生活,从生活里得到的东西其实是翻倍的。用我的观察和分析,第一时间去处理我经历和看到的事情,这样经验才能丰富。如果只说生活经验的丰富,我是欠缺的。为什么我能写?在于一个人处理生活的能力,只有你在阅读中累积了较多的能力,带着这种能力去理解生活,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好作家:写作“失控点”越多越好
羊城晚报: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很红火。但作为小说家,虚构的能力应该更重要吧?
田耳:我觉得虚构可能恰恰是考验写作者档次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虚构的基础是实的,是由作者实在的体验和间接的经验构成。小说好玩的地方,就是由实入虚。经过一定过程以后,突然到在一个点上,根据你在小说中建立的逻辑,写作开始失去你的控制,进入一个你无法预想但比你的预想更好的状况。在一个小说中,从控制到失控转换这样的点碰到的越多,越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这又关系到作者面对自己现有的经验,如何处理把经验上升为写作、上升为作品的过程。
我跟写作的朋友谈过一个观点:虚构就是我们处理现有的材料,一般的作家是粗选,要达到一定量才能选出矿来;但优秀的写作者,甚至可以把重要的矿山里选出来的尾矿买过去,继续提炼。但我那位朋友就用了一句话,好的创作就是在下雨之后的路边,从一潭积水里面钓出鱼来。这个比方,我非常惊讶。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70后作家由于生活阅历或经验不足,导致作品不如60后,这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吗?
田耳:每个时代都是先入为主的,这其实没什么好说,我更愿意说说写作的快乐。我在写作中获得的快乐特别多,我到今年才开始调了工作,到了大学,环境变了,觉得自己是作家了,反而写作的快乐没那么多了,有种焦虑感。现在是给你一间办公室坐那写,我以前写作是在县城里,天天喝酒,醒了有灵感就写,写完了也是不要改的,都是脑袋中先想好了,这段我觉得过了就走到下一段,不过就继续写。
我喜欢看NBA,写作的时候经常让自己感觉像打球一样:写出来的句子好,我满意了,两分,这个句子觉得更加好,三分。写一天下来我看自己打了多少分,是这样激励自己的。
3、《长寿碑》:惊喜自己有了预言家的气质
羊城晚报:《长寿碑》这篇小说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写出了生活里的复杂性,但不做任何褒贬的评判,你是有意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其中吗?
田耳:不是隐藏,而是发泄掉了。《长寿碑》的题材很简单,大家知道很多长寿县是造假的,老人的年龄档案是改过的。如果从人类学这样高屋建瓴的角度写,我就没法进入。那怎么跟人们进入得不一样,我要想一个点。
从我想写长寿村造假,到真正写出来,隔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想到,这种造假存在伦理难题。如果一个老人今年加了30岁变成100岁,假设他只有一个儿子今年40多岁,儿子如果不随之改年龄的话就会有漏洞。那如果把母亲和儿子中间加一代,原来的儿子成了孙子辈……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写下去肯定会有快感的。很好玩,这篇小说写出来以后,很多人说,你写的是我。
《长寿碑》写完以后,我小孩刚出生,于是请保姆。保姆一般是50多岁的妇女,但这位老人家到我家后,说她59岁,但我觉得不止。于是我按正规的手续,要她把身份证给我看,但她不给。后来我打听到老人住的村子,通过我父亲的熟人了解到,老人其实70岁了,档案中她的女儿是她妹妹。过了几天,有人打电话说,又有一个保姆带来我家看看,我一看真的傻眼了,和前个是同一人。我说你来过,她说我从来没来过,她已经失忆了。
你的写作和想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洽地发展,在现实中会应验,这是写作巨大的困难也是挑战,但也是惊喜。最后你发现自己有了预言家的气质。
4、写长篇: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明天
羊城晚报:您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曾入围“2014年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前十的榜单。在这部小说之前,你已经写过两部长篇了。
田耳:《天体悬浮》原本是个中篇,最初名叫《左道封闭》。2004年我还是到处游荡的状态,有个亲戚在派出所当所长,他知道我能写,邀我去住一阵,最好能写些好人好事。我在那待了两个多月,看到的无非是琐屑之事,大案也轮不到他们办,小事还有居委会。但我意外地得知辅警这个群类,那段时间我和他们称兄道弟,他们没有正式身份,是临时工。2007年我忽然想写,两个能力相当的辅警竞争派出所唯一的转正名额。当时写了几万字,但写着写着发现,对于身份的获取,并不限于辅警,各行各业都有,如果只写这个,格局太小,写起来也没劲,所以没写完就扔电脑了。
羊城晚报:后来为什么会捡回来?
田耳:2012年初打算结婚,想挣点钱,刚好有朋友邀请我当编剧,就去了。那部戏是室内剧,对故事要求不严谨。后来我发现,编剧只需先确定人物形象,塑造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之后只要按照他们的性格碰撞一集集往下走。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写不好长篇的症结所在:以前是用写中短篇的思维写长篇,事先把开头结尾都设计好。但现在写长篇,20多万字,这么大的篇幅,如果事先想好开头结尾,整个写作就变成是完全封闭的。从开头到结尾,总会与设想有所偏差,如果调不过来,勉强朝着事先设定的结尾走,势必会变得非常别扭。
我忽然想,能不能用编剧的法子写小说?于是捡起了《左道封闭》的四万多字,展开重写。确定人物性格后就由他们领着我走,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不可预知的明天,也扔掉了原有的结尾。写《天体悬浮》印证了我对长篇小说的设想,写顺以后,度过了一段安定惬意的日子。《天体悬浮》卖了三万册,是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接下来我打算继续写长篇。
王威廉:以悲壮感面对个体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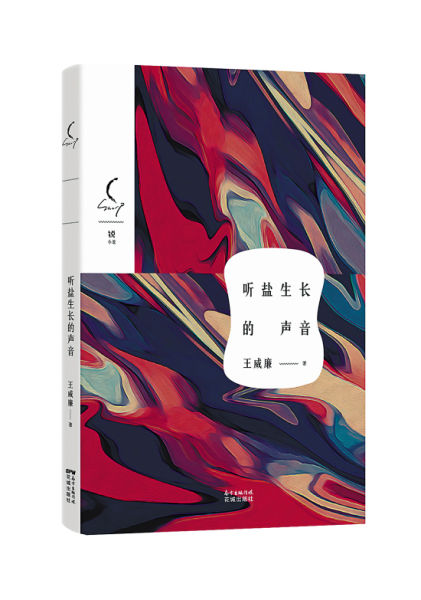
 王威廉,1982年生于青海海晏。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院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等。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
王威廉,1982年生于青海海晏。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院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等。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
王威廉从小喜欢听故事,因为他幸运地拥有一位满肚子都是故事的爷爷。“爷爷讲两种故事,一种是书里的,一种是他亲身经历的,比如抗战的、青海剿匪的等等。我能够写作,和经常听祖父讲故事很有关系。”王威廉说,还是孩童时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的生活丰富无边,并且能用语言保存下来,让其他人也能体验,“这是我生命经验的最初觉醒。”
中学时期,王威廉的作文一直很好,但他的偶像是爱因斯坦,对物理非常感兴趣。高考过后,他考取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没想到,入学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完蛋了,听不懂老师说的,数学不行”。他只好考虑转系,想去中文系将文学特长发扬下去。“结果中文系的老师说不要我,中文系就业率比物理系还高。所以最后我只能打打文科擦边球,选了人类学系。我给系主任写了一封信,他们很高兴,说欢迎我加盟,于是我成了中大校史上第一个大二转系成功的人。”
从那以后,王威廉开始写作,写了几年发现上了“贼船”,根本没人理、也没人看。用他的话说,是在中大校园里当了两年的无业游民。那时他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黑洞洞的,只有一个单间和公共卫生间。有一天,他在公共卫生间遇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他决定在小说里报复。“在小说里我把这个男人写得非常坏,写完之后忽然觉得,原来小说是这样的,不是写作文,而是把你的愤怒和情绪写出来。”
从事写作以来,王威廉也不止一次问自己,谁会喜欢听我的故事呢?“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但尽管如此,没有故事的我依然有着讲述的渴念,依然希望有人通过我的讲述,激活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在这种困境中,我只能虚构起来了。”后来,他读到本雅明所说的“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深感自己被理解了,“我再也不为那些从自己的孤独中凝聚起来的想象而惶恐不安了。”
新书《听盐生长的声音》中,第一篇即同名小说,源起于王威廉去西部旅行见到的一大片盐湖。“盐湖是干涸的,给人非常壮观、苍凉的感受,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场景写出来。刚开始我以自己的角度写,写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但心里还是惦记着。几个月后,我换了一个身份,还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但‘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生活在工厂里的工人。这样整个写作就打开了,我一下就理解了他的生活,他面对盐湖荒凉的心境是怎样的。盐湖不再是自然景观,而是我心中的人文景观了。”
在王威廉看来,对小说创作而言,最重要的是从生活中挖掘素材,从阅读中吸取经验;但这二者其实又并不是全部,小说的复杂性应该是一种锐度,展示人性精神存在的复杂性,所以发现和创造更重要。
谈到80后作家与老一辈作家的关系时,王威廉说:“60后作家的成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文学爆炸的时代,在今天,作家、教授、诗人在文化中占的比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一种悲壮感,在个体面对写作的时候,内心应该平静下来。代际这个概念是80后出来之后产生的,然后再逆推回去,如果不用代际的概念,80后作家似乎完全被淹没在我们对上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中。”他认为,在今天从事文学职业,需要的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