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电影 >> 资讯 >> 正文
谁是好电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11月11日10:05 来源:中国艺术报 赵志伟登上了8844米的《喜马拉雅天梯》和登上6000米的《绝命海拔》 :
谁是好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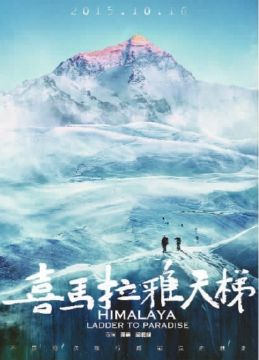 国产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海报
国产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海报 好莱坞商业大片《绝命海拔》海报
好莱坞商业大片《绝命海拔》海报2015年下半年,随着《捉妖记》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煎饼侠》 《港囧》 《夏洛特烦恼》等国产电影的大卖,中国电影市场惊喜连连,票房持续火爆。与此同时,不少纪录电影也在跃跃欲试,频频向大银幕发起冲击。这其中,有两部电影的上映特别引人注目,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部是国产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 ,另一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纪实电影《绝命海拔》 。两部电影同中有异,但因其聚焦题材的特殊性,再加上票房市场、观众口碑、媒体报道等多种因素相互纠缠,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被人拿来进行比较:究竟孰优孰劣?
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厘清的话题。在当今电影美学标准不断遭遇商业革新的语境下,说票房是硬道理未免偏激;而有众多专家学者乃至名人明星捧场的电影往往曲高和寡;豆瓣等网络评分及大众媒体的报道是否能够代表民意?一切也尚未可知。普通观众越来越看不明白电影的好与孬,看似一步之遥,实则论起来大有门道,颇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味。
好在就电影本身而言,无论《喜马拉雅天梯》和《绝命海拔》的拍摄手段是跟踪纪实也好,还是“真实再现”也罢,不过是两部影片的导演或主创人员运用不同的美学手法而已,对于买票走进影院的普通观众来说,只要电影这两道菜好吃就够了,至于其生产流程区别不过是观影前后的谈资和花絮而已,毕竟两片终其目的均剑指票房,力求市场与口碑双赢,否则何以要开足马力走进院线?因此,归根到底,两部影片能否满足目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某种程度看,在影院关灯与开灯之间的那一个半小时就早已定论,而非其他说辞。
就此而谈,首先在影片叙事上,实拍加特技制作的纪实影片《绝命海拔》比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更胜一筹,或者说更像一部电影。诚然,何为电影?见仁见智,著名导演黑泽明说终其一生都在探索电影是什么,可放眼电影诞生至今短暂的120年历史里,尽管其美学标准在不断嬗变中与时俱进,但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院线影片,核心的故事及叙事的流畅仍是必不可少的。 《绝命海拔》的故事紧紧围绕新西兰领队罗布·霍尔率领的“冒险顾问”和史考特·费雪带领的来自西雅图的“疯狂山脉”两支登山队,在攀登珠峰过程中相互竞争,又彼此帮助的内核展开,即便有大量惊心动魄的影像奇观及温暖人心的亲情、友情、爱情等细节穿插其间,始终不脱离故事内核,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结构更为贴近大众的审美接受心理。相比之下, 《喜马拉雅天梯》叙事支离破碎,故事的内核自始至终游离不定,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画面感更强的纪实影像而已。近的不说,就拿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为参照, 《喜马拉雅天梯》的叙事流畅和可看性也很是不足,甚至有青年纪录片导演看后毫不客气地指责影片构架叙事出现重大失误。
其次,虽然电影诞生于1895年,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得到世人的认可,绝不是从卢米埃尔兄弟的《水浇园丁》《工厂大门》等开始,因此,无论电影作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存在,不能仅仅立足于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或者展现影像奇观,更在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能够像其他姐妹艺术一样,通过其独特的视听技艺,直抵人类心灵深处,关切人的生命、生活及生存状态,甚至具有某种社会学、人类学意义或哲学意味等。就此观察《绝命海拔》和《喜马拉雅天梯》,前者剧情张力十足,丰富的情节处处彰显人文关怀,虽有美式煽情之嫌,却是《喜马拉雅天梯》之不足。当然,《喜马拉雅天梯》也并非不具有人文关怀,绒布寺里老喇嘛面对镜头时的无奈叹息等细节捕捉,使得影片对人类攀登珠峰商业化的叩问比《绝命海拔》更加直接,也更具历史、文化与道德的深度思辨。不过,如此就说《喜马拉雅天梯》比《绝命海拔》在深层开掘上更富思索意味,言之尚早,毕竟《绝命海拔》所讲述的登山故事从开篇到结局并未避讳这种商业化行为及利益角逐,而且直面故事主角,探寻个体攀登珠峰的理由,从这一点来看,较之《喜马拉雅天梯》又更为纯粹,将商业进行到底。两相比较,虽各有千秋,但均显不足,特别是两部影片的“局外人”视角,不能代替“局内人”的诉求,这种根源于开机之始的局限性,无论如何难以弥补。相比之下,由云南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摄制的纪录片《触碰神灵——记卡瓦博格峰山难》虽非聚焦珠峰,且故事性架构更为有限,但力透纸背的诉说与批判意识却令人警醒,颇为难得。
诚然,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审美差异不可否认。 《绝命海拔》无论如何“真实再现” ,即使他们克服极限上到了6000米,也不如《喜马拉雅天梯》把摄影机直接架上海拔8844米的珠峰峰顶拍摄更具真实存在感,也更具诱惑和唯一,这也正是《喜马拉雅天梯》作为纪录电影的最大卖点。但文化价值及技术含量果真无以匹敌、天下第一吗?制作者恐怕要三思。
最后,相比《绝命海拔》 ,影片《喜马拉雅天梯》满屏赤裸裸的商业广告植入,说有欠诚意未免过重,但既想好又想巧,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固然是制作经费有限,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当前国内影视制作不良生态在纪录片领域的蔓延,但终究处理得不够妥当,沦为一部虽是可敬却不可爱之作,当不能责怪观众过于苛刻。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