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电影 >> 酷评 >> 正文
《乡村里的中国》: 摇摆的乡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26日07:39 来源:北京日报 童凯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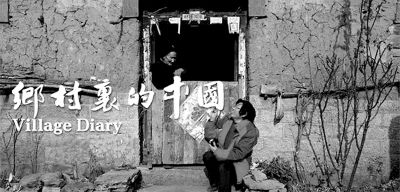
近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4年度表彰大会入围名单公布,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获得年度导演和年度影片两项入围,这是21部入围影片中唯一一部纪录片,颇受瞩目。
以最大的诚恳
《乡村里的中国》,名字实在不讨喜,题目大而且拙,在洋溢着爆米花和巧克力糖霜味儿的影院里,它显得那样“水土不服”,况且又是纪录片,很容易让来此消遣娱乐的人群敬而远之。但这片子确实让我惊喜,私人打分甚至高于一年中绝大多数国产剧情片。只是要来认真评说它,却难免有些摇摆。
影片锚定山东沂蒙山区的杓峪村,整整一年无间歇跟拍。硬桥硬马,质朴平达,没有一点花招与虚饰,也全无作者纪录片容易流入的绝望与沉闷,这是它最迥异时俗的地方:仅以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就可以让观众从头笑到尾哭到尾;感慨有之,沉重有之,而看到最后心底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激。尽管全片没有一句旁白,但在春去秋来的时令流转间,在稼穑社庆、婚丧嫁娶的农事琐记里,仍可感受到残存于乡土中国的自然之美与淳朴人情。它温润了过于残酷的现实,使人在苦难中犹能看到斯土斯民明亮开豁的一面。这与导演焦波出身山东农村有关,他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感情,以及摄影记者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可以在沂蒙山区跑遍十几个村庄,最终选定一个相对理想的标本,并以最大的诚恳,为不断被现代产业围剿和重构的乡村,留下了一组无奈却又豁达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群像。
难以捕捉的私密情境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流行,无论是出自本土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抑或美国人何伟写下的《寻路中国》,都在坊间热动一时。从纪实角度而言,文字与影像各有所长,譬如许多现实中的私密情境,捕捉下来极出彩,写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即可做到,但摄像机镜头往往很难介入。《乡村里的中国》则突破了这一媒介工具上的短板,过去不敢想像能随便开机的场景,譬如村民干仗、夫妻斗嘴、村官的苦闷与发泄……都给剧组拍到了,而且拍得从容不迫,沉稳得当。有了这种几无间隔的近距离拍摄,纪录片的品质一下结实了许多,大到乡村的政治脉络,小到村民的悲笑呼吸,都活生生放大在黑暗中的银幕上,直击心肺。且因为有细腻的体察,平视的尊重,每个镜头都像刚从地里拔出的萝卜,带着原汁原味的土腥与鲜涩,它们似在呼召:看哪!这些人,他们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
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全新而陌生的观影体验,它所能激起的联想大概远远超出了导演的初衷。我用“乡愁”来做题目,也自觉口齿不清,因乡愁一词似早已被用坏了,近乎一种发甜的、远距离的、聊以自慰的闲愁;而本片的创作者虽是眼睛在摄影机后面,身心却与乡村同在,这样的血肉相连,使他的镜头无论怎样摆,随时会发现农耕文明下的人情风物之美,又能体会到农民内心对土地爱恨交织的真实痛感。当下,有些地方的城市化运动许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市民阶层与土地的关系早已隔膜,连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对土地的感情逐渐淡漠,仿佛土地是没有前途的,是亟须摆脱、离得越远越好的梦魇。有些知识人更抵制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理由是大量乡村早已破败,“现代化”的命题下,没有回头路可走。《乡村里的中国》未必能回应以上声音,却呈现出现实生活蕴含的丰富面相。譬如,片中全部采用村民的原声对白结构剧情,土生土长的淄博方言有着不可思议的诙谐和鲜活,职业编剧憋破脑壳也想不出的台词,在人家那里像掐豆荚一样随掐随有。你会爆笑,会叫绝,甚至反观自己平日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倒像是人工塑料制成的,贫乏、单一,没有生命力。
“精神”也要吃饭
记得贾平凹为小说《秦腔》和《高兴》写的后记中,曾极度纠结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即想尽可能地记录三十年间在故乡已经消绝了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农耕用具。贾平凹出身陕西商州,今也还是三秦最贫困的地方之一,用他的说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一开会黑乎乎一片土皂衣裤。就是这样的土地上“竟也出了那么多能人,有善制木的,能泥塑的,精通胡琴的,说评书的,学绘画的,懂《易经》的”……而纪录片里杓峪村的“才人”杜深忠,就是从这样的世界里浮现于银幕上的一个。片子一开始,初日照进农户一隅,杜深忠蹲踞于阳光下,用毛笔蘸水在自家门厅地上书写《道德经》,这是个兼具智慧和诗意的隐喻——一个身板瘠薄、干农活不灵、进城打工又掉了13颗牙的农民,却关心国事,深爱文学和音乐,在村民看来,文化虽好,毕竟填不饱肚子。杜深忠则坚持“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饭,‘精神’也要吃饭”,而他的精神食粮,并不是果树栽培、畜禽养殖一类的实用性读物,而是纯为审美愉悦的“无用之用”。老子哲学以守常抱朴、复归其根为谛旨,意即在生存上淡然处之,存在方显得诗意盎然,只是这样的诗意对于杜深忠而言显得何等艰难!为供两个孩子上学掏空了家底,至今还欠债两千余元,饶是如此,他仍要挤出钱来背着妻子去买琵琶,仍对文学怀有梦想。杜深忠是农民中的“异类”,又是影片的灵魂,从他身上,许多人或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能想到,以乡土中国之大,每个村庄可能都有一个杜深忠;他们是散落于草野的布衣匹夫,识文断字,天赋才慧,身处贫贱而心怀高远。这是一个民族潜蓄的文化底气,以民间的水深浪阔,这样的底气历来在草野中代继有人,而当草野无“草”之后,这样的底气是否还能存续?
乡村,请消逝得慢一点
《乡村里的中国》只是一部“命题作文”,焦波要完成这一作文,他想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尽,我今想代他说下去,也好不为难。镜头下杓峪村虽然让人想往,但包括杜深忠的儿子在内,考出去的农家子弟多已难再回返家乡,何况大量的传统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年轻人一脚踏进大城市,转瞬就会成为异乡人,现代化带来了物质丰裕与便利,但诗意的空间更趋逼仄,堵车、雾霾、高房价与消费社会、虚拟社交一起,将上班族骗进一种宛如格式化的生活。而乡村与城市又岂好简单割裂,在南水都要北调的今天,若是源头的清水染了毒,乡村的农地变荒敝,玻璃幕墙装点下的水泥丛林又能光鲜多久?
但这不是我们独自面对的命题,住在豪宅里的西方人早经说过,现代人是无根的,是没有家乡的。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摄影师阮义忠便走遍宝岛,创作了摄影集《人与土地》,他想借此留住人性的美好,包含“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摇摆的乡愁,进退失据的乡愁,一部纪录片能做的,不仅仅是记刻与乡愁有关的、正在消逝的人情与风景,它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生命的来处。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