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寓言 >> 新闻 >> 正文
作为“当代上海寓言”的《繁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1月21日16: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曾军《繁花》是一部地道的“上海味”的小说,它不仅是由 上海人(《上海文学》副主编金宇澄)用上海话(采用的是地道的上海话,正式出版之后适当做了部分的普通话的处理)写的上海故事(从1960年代直到 1990年代的上海社会变迁);而且其首发之地是以“上海人讲自家身边的故事”为宗旨的“弄堂网”,其正式发表的刊物也是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收获》杂志,
随后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文化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各地城市文化“千城一面”、大众传播媒介无所不在、网络文学生产急剧扩张的今天,《繁花》从 容应对这些被认为导致文化同质化、文学平面化因素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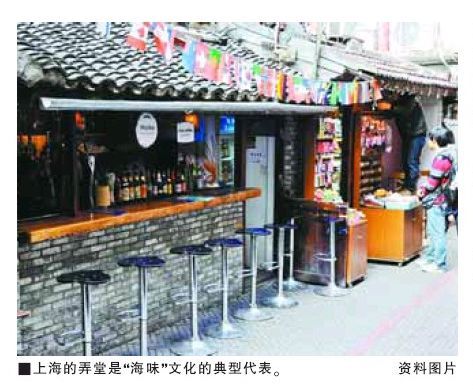
“沪生”体现上海市民意识
《繁花》写的是沪生及其好朋友阿宝、小毛们从童年直到中老年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并以此为中心,围绕其亲人、同学、恋人、朋友、同事等的人际交往,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社会各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
沪生出身革命家庭,其父母积极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但最终在政治事件中受到冲击;阿宝作为大资产阶级的后代,亲眼目睹了祖父家的变故,而自己也
由一个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转变为接受社会改造的工人阶级;小毛则一直处于工人阶级地位,看似平稳,实则艰辛,空有一身功夫,最终孤老病亡。在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沪生转型成了律师,阿宝经商成为“宝总”,而小毛则一直还是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版《繁花》中,最初确定的主人公是“腻先生”,后更名为“沪源”(其中“沪生”是沪源的哥哥),但到了《收获》杂志的期刊版中,作
者最终确定“沪生”作为主人公,而其哥哥更名为“沪民”。所谓“沪生”,意指“上海所生”,“沪民”当然也是“上海之民”,完全贴合小说展现上海20世纪 50年代末到90年代上海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旨。
在小说中,沪生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与新中国同岁(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出生)的一个普通上海市民,无论是其出身背景,还是人生经历,都远没有《海上花列传》通过烟花女子观察上自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式的“传奇”,也没有《子夜》、《上海的早晨》那样直接将视角聚焦于上海社会变迁的重要人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没落)那样的“史诗”,同样也没有像《长恨歌》中,王安忆直接以作家兼叙述者的口吻直接将王绮遥等同于“弄堂”、“闺阁”、“上海”的那种“隐喻”。《繁花》中的“沪生”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风云际会,但他们并没有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以英雄的形象置于精神高地的顶点。恰恰相反,他们更多是以随波逐流的方式被裹挟到大时代的洪流中,没能够对历史和时代产生重要的影响,只能自我适应、自我调整,于逍遥中获得暂时的喘息,于被动中寻找生存的希望。这也就意味着,“沪生”在成为“当代上海的寓言”的过程中,“上海市民意识”成为《繁花》的基本定位。
从陌生人世界到“熟人社会”
整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沪生却并没有充分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他更像一个参与者、旁观者的角色,参与到他的同学、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之中。以沪生为中心,人物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男性,即沪生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阿宝、小毛、陶陶,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康总、徐总、苏安等。另一组则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在他们周围的女性:蓓蒂、姝华、银凤、小珍、春香、兰兰、雪芝、菊芬、白萍、梅瑞、潘静、汪小姐、李李、小琴等。她们或是“沪生们”童年的邻居、玩伴,或是他们长大成年之后的恋人(或者是朋友的恋人)、同事。
透过各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难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繁花》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熟人社会”的上海叙事。作为“大城市”的上海人,并不像有的城市社会学所说的,“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因此,在许多城市文学中,“陌生人世界”往往成为观察城市、反思城市的视角。但《繁花》花了数十年的笔墨,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上海人(或者再普泛一些,所有的“城市人”都具有这个特点)始终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其中亲戚、邻里关系构成了市民交往的核心,其次是恋爱和工作的交往构成了其交往圈的外围,再次才是陌生人世界。这个陌生人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关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而一旦与人发生关系,陌生人也就会转化为熟人。这就是《繁花》为我们确立的“城市人‘陌生/熟识’的辩证法”。
小说中有两个场景最具有代表性:其一是阿宝全家搬到曹杨新村的“两万户”,一下子被置于一个陌生人世界。但很快,他们便建立起新的邻里关系,彼此开始尝试和睦相处、互帮互助起来。其二是梅瑞在与康总的交往中,频繁接触生意场上的各色人等,到第二十八章梅瑞筹备大型恳谈会时,与梅瑞有关的康总、李李、沪生、阿宝等均被邀请,总人数近四十桌。小说详细开列了各桌的排位,完全就是根据关系亲疏、彼此间的远近进行了组合。这份座次表正是以梅瑞为中心的上海熟人关系网。从陌生人世界到熟人社会的转变并不是上海城市市民自身的“熟悉化”过程,而是文艺作品通过想象再现的方式,对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建立在与“乡土社会”对立的基础上所强化的对城市片面认知的纠正。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展开“沪生”们的精神世界——上海这座城市。小说究竟是如何塑造“上海人”及其市民意识的?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的描述中,上海一方面被指认为“移民城市”,这当然基于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大量城市移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排外”意识最强的城市,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影响下,逐步形成“上海人”意识,所谓“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之争即此。但是《繁花》中所塑造的“上海人”,却是一个并没有明显“排外”意识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繁花》的叙事重心并不指向是否“排外”,而是更加侧重于“上海人讲述上海自己的故事”的这种相对封闭的叙事系统。而这一来源于“弄堂网”的宗旨,恰恰成为金宇澄《繁花》重新讲述“当代上海寓言”的视角。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