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电影 >> 酷评 >> 正文
为《黄金时代》一辩(李摩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3日07:59 来源:北京日报 李摩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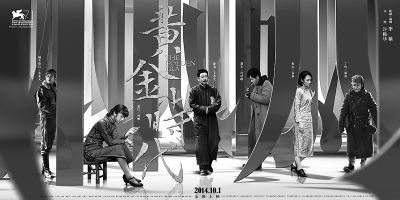 《黄金时代》海报
《黄金时代》海报当此《黄金时代》“票房惨败”、种种高端挑剔汪洋恣肆之际,作为受其打动的观众一枚,我要没眼色地为自己受到的打动一辩。
当然此片不是没毛病。个人感觉,毛病不少也不小。最扎眼的是关于鲁迅的段落。作为一部写实电影,把鲁迅私下与友人聚会的神气拍得那样端“装”肃杀,不能不说是败笔。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开篇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底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关于他喜欢说笑的记述,其实有许多。当然他心底的哀伤和愤懑亦多。这是他个性的张力。影片没能把这股幽默而忧愤的张力呈现出来,观众看到的仍是习见的那个冷肃的老头,虽然内容截然相反——以前是刻板的革命导师,现在,他刻板地向萧红们牢骚着“左联”内部的嘁嘁喳喳。
此外呢,萧军太甜软,许广平太老迈,胡风太官气——演员的选择是否意味着导演对这几个历史人物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这不妨碍我觉得《黄金时代》是部好电影。一部充满丰盛的写实主义细节的巴洛克式电影。巴洛克式的“繁琐”写实使影片不能主观直接地刻骨画髓,却也成全了它从纷繁表象中节制地暗示本质。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建议读者每读一部书之前,放下所有的知识武装,把先入之见清空归零,在阅读中与作品的本真相遇;若预先带上所有的储备和成见,则对作品的判断未免扭曲失真,也难有所得。此经验也适合观影。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需先认清该片本身“想做什么”,这个“想”有何价值,以及它“做”得如何。对一部传记性的文艺片而言,观众尤需先尽此义务,暂时搁置自己对人物原型的了解和对照——诸如他/她“本来”怎样,“应该”怎样,却“没能”怎样的标准答案——先了解创作者的“语法”,以及这语法是否构筑了一个合乎其自身比例和韵律的世界。艺术之为艺术,即因它无标准答案,而承认创作者的个性语法正是拓展形式与意义之疆界的利器。
我以为编剧李樯和导演许鞍华在《黄金时代》里想做的,不只是复原萧红和她的时代。它想借助这“复原”,说出“智识女性之灵肉困境”的真实寓言。一如萧红所遭遇的: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一无所有的女子必面临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想想鲁迅所说:娜拉出走后,等着她的只有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在由男性话语建构评判尺度的智识领域,智识女性则面临着否定自我的价值困境(想想萧军对萧红写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在历史转折的当口,这智识女子则面临着选择困境,这困境超越了她的性别,而获得普遍的深意——是放弃自我,追随激进大潮投身时代洪炉,还是守护自我的天才,用孤独的书写,为人类留下一片个体的宇宙?
影片工笔呈现了萧红在此困境中的抉择及其状态,而非这抉择的前因后果——它明确拒绝了因果律叙事,而运用跳跃式的状态叙事。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以这种跳跃性的素材选择,暗示作者的历史观、生命观与价值观。萧红生平凄苦,影片却以“二”写苦,以笑写哀,以吃写饿,以依偎写无所依偎……总之,以轻写重,反更见其凄苦,也超越了凄苦,触到她凄苦之上、生命之中的自由意志。正是与这意志相伴而生的天才,“越轨的笔致”,才有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萧红。这意志也有一种自明的本能,使她抽身于时代主流之外,独自飘零。这是丁玲对她自感优越之处,也是她高于丁玲之处。
演员对着镜头叙述,这种来自戏剧的间离手法,伯格曼在电影里玩得最早最熟。台词不时和镜头语言相脱离,借助影像扩展台词之外的意蕴,侯麦最精此道。这两招经典的电影手法,在《黄金时代》中用到极致,使它得以彻底脱离因果律的线性叙事,以视角、时空、状态的纷繁变化取代快节奏情节演变的单一悬念,而获得了别样丰盛的电影悬念。影片营造伪纪录片的形式感,并不意味着它承诺“按照纪录片形式叙事”,而是提醒观众:一切都是假定的,即使历史证人的证词,现在时而主观、时而客观的镜头叙事,都是假定的。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你自身的感受。
因此,你能感到影片弹拨出的历史余响,与当下的响声是同质的——一样的困窘,一样的欲望,一样的恋爱,一样的出轨,一样的从屌丝到成名,一样的从心动到心碎,一样的从忍耐到离开,一样的从热闹到冷寂,一样的从生到死……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对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质感以及人物灵魂的景深,电影谨守着它的忠实,并不因当下精神的简陋,而去简化历史灵魂的繁复。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