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洪子诚:“文学史”这个“世纪迷思”的病症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洪子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16日10:07 来源:深圳商报 魏沛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洪子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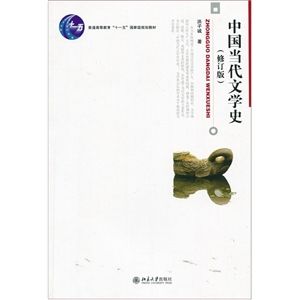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著《当代文学的概念》。
▲洪子诚著《当代文学的概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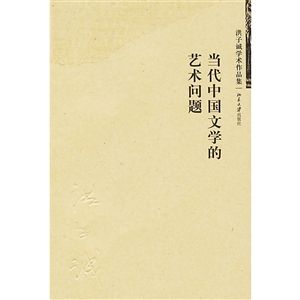 ▲洪子诚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
▲洪子诚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 ▲洪子诚著《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洪子诚著《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修订版)》。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修订版)》。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奠基者与开创者,洪子诚学识渊博而严谨,著作等身而低调,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这位从潮汕揭阳走出去的优秀学者,“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没有受到什么惩处,没有得过什么奖赏”,如今年逾古稀,仍然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洪子诚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正如有学者指出,他被学界关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性和经典性,一是其个人‘边缘性’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被部分学者戏称为“学界的红宝书”,足见其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不要妄自菲薄
目前,洪子诚正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邮件专访时,洪子诚强调,“我很不能同意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著述有一种不加分析的崇拜和贬低国内学者的现象,有一些学者就靠这个吃饭,提高自己名声。”
针对国内有些学者盲目批评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他发出质疑:“其实,像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吴福辉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去年刚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 》等,水平都是很高的。我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在荷兰莱顿的布里尔出版社(Brill)出版了英文版。布里尔是很有权威性的学术出版社。去年,日本东方书店出了日文版,明年,俄国的东方出版中心还要出俄文版。为什么我们国内学者对待自己就那么苛刻呢?”
在洪子诚看来,“现当代文学学者,有许多很优秀,并不比王德威、顾彬他们差,像钱理群、陈平原、吴福辉、赵园、孙郁、范伯群、陈思和等等。完全不要妄自菲薄。”
此外,谈及当代人写史的问题,洪子诚说:“当代人写史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总是在说。奇怪的是,没有人指责朱自清、周作人在新文学诞生只有十多年的时候就写类似新文学史的论著不应该,可是,在当代文学已经过了30、40、60年的时候,还说距离时间太近,还说不能写史。多少年才‘不近’啊?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缺陷自然存在,问题多多,但当代人的讲述,也有隔代、隔隔代人讲述不能代替的方面存在。”
至于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选择与处理,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写道:“表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无法回避的价值评析尺度……一方面,会更注意对某一作品,某一体裁、样式,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价值判断并不能取消
《文化广场》: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作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也就是说您不是梳理“文学中的历史”,而是探寻“历史中的文学”,那么对于文学史,您是否更倾重“历史性”?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者都是在面对、处理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史问题。上世纪9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处理文学观念、题材、形态、样式、风格的变异的时代历史依据上,在探讨“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上,以及将“当代文学”不是作为批判对象,而是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结构加以辨析上,还有很大拓展空间。这就是我的“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判断其实并不能取消,不能真正搁置。我只是降低它的地位,在表达上缓和其紧张度而已。
《文化广场》:当代文学史书写一直面临着尴尬的状态,不少学者都强调需要勇敢与力度。刘再复先生也认为,若从1949年至今65年,以七十年代末为分界点,“前半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失败的文学史”,“倘若真的敢于‘重写’,那么,对于前半期就得敢于触犯许多戒律”。不知您当时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勇敢”来源于哪里?
洪子诚:写当代文学史时,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勇敢。也不认为指出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失败”需要多大勇气(虽然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大)。我的当代文学史书出版的时候,表扬的人说是“寸铁杀人”、“老吏断狱”,批评的说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表扬是太夸张承受不起,我也不是有许多诡计的人;而批评我也不想承认,虽说“胆小怕事”确是我的性格。退一步说,设想我变得“勇敢”起来了,文学史我还是会这样写。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戒律、禁忌是存在的,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去处理,但不要过于夸大。我的书的缺陷属于另一层面,也就是因学识、经验、才情的限制,导致面对“现实脉络的纷繁”与“种种权力格局的纠缠”(戴锦华语)时,在把握上存在缺失。
“理想的文学史格局”不可能出现
《文化广场》:26年前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对于复杂时代篡写的文学史均有深刻的切肤之感,故及时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希望建构新的理想的文学史格局。而在这26年间,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如雨后春笋出现,尽管数量突现,但质量似乎并不乐观。您是如何看待“重写”这个问题?如今文学史书写是否还存在困境和难题?
洪子诚:文学史的重写总是在进行。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口号,组织的专栏,表达了当年文学史突破的普遍诉求,具有积极意义和很大影响。自然,这一口号、诉求存在的缺陷、偏颇,90年代以来也不断受到反思。反思是必需的,但我不大同意这种反思导致对“重写文学史”在当年和今天的意义的全盘否定。
至于这些年出版的大量现当代文学史著作,质量,水平自然参差不齐,高低互见。“理想的文学史格局”是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但也无须那么“不乐观”。或许也有理由可以审慎地“乐观”一下?这二三十年来的多种文学史著作,不是都乏善可陈;不要总是唯“古”唯“洋”是崇。
《文化广场》:近十多年来,海外学者也寻找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新出路,出现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著)等,您关注过这些文学史著述吗?在书写实质上究竟是否够称得上“突破”?
洪子诚:“剑桥”、“哥伦比亚”等文学史,名字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当然,它们水平的保证主要来自撰述者优秀的学术品格、修养。因为知识、视野、处境、才情等与国内学者的差异,这些著作确有许多令人兴奋的布局和新见,相对国内的同类著述而言,这也可以说是“突破”。但国内学者有质量的著述,在许多方面也是它们难以企及的。
边界总是在不断移动之中
《文化广场》:对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选择和分析,除了体现文学史观,也表达了编写者的价值诉求。而像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再到目前所见的钱穆《中国文学史》讲义等,他们更希望通过写史来寻求安身立命之处,寄托传统文化情怀,但在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情怀”似乎难以再见,不知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之间出现的“断裂”?
洪子诚:“文革”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谁谁是五百年才出一个。因此大家只有膜拜。同样,拿这些史著经典来衡量,我们确实抬不起头来。这是一种类乎“极致”的目标吧。如果可以降低一下标尺,那么,我要说的是,在你指出的确实存在的问题之下,也还是可以发现有安身立命、文化情怀寄托的著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情和耐心去发现我们周围的创造?
《文化广场》:沈从文的后半生与文学创作无缘,但他的书信、日记依然细致表达了对生活、文学和社会的理解,研究价值极大。然而,在目前所见的文学史里,几乎很少见到有学者重视书信、日记、读书笔记等。再如您于2011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个人文学史”,您如何看待书信、日记、读书札记此类史料对于文学史编写的作用?
洪子诚:“表达了对生活、文学和社会的理解,研究价值极大”的书信、日记、读书札记等文字,在文学史写作中,是当做研究对象的“文学”,还是当做研究文学的“史料”,这个难以一概而论,需要文学史写作者去判断。“文学”是个历史概念,边界总是在不断移动(扩张,渗透)之中,我赞成不墨守成规。《傅雷家书》不是写进文学史了?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写入沈从文的日记、书信,张中晓的笔记。不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这一处理方式在学界也有争议。
《文化广场》:在史料运用问题上,记得谢泳说过“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不能光有公共生活,必须要有私人生活”,为此他以鲁迅、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为例,说明社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了解得愈全面愈完整,愈有利于文学史研究者深入理解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而,“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作品间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一步”,不知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洪子诚:谢泳先生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处于同一时代、相似社会环境中的不同作家,他们个人经历、生活情况其实差异极大。他们的私人生活,婚姻、家庭、经历等情况,经济生活条件,包括居住地域环境等等,对他们的性格、创作都不是无关紧要。我们的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确实这方面关注很不够。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阻碍对他们作品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史写得没有情趣,味同嚼蜡:我的文学史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计划是“告别文学史”
《文化广场》:对于郭敬明、韩寒这些新一代作家,如果按照“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务”这种说法,您觉得可以把他们写入文学史了吗?如果可以,怎样在文学史中介绍并评价他们的价值和地位?
洪子诚:对待时间最靠近的作家作品,文学史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所谓“经典化”的方法,另一种是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来描述,“立此存照”吧。如果你有胆识,有魄力,那你可以为他们(作家)、它们(作品)做文学史的定位,就像19世纪俄国别林斯基对待普希金、果戈里那样。如果拿不定主意,对自己的判断力有怀疑(对批评家、文学史家来说,这类乎患有绝症),作为现象描述其影响和不同评价,也未尝不可。如果我来处理的话,大概会选择后一种方式。
《文化广场》:当下也有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质疑“文学史”存在的意义,认为“史”和“文学”本末倒置,不如编好的文学选本,让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这一点在大陆学者身上最明显,不少学者都经历了一个从“重写”到“淡出”的过程,像王晓明教授的研究重心已转在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上。在您看来,学界这么多年对文学史书写喋喋不休,其实是否高估了“文学史”这一著述的价值?如果抽掉文学史,会影响我们理解文学吗?
洪子诚:王晓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精力转向文化研究,主要是他认为文化研究更能有效触及、回应现实紧要问题,这不是“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文学”转向“文化”。如今社会仍然热衷于讨论 “重写文学史”,其实也是不自觉患有高估“文学史”的这个“世纪迷思”病症,也在推动这个有关文学史的“喋喋不休”。这种文学史热,肯定是不正常现象,但是,在目前的教育、学术、出版体制下,改变这个现象也不大容易。确实,认真编好的选本,是另一种、有时是更重要的文学史书写。我和几位先生(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花了两年时间编选《百年新诗选》(今年可以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也是表现了重视选本的意图。但也不要因此就笼统否定文学史的价值。这些年,各种各样的“选本”出得还少吗?文学就“回归自身”,就井然有序了吗?那也不一定。
《文化广场》:可以请您透露介绍一下目前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吗?
洪子诚: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告别文学史”。因为年龄、精力关系,大概只能写一点随笔性质的小文章。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