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关于《日头》和“农民三部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15日09:00 来源:河北日报 张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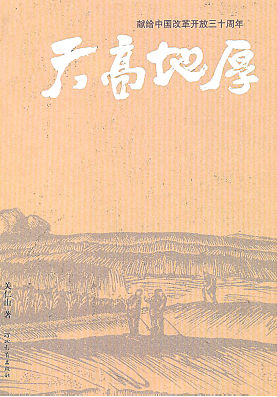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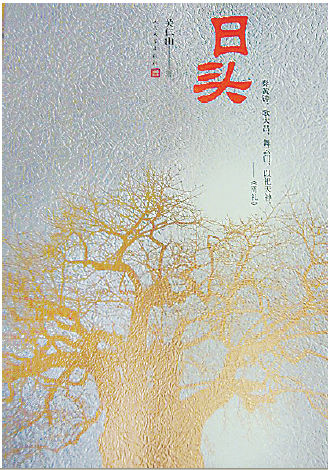
近日,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8月27日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新书首发式。作为关仁山“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该书以现代中国北方农村为背景,对当下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度探寻和思考。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一部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力作,它将传统写实与乡村魔幻巧妙融合,书写了传统农耕文明逐渐瓦解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关注和书写了改革开放中的乡土中国,富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日前,本报记者在京与关仁山就《日头》及其“农民三部曲”展开了一场对话。
《麦河》落选茅盾文学奖
记者:2011年夏,《麦河》曾经参与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虽然顺利入围前十名,但最终还是以微弱劣势与茅奖失之交臂。请问,这种评选结果,是否打扰了您的写作心态与创作方向?此后,您如何安排自身的文学创作呢?
关仁山:这是一个敏感话题,还应该坦诚面对。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作品获大奖,但是,评奖就像体育比赛,注定有人得冠军,有人被淘汰,而且原因很复杂,作家不能为了奖而创作,这涉及写作“为了谁”的问题。我就想,永生永世为那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写作,尽管他们不买我的书。可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天高地厚》时,收到贵州农民从田间地头寄来的鼓励信,这种奖赏更令人欣慰。那年《麦河》落选,我觉得,还是作品写得不够好。我马上调整好心态,继续写《日头》的创作大纲,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完成了“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日头》。
记者:作为“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头》这部小说对《麦河》有怎样的参照和突破?在读者阅读方面抱有哪些期待?同时,您又遇到了哪些美中不足的细节呢?
关仁山:说到《麦河》,它真是这部《日头》的参照。一个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上,还是艺术创新上,都必须对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否则就没有写作的意义。《麦河》是以一个唱“乐亭大鼓”的盲人视角写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重点写了今天的土地流转。土地是小说的灵魂。《日头》选择了两个人交叉叙述,小说中有两个“我”,即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敲钟人老轸头,一个是天上的毛嘎子。两种语气叙述,前者在地上客观参与,一个在天空抒情议论,这肯定是一个挑战。其难度是实和虚的处理,弄不好会让读者以为是两部小说,产生割裂感,无法有机地成为一体,成为故弄玄虚的败笔。毛嘎子被赋予了一个特殊能力,他飞回村里,只能落在树林里的一棵菩提树上,老轸头与毛嘎子之间能够对话,智者的对话,众人听不见,这让小说产生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让哲理思考自然呈现。
因为老轸头是一个老农民的叙述,必然口语化,本土化,他亲历日头村的变迁,一方面是权桑麻的亲家,一方面又与金沐灶有着特殊关系,可以说是“准岳父”。他是敲钟人,身份决定了故事的传奇性和野逸风格。毛嘎子的语调优美抒情,长长的句式,让其富有哲思和美感。因为我们通常把精神和心灵的愉悦称为美感。有了这样的审美目标,这个天上的叙述只能是精神或灵魂叙述了。即便是昙花一现的幻影,也要出现生命美感体验,那是忧患之美,纯洁和高尚之美。描述的故事不再是目的,他只是借助对故乡的怀念和质疑,对人类的生存发问,是想让作品来抒发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心声,蕴含其中的古怪的激情和精神疑难,让读者体悟鲜活澎湃的生命感。毛嘎子还有一些特异功能,他有在天上的云顶,根据星宿的闪光给人解梦的功能。实际上给予了他全知全能的视角,对老轸头讲述故事的局限做了补充。
当然,这部作品也难免美中不足,就是想象力没有尽情发挥,毛嘎子应该思考人类的命运。
记者:您的“农民三部曲”,依次包括《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请问这三部长篇小说在艺术题材和小说创作上,具备哪些异同之处?在具体的创作当中,您碰到了哪些较难解决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仁山:我创作《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时,对农村安抚灵魂的道路描述是单向的,在《天高地厚》这部小说中,开始追问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但不能全景,难以壮阔,叫人不满足。后来,我把叙事放在尽量宏大的背景上,开始了多向度的写作,开始更为复杂、更为深入、更为超拔地讲述冀东平原的动人故事。“农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的东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
《日头》是一座“分水岭”
记者:我个人认为,《日头》是您小说创作的“分水岭”。所谓“分水岭”,就是在《天高地厚》和《麦河》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仁山:《日头》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这个提法很新鲜。我想,如果说《日头》是我的重要作品更为恰当吧。
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总按领导的意思写,要写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多了一些,这一篇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要加强批判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这部作品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写农民的书,怎样才能做得好?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日头》跳出了农民种地打粮的传统模式,抛弃了原来用过的精神资源,带着忧患意识去写一种新的形态。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提纲阶段,不断对自己说: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要面对良心说真话,以良心的名义。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大胆地探索一些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说《日头》是我小说创作“分水岭”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创作,可能会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记者:创作《日头》这部小说前后耗费了您多长的时间?其间写作状态如何?在艺术上的探索表现在什么地方?
关仁山:这部小说从搜集素材开始,到构思,到写作初稿,三遍大改,共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写作过程很痛苦,其间,确实出现过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这是不够的,作家要超越现实。显然,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异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诡秘和神奇中回归常人,回归常理。靠什么?魔幻是我所偏爱的手段之一。一提到魔幻,我们往往就想到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别是想到《百年孤独》,但是,我所要做的是让中国式的魔幻自然地走进作品。从《天高地厚》的蝙蝠开始,到《麦河》中的盲人与鬼魂对话,再到《日头》里神话传说中的红嘴乌鸦和古槐流血,这些都是冀东平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红嘴乌鸦,我在迁西的景忠山上亲眼见到过。
好的小说家除写作技巧之外,还要学很多东西,比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谣和民俗等,这对丰富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很重要。仅有传说还不够,一部厚重的作品必须要有文化的提升。小说的文化气息,需要“国学”根底作支撑,我去北大听过国学老师讲课,还学习过基督教的知识。当然,文学作品表现的文化不能单一,应让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神秘文化等交织在一起。
记者: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文学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与国外的作家作品相比,中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文化意识缺乏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当代作家来说,究竟应该怎样弥补文史缺憾,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投入到创作之中呢?
关仁山:好小说应该是写文化。说到文化,我自然先想到燕赵文化,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
对于文化,乐观与悲观,都不是简单的判断。面对乡村文化的崩溃,金沐灶从药王庙的道士杜伯儒那里接受了道家文化,但是,刻骨铭心刻在他心底的还是佛教文化。他母亲信奉佛教,他的父亲和爷爷,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但是他父亲却死在天启大钟前,他随身带着沾着他父亲血液的拓片《金刚经》。佛家讲“因果”,金沐灶身上的宽容、大爱得益于佛教更多一些,但是,道家、佛家和儒家以及后来槐儿带来的《圣经》,几乎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其实,宗教在入口处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最后都归结于善和爱。你感觉金沐灶完美了一些,因为他寄托了我的理想。但是,从故事中还是能看到我对他的不满,对他还是有批判的。比如,他整合宗教的荒唐,他的某些偏激,他的鲁莽,他的绝望。他把轸木撅折一半扔向天空,一半扔到河里,最终悲壮地消失,这些细节说明他绝望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向往。他注定是这样的命运,他的来与他的去,建立在模糊浑浊上,是一种自然生长……
“农民三部曲”与现实主义创作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为主,身为作家,您为什么像农民种粮一样,坚守农村题材的写作?
关仁山:我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有浓厚的兴趣。农村题材的经典著作太多了,如《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人们很难逾越。不过,如今农村题材小说,明显衰弱了,就像一穗“老玉米”,很难啃出新意来。我感觉,在这篇变迁的土地上,创作还能够冲破旧有模式,依靠新鲜的生活,书写农民的命运史和精神史。对于现实主义,有人强调它的批判功能,批判功能的确很重要,但是批判功能不能简化生活的复杂性。我们呼唤一种开放式的现实主义,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还有概括功能、典型人物塑造、叙事的综合能力等等。
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记中说过: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生存。我写农民的小说出版后,赢得了一些赞誉,也听到一些批评。把我划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特别是写当代农民的作家行列,我感觉没什么不好。
记者:面对现实乡村,作家很痛苦,原因是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找不到与今天大众的精神连接点。请问,旧有的传统经验还可不可以用?小情感、小圈子是不是可靠?是否会遮蔽更广阔、更鲜活的世界?
关仁山:文学本身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在克服困难、突破自我、突破前人中行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要想全景深入地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不可能达到目的,就必须纵横交织地全面体验生活。
《日头》区别于上两部作品的最重要内容,是两个人物形象的确立。权桑麻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权桑麻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儿子权国金身上,也象征着权桑麻专制体制的实质性延续,改革的路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农民问题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
记者:在农村题材这个范畴,国内作家的整体状况如何?您如何适应这种“各领风骚”的创作环境?此外,河北作家存在哪些普遍性的不足?
关仁山:农村题材小说划分已经不科学了,有人说,把农村小说写成不像农村小说了,那小说就成功了。辩证地看,也有一定道理,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是减少农民,少数现代农民留在土地搞现代农业。在城镇化潮流中,大量农民进城,农村小说与城市小说也悄悄融合。中国有写农村题材小说的重镇如陕西、山西和山东等,东北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深受老百姓喜爱。河北作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是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我们的作家有生活根基,有些青年作家,已经培育起了艺术创新的自觉,比如,继“三驾马车”之后,文坛又涌现出“河北四侠”。
我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时,我怀疑自己写长篇的能力,这个能力指的是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的力量。既然是小说,是写爱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作品深度靠思想力量。好小说最缺的不是故事,是哲学,是思想,所以必须埋下问题,浮起追问。金沐灶是个民间思想者,借助他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这样方能带领读者去思考。没有思想的手术刀,哪能剖析农民贫困的根源呢?
记者:如今,您的“农民三部曲”已经出齐,将来您还会继续关注农民的命运吗?商品社会对阅读也有冲击,农村题材受到青年读者冷落,此后,您如何规划安排自身的文学创作呢?作为省作协主席,您认为河北整体的文学创作在全国处于怎样的地位,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关仁山: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中,河北的作家胡学文、张楚和大解获奖。从这个情况看,河北的创作在全国不弱。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作力作还不多。河北作协很重视青年作家培养,近几年每年都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今年还要召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表彰成绩突出的十佳青年作家。为青年作家出版丛书,研讨他们的新作,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向青年作家倾斜。一句话,我们要为青年作家服务,为他们的好作品问世提供脱颖而出的平台。
多年来,几代青年读者一直都非常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如果我们写出好作品,青年读者也会喜欢的。如今,“农民三部曲”已经全部出版了,此后的写作却不能停止。我对自己的创作没有长远规划,适合什么就写什么。是生活感动了我,我才有激情写作。《日头》写完后,农民和土地我还会继续关注的,还要尝试写一些城市生活的小说。
《日头》节选
关仁山 著
 关仁山
关仁山 仰了脸儿瞅,雪纷纷扬扬。
雪花将古钟糊住了。古钟挂在状元槐,槐枝嘎地响了一声,不知是钟太沉,还是雪太厚。老槐树枯着,竟然没折,家雀呼啦啦飞了。灰巴巴的槐树枝,一律快活地动着,弹出雪粉。槐树下的麦秸垛也气吹似的胀起来,隐隐有些抖动。
常日溜达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也不见。
雪越下越疯了,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歇不住。雪和泥搅成一团,踩在脚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哧啦哧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紧不慢,却跌跌撞撞的,只一个孤独的影了。
我就是会讲故事的敲钟人老轸头。
我踏雪敲钟来了。我在槐树下站了好久,雪粉从枝杈上掉下来,奇怪的是这雪粉竟像烙铁一样烫人。
我开始用轸木敲钟了。
咣!咣!钟声跳着,滚着,响远了。
我叫汪长轸,是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我须发花白,脸上的褶子很深,牙掉得没剩几颗。我穿戴邋遢,却满面红光。到了这把岁数,难免有些怪异,神神道道。我种过庄稼,守过大车店,当过饲养员,杀过猪,宰过羊,卖过鸡蛋,还是村里最后一个敲钟人。在村人的印象里,我老轸头是和古钟、槐树、红嘴乌鸦、血燕连在一块儿的。尽管耳朵被钟声震木了,我还是乐意敲钟。钟声就是村里的日子。每逢节日,我就敲钟,要是赶上日月同辉的日子,村里就会出现异象,还得敲钟警示村人。眼下人人都焦虑,想钱想疯了,日子难免过得鸡飞狗跳。钟声能给人警醒,给人安详。我推着慈悲木开始敲钟,双手触摸慈悲木的一瞬间,手竟有些抖。悠扬的钟声在大雪天里响起,顺着老街荡出去,滚过大平原,爬上披霞山,满世界都是天堂的声音了。钟声的余音,野外都能听到。隆隆的声音犹如遥远的雷鸣,给小村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