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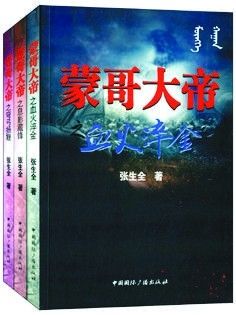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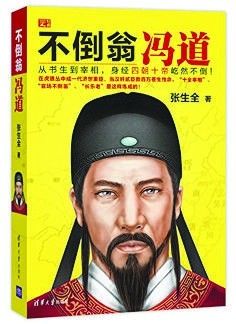
张生全,笔名三叠弓,现居眉山。在《钟山》《天涯》等刊发表小说、散文三百余万字。多篇作品入选各年度选本、大学教材及全国各地高考、中考试题。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蒙哥大帝》(三部)、《不倒翁冯道》,散文集《屋檐口下望天》《变形词》《半拍澄澈》。获华文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近期,作家张生全接连推出长篇小说《蒙哥大帝》和《不倒翁冯道》,以虚构形式重塑这两位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却因为种种因素被遮蔽、忽略的人物。选择他们进行书写,张生全坦言“我有一种发现历史,发现真相的野心”。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他承袭了在场主义写作“去蔽求真”的理念,并认为“历史并不都是具有逻辑性的,太圆润的丝丝入扣的历史写作是可疑的”。
记者:许多人都因为散文写作和在场主义的理念而熟悉你,在多年的散文创作积淀下,长篇小说《蒙哥大帝》的问世令许多人眼前一亮,可否谈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初衷?
张生全:其实我一直都在写小说。或者说,一直都在进行带虚构性质的文本的写作。以前写散文,经常和别人争论散文可不可以虚构的问题。我是倾向于散文可以虚构的,因为我就经常有这样的策略。别人读了,并不以为我在虚构,反而觉得很真实。这说明,虚构原本就不是散文艺术的核心问题。后来我干脆放弃争论和解释,更多地着力于可以虚构的小说创作了。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能够给予我写作更大的自由,传递出更加浩荡、丰沛以及尖锐的艺术感觉,趋近文学的无限可能性,这让我着迷。
记者:在忽必烈的耀眼光环下,蒙哥这一人物可以说在历史上是有所遮蔽的。近年来,文学界多有“重新发现历史”的写作,虽然《蒙哥大帝》是小说体裁,但重提蒙哥,将他的一生峥嵘带回历史舞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历史的补遗。发掘被淹没的、发现未发现的,这样的写作,在当下嘈杂的出版市场上无疑是冷僻且冷静的一支。你为何选择这样的写作作为最近思考的主要方向?
张生全:你前面提到在场主义,在场主义有个重要的理念是去蔽求真。我写蒙哥,也正有这样的想法。你说得不错,蒙哥确实是被遮蔽的。他在蒙古帝国形成与壮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大汗,蒙哥登上汗位之前,帝国事实上已经四分五裂了,是他以及他的家族用铁腕把帝国重新捏合在一起,并且占领了整个西亚、大半个欧洲并一直打到非洲,拥有了蒙古帝国史上最辽阔的疆域。蒙哥也是帝国最后的荣光,蒙哥之后,帝国便一分为四。忽必烈的元朝,其实只是大蒙古的一支。蒙哥大帝的显赫声名被遮蔽,这是有原因的,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我选择他作为我笔下的主人公,正是有一种发现历史,发现真相的野心。虽然明知道蒙哥的题材偏冷,就算我写得再好,在从众的当下市场上也不可能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我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作家最重要的东西。
记者:历史小说的创作,往往以真实历史人物、事件为基础构架,在此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这同时也导致了一个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即客观真实对象与主观作者审美、创作需求之间的差异,你是如何在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故事之间取得平衡的?
张生全: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历史人物或许是不需要虚构的。历史人物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印象,都来自于史书。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干瘪乏味,那是因为官方史学家按照公文的范式,甚至按照当权者的需要,让真实历史人物缩了水,变了形,漆了面,成了一具木乃伊。历史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唤回历史人物的生命,让血液在他身上流动起来,呼吸起来,甚至让他可以生长、思考和创造。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历史小说就成了。我说这话并不是回避和辩解,你看《史记》,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多么精彩,你能说司马迁在虚构吗?抓住历史人物的根核,给他以水分和阳光,让他自然生长,或许他的外表和真实的那个历史人物有差异,但本质是一样的。
记者:如此大的框架、人物、事件众多,很容易在写作中陷入细碎,但如果以主人公一生经历顺延铺展,又在结构上丧失了难度,这也是许多历史长篇小说面对的问题。你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张生全:你说得对,这些确实是在写作前曾经苦恼过我的东西。不过我相信,任何长篇历史小说都是有自身结构的,随着对史料的研读和分析,这个结构会自然浮现出来。以《蒙哥大帝》为例,我是带着探究蒙哥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会被遮蔽的疑问进入史料分析的。接下来我便发现,不仅是蒙哥,他的父母拖雷和唆鲁禾帖尼也有着非常精彩的故事。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成吉思汗的汗位应该传给四子拖雷,而且拖雷在他几兄弟中战功最显赫,拥有的军队最多。但是,成吉思汗出于复杂的考虑,把汗位传给了三子窝阔台,而且让大家发誓,将来的汗位也必须在窝阔台的后代中产生。这就出现矛盾了。后来,拖雷又不明不白地喝下窝阔台给他的“病水”而死掉。这样,矛盾不但有,而且相当尖锐。但此后,拥有庞大军队的拖雷家族并没有叛乱,而是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隐忍,直到汗位几乎水到渠成地落到拖雷长子蒙哥头上。但是不久,权力中心又从蒙哥一支转移到他的弟弟忽必烈那支上,忽必烈非常干净彻底地取代了蒙哥家族在蒙古的地位和控制力。你看,到这时候,《蒙哥大帝》的结构是不是就呈现出来了呢?它已经不简单是蒙哥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是蒙古权杖如何从窝阔台家族转移到蒙哥家族,又从蒙哥家族转移到忽必烈家族的过程。还是蒙古帝国如何从分到合,又从合到分的过程。这样,小说的结构就不再是单线的,而是复调的。蒙哥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和蒙古帝国的历史并不是分离的,相反联系得非常紧密,他是一根主线,扯动这条主线,整个蒙古政治史战争史、故事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及命运这些东西都动起来了。
记者:在《蒙哥大帝》中,你的写作并没有过多渲染蒙哥作为一代英雄的传奇色彩,反而将他的性格细致地在种种日常活动和对话中展现。这样的写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而将在史料中一定程度上被神化的蒙哥还原为真实、复杂、丰满的个体形象,这是否刻意而为?可否就此谈谈?
张生全: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特别迷恋古典传奇小说的。古典传奇中常用三句话,来描述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一句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句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句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伏脉、铺衬和悬念等故事技巧; 第二句说的是故事的丰沛和生动; 第三句说的是故事的节奏和起复。我在写《蒙哥大帝》时,很多地方都借鉴了这样的经验。但是,现代小说和古典传奇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的重心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存在意义。因此,还原生活场景,书写日常细节,这些有别于情节技巧的策略就变得非常重要,历史小说也不例外。虽说这种方式有可能打断情节的流畅性,但小说的容量和力度上会有大收获,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记者:但凡历史题材的写作,作家多有自己的思考路径和写作倾向。《蒙哥大帝》中,似乎能读到这样的意味———宏观而言,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具体到个人,英雄人物的命运却常常由种种琐碎、意外小事而决定。命运的无常和戏谑在历史长河中从来不乏佐证。这是否一定程度上也是你对于历史的看法?
张生全:在《蒙哥大帝》中,我确实在很多地方写到了偶然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蒙哥久攻钓鱼城不下,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集合所带领的全蒙古军和钓鱼城宋军进行最后的决战。不过,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这样打。他虽然举起了指挥棒,但并不确定是否挥下。恰在这时候,一只蜻蜓落在了他的指挥棒上。他本想先把蜻蜓抖落,但蒙古军误会了他的动作,总攻因此发动起来。正如你说的,我选择的这个细节不无戏谑,也是来自我的想象。但是,我并非胡想。因为蒙哥被飞石打死,其实也是相当偶然的,我的“抖蜻蜓”细节便契合了这种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那正是处于事业巅峰期的蒙哥性格的一种体现。我写这个细节,既在写蒙哥的性格,也在批判蒙哥所发动的好大喜功的战争,同时表明了我的一种历史观。历史并不都是具有逻辑性的,太圆润的丝丝入扣的历史写作是可疑的。
记者:近期,你又推出了新作《不倒翁冯道》,全面展示了冯道的一生宦海生涯。与《蒙哥大帝》相比,《不倒翁冯道》 在写作上的重点是否有所不同?可否大致介绍一下?
张生全:在题材选择上,《不倒翁冯道》和《蒙哥大帝》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比较偏冷偏难的。所谓偏冷,是这两个人都不太为大家所熟悉。所谓偏难,是指要么史料偏少要么历史太混乱不容易厘清。在主旨上,两个作品也都寄寓着我重写历史重写历史人物的愿望。蒙哥是长久被遮蔽被忽视,冯道则是反复被误解被歪曲。我写冯道,也是有为他翻案的想法。不过,在表现手段上,区别很大。蒙哥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但性格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冯道一直高居相位,流水的朝廷铁打的宰相,但他的性格非常复杂。写蒙哥,需要从历史中把他凸显出来,力量是往上的,传奇的。写冯道,则需要让他回到历史的原生场景,展现他的本来面目,力量是往下的,日常的。这两种写法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任何手段都是由人物决定的,两个主人公性格与际遇的差别,决定了我有这样不同的选择。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