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小说 >> 作品展示 >> 正文
蟠虺(pán huǐ)(节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16日09:53 来源:人民日报 刘醒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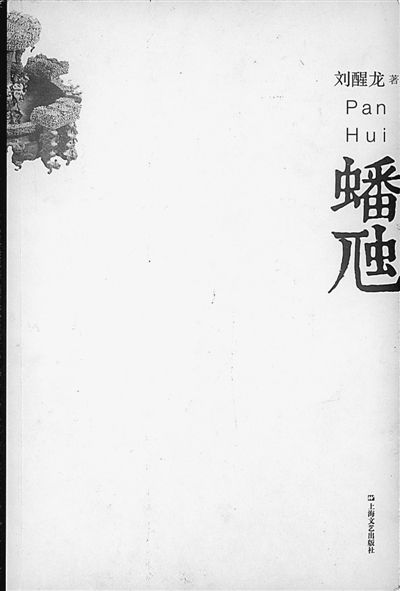 长篇小说《蟠虺》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蟠虺》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人来说,其他人所表示的敬爱是一种不胜其烦,亲爱则是一种不胜其扰,深爱更是一种不堪其扰。
曾本之到宁波头两天的遭遇正是如此,郑雄的谦卑问候,曾小安嗲声嗲气的关切,最后是安静蛮横无理加上柔情如水的呵护,让曾本之不得不尽可能晚地开手机和尽可能早地关手机。让曾本之最心烦的是,这些短信与电话,十次当中,至少有九次询问他的脉搏次数,剩下那一次,不是问有没有胸闷,就是问有没有头晕。
马跃之就出主意,让曾本之主动发短信回去,认真报告自己的脉搏、血压、喝水、吃饭以及排泄等情况。短信一发,果然就平静了。
为此,曾本之多次表示对马跃之的佩服。
反过来,马跃之更佩服曾本之。他俩一到会议的报到处,就被与会的同行围住。那些人是冲着曾本之来的,对马跃之只是顺便客套一下。他俩住的房间也是与别人不同的大套,即两间卧房共用一间会客厅。待到会议的最高主管来房间看望他俩,恭敬地表白,住宿和相关人员邀请全部遵照曾本之的提议办理时,马跃之才明白,所有这些,包括点名要自己和曾本之共同与会,其实是曾本之事先发了话并作了安排的。
马跃之有些奇怪,他将会议手册摊开:“这个会是研究青铜重器的,就我一个人不属于你们这行,你不会是想出我的洋相吧?”
曾本之免不了要安慰他:“一般会议都是务虚,不会有太大意义,我就是想拉你出来,一起散心和说说话。”
说起来轻松,真实情况却未必。
曾本之在青铜重器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威望,得益于他对早已失传的青铜重器铸造工艺的研究。
声名远播的曾侯乙编钟,是青铜重器领域最广为人知的精品。全套六十五件编钟按大小和音高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总重量达两吨半,为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外行人喜欢将它说成青铜重器中的万里长城,名头与天齐高,值得研究的奥秘却不多。比如铸造工艺,因为编钟的各个部位有明显的范缝,也就是铸造模型的不同模块间的缝隙。编钟钟体那些突出来的浮雕纹饰,也是明显通过复合方法组成范铸模型浇铸而成,若是再去研究是否还有其他铸造工艺,无异于说普通算术中的一加一不等于二。又比如青铜成分,这一点同样称不上难度,普通的化验员就能弄清楚。所以,有以上两点作保证,出土才五年时间,就被完整地仿制四套:一套放在原件出土地点所在的随州市博物馆,一套留在省博物馆,第三套给了有小故宫之称的台北市仁爱路鸿禧美术馆,第四套则被黄帝陵所收藏。
按时下常常被人形容的,如果说曾侯乙编钟是青铜重器中的皇冠,那曾侯乙尊盘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曾本之正是因为对这颗明珠的研究而享誉中外考古学界。
时下还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行不行,要看说这个人行不行的人行不行。同理用在学界也是如此,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行不行,要看研究者所研究的东西行不行。曾本之在楚学院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就在于他潜心研究的曾侯乙尊盘的地位,在所有已发现的青铜重器中是至高无上的。连那些喜欢买彩票的楚学院勤杂工,都会用曾侯乙尊盘打赌,说假如某组号码能中大奖,自己马上就去做梦,将曾侯乙尊盘仿制出来。像马跃之这样的非青铜重器专家,也会在某个场合脱口冒出一句说:“你都要成为曾侯乙尊盘了,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青铜重器研究方向上,因为研究曾侯乙尊盘成了楚学院的专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楚学院的水准就是学界的最高水准。
曾本之不知对那些更看重曾侯乙编钟的人解释过多少次,对曾侯乙尊盘的敬畏与崇拜,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正是这种横空出世独步天下的绝对之美,给曾侯乙尊盘带来空前的神秘与玄幻。让人禁不住地想知道,如此美轮美奂精巧绝妙的青铜重器,为何上下几千年来仅此一件,哪怕有些许相似的,也找不到第二件。
“普天之下但凡穷尽精华而为的物品,一定是非凡之人作非凡之用。”
出自曾本之之口的这句话,所指的正是曾侯乙尊盘关键所在。研究成果公布之初,曾本之曾在不太大的范围内作过确切的说明。其中,那世所罕见的祥瑞事例,更是只与极为核心的少数人谈及,一方面是担心此种事例会颠覆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更担心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因此萌生邪念。自从郝嘉从楚学院顶楼孤孤单单地飞翔而去,曾本之突然闭口不再谈及这些,非要说明曾侯乙尊盘至高无上地位的原因,也只说纯粹是因为其无法仿制。
如此重器中的重器,国宝中的国宝,一九七八年在随州擂鼓墩出土,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以对它的完整仿制,来实现个人在考古学界的梦想。到头来无一不是青铜如旧,梦想如旧,那些心怀侥幸者,试着仿制的或尊或盘,破烂得连垃圾都不如。
多年前,曾本之在青铜重器学界,石破天惊地指出,曾侯乙尊盘是用失蜡法工艺制造的。曾本之还通过一系列相关研究证明,最早使用失蜡法制造青铜重器的人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为中国青铜史写上全新的一页。
用失蜡法也被称为熔模法铸造青铜重器,从难度上讲,也不是高不可攀。如果想做一条龙或者一只凤,先用蜂蜡做成龙或凤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并敷成外范。然后加热烘烤,让蜡模熔化后自然流失,待龙或凤的模型变成空壳了,再往里面浇灌青铜溶液,一条龙或者一只凤就铸成了。因为蜂蜡的柔韧可以做出任何形状,曾侯乙尊盘上那些玲珑剔透,像蕾丝一样多层透空蟠虺纹饰附件的模型完全可以做出来。然而,从一开始曾本之就对自己的理论作了补充说明,不要设想从殷商到楚共王,古人用了一两千年才造出唯一的曾侯乙尊盘,今人会像复制曾侯乙编钟那样,只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再现青铜重器鼎盛时期的辉煌。
曾本之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比如泥芯用什么材料,外范又用什么材料,泥芯与外范材料中的含水比例,青铜熔液的温度,浇铸青铜熔液的速度等等,还有其他一切与青铜铸造相关的工艺,只要有一项不正确,尊盘上面那些只有几毫米粗细,却密密麻麻弯曲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透空蟠虺纹饰,就会变形走样。只要有一粒米大小的变形走样就是失败,而在如此精密如此复杂的曾侯乙尊盘上,太容易发生此种失误了。况且,从曾侯乙尊盘出土至今,那些透空的蟠虺龙纹,到底是一千条,还是几千条,连曾本之自己都没有弄清楚,谈何百分之百仿制。
无论如何,作为青铜重器研究的关键成果,曾本之就是失蜡法,失蜡法就是曾本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让马跃之没想到的是,曾本之暗中拉他来参加的宁波会议,居然汇聚了国内几位对失蜡法强烈质疑的青年学者。他一看到会议手册上那几个人简介,虽然没有跳起来,心里却着实揪了一下。其中一位叫易品梅的女子,学术简介唯一提到的论文标题赫然写着《论青铜时代中国并无失蜡法兼与曾本之先生商榷》。易品梅这篇从根本上否定失蜡法的论文,前几年就公开发表了。马跃之知道较晚,并非仅仅只是因为没有研究青铜重器,还在于楚学院资料室订阅的各种专业报刊,必须由当院长的郑雄一一过目才能上架借阅。凡是刊载有反对失蜡法或者对失蜡法表示质疑文章的报纸或者杂志,都被郑雄先行借走,用不再归还的方法拦截下来。至于一些专业会议与活动,要么由郑雄陪着曾本之参加,要么是郑雄独自参加。郑雄调任文化厅副厅长之后,对楚学院的日常事务有些鞭长莫及,马跃之才从新来的报刊中了解到,被奉为青铜重器之神的曾本之,其不败金身已经被雾霾所笼罩。
会议进行到中途,情况似乎有了变化。众星捧月般围在曾本之身边的人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与曾本之的名望差不多的人,无一例外地疏远了,开会时不得不坐在一起时,也没有人与他交头接耳了。曾本之很快从易品梅那里得到消息,那些人听说曾本之要申报院士,并且有可能当选为院士,才故意疏远他的。易品梅没有因为质疑失蜡法而反对曾本之申报院士,相反,她觉得不能因为在失蜡法的问题上存疑,而否定曾本之在青铜重器领域的卓越贡献。
紧接着,马跃之也听到有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凡是生不出如花似玉的女儿,找不到精明强干的女婿的人,就不要入青铜重器这一行。马跃之就与曾本之说,自己马上回武汉,换郑雄来参加这个会,郑雄一来,就会将这股邪气镇压下去。
曾本之不同意,还反问马跃之:“我这样子像不像院士?”
马跃之想了半天才回答:“一半像,一半不像。”
曾本之又问:“哪一半像,哪一半不像?”
马跃之说:“上半身像,下半身不像。”
曾本之说:“你说的不是院士,而是太监!”
对于自己说过的话,二人都是一笑了之。
会议的最后两天安排参观。头一天去奉化参观蒋介石故居,那位写论文与曾本之商榷的易品梅,一直跟着曾本之,一有机会就请教有关失蜡法的一些问题,说当初写那篇论文时,有些匆忙,经过这几年的深入研究,才认识到否定一种东西,要比肯定某种东西来得容易。曾本之要她不妨再坚持一段,说不定又会峰回路转。曾本之没有直接说明,要对方按照自己论文所推论,用范铸、热加工和焊接等办法来复制曾侯乙尊盘,他婉转地提醒易品梅,可以向有关方面申请专项经费,用自己认可的方法,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马跃之在旁边听着,心里觉得奇怪,若不是自己太了解曾本之,一定会将这些说法当成极度虚伪。他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开玩笑地说:“什么叫大师风范?这就叫大师风范。鼓励那些反对自己的人继续反对下去,这样的事我就做不到,所以我这样的人成不了大师!”
曾本之也跟着他说笑:“跃之兄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吭声,将一肚子话留在蒋家故居里说,这是什么动机呀?”
马跃之说:“这叫什么会,除了我老马,人人满身铜臭,我才不屑与你们为伍!”
不等曾本之开口,伶牙俐齿的易品梅抢先说:“幸亏马老师提醒,先前我好奇怪,马老师身上的气味与我们不一样,这下子我可就明白了,原来马老师是贾宝玉的转世!”
马跃之没有反应过来:“此话怎么讲?”
易品梅抛了一个媚眼:“贾宝玉身上的脂粉气全转移给你啦!”
见曾本之笑得很开心,马跃之说:“以前我就没弄明白,为什么一天到晚总有人与我商榷,而研究青铜重器的比我们这一行的人多上一百倍还不止,怎么就只有那个叫易品梅的女子敢公开与本之兄商榷。今天我算是明白,什么叫温柔一刀!”
曾本之收起笑容,很认真地对易品梅说:“谁没有一点顽固,年轻时叫小顽固,老了就叫老顽固。今天我这个老顽固,给你这个小顽固介绍一位我的同事,往后有事你可通过他和我联系。”
易品梅说:“是不是您的那位大秘呀?我可惹不起,为了那篇商榷的文章,都快被他逼疯了!我们长沙说什么也算是个青铜重器大市,原说要成立的青铜重器研究所,最后却泡汤了!据说也是大秘的杰作。”
马跃之连忙说:“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你看曾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不可能让下面的人做这种事。”
易品梅说:“先前我对曾老是有误解。好几年了,我一直被人封杀,这次突然接到邀请函,心里很奇怪,来宁波报到之后,才听说是曾老点名要我参加。官场上是秘书干政,学术上也有助手绑架导师的。我就猜测,过去的事,一定是曾老的那个‘大秘’,背着曾老搞学术专政!所以才敢对曾老说心里话。”
曾本之说:“有些事情并不是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也不是谈一次话就能澄清的。往后有事可以先与万乙联系,是刚到楚学院上班的博士生。”
易品梅说:“我晓得他。春节时我们在网上认识了,就是没见过面。”
马跃之正要说话,被曾本之拦住了。蒋介石故居并无特别之处,让曾本之唯一注意的是蒋介石最后一次离开奉化老家,与乡亲话别的那张照片。从不让马跃之说话起,他就盯着那只挥别的手和那手上伸出来的三个指头。讲解员请大家猜,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是何寓意。
马跃之忍不住说:“这太无聊,当年的小学课文中有篇《三五年是多久》,不就是这样的吗,蒋介石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被迫撤离江西瑞金时,对乡亲们说,过三五年红军就会回来。于是,乡亲们盼了三年,再盼五年,然后又盼了三加五等于八年,哪想到最后是三乘五等于十五,过了十五年红军才回来。”
讲解员有些尴尬,但还是坚持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说奉化的乡亲先是以为蒋介石三年就会回来,而后又以为三十年会回来,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严,成为蒋介石离开奉化后第一个回来的蒋家人,奉化的乡亲们才明白,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是告诉大家,自己没机会回来,蒋经国也没机会回来,只有蒋家的第三代才能回来。
听到这话,曾本之心里一动。
其他人跟着讲解员往前走,曾本之留下来将蒋介石伸出三个指头的样子看了好久,直到易品梅回来找,他才心事重重地离开,并不再对易品梅有问必答了。
从奉化回宁波的路上,曾本之睡了一会儿。
大客车行驶得非常平稳,连驾驶员都在不断地嚼口香糖,免得自己也打瞌睡。曾本之像是做了噩梦,猛地叫了一声,邻近座位上的人,不管是睡着还是没睡着的人,全都听见了。那些没有直接听见曾本之惊叫的人,受到其他人的惊扰,纷纷环顾左右,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别人都醒了,曾本之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又继续睡去。片刻之后,车厢内又恢复了平静。
回到下榻的酒店,一应事情忙完之后,窗外的霓虹灯已经亮了好久。马跃之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发现对面房间没有动静,叫了两声也没有人应,走进去一看,一起回来的曾本之不见了。
正好柳琴打来电话,问这边的情况。
马跃之回答说一切都好,后天就可以回家。
老夫老妻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就没事了。马跃之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没事乱想,忽然觉得曾本之有可能与易品梅聊天去了。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忍不住独自笑了起来。
正在这时,门一响,曾本之回来了。
见马跃之一个人关在屋里笑,曾本之就问:“是不是有丝绸包裹的楚国美女复活了?”
马跃之笑得更起劲了:“我俩又想到一块去了,实话告诉你,我在笑你是不是喝茶品梅去了!”
曾本之说:“我还真的在电梯里碰见她和另一个女的,说是出去逛街。”
活到七十岁,这类带有青春回忆色彩的话题,总是难以为继。很快马跃之就说起在车上曾本之的那声惊叫。
“你是不是做白日梦了?”
“是的,我梦见郝嘉了!”
“一定是蒋介石伸出的那三个指头勾起你的回忆!当时我看你在那幅相片前发呆,就觉得要出点什么事。”
“实在是太像了,郝嘉死的时候,也是伸着三个指头!”
“是啊!以前我们都觉得郝嘉的手势只是平常习惯表示的OK,听了蒋家的传说,我也觉得这里面是不是还有玄机!”
“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想,就想这个,想来想去,别的没想出来,却想起那年他从楚学院六楼跳下来的情形!”
“若是我梦见他从六楼跳下来的样子,也会做噩梦的。按他们说蒋家的那样,郝嘉伸着三个指头,是要表示三年、三十年和第三代人的什么呢?是他自己要去武汉长江大桥卧轨的,楼也是他自己要跳的。三年早过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估计三十年也和三年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事。下面的就更不要想了,他连个儿子都没有,哪来的第三代?”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哪怕不是从他那里偷的,也是他赠送的。那一年,随州那里修铁路,我和郝嘉被派过去帮忙,沿铁路线查看有没有挖出来的文物。那天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铁路民工挖出一座大墓,要我和郝嘉尽快赶过去控制现场。要说郝嘉比我激动得多,一连几天都在说,这辈子他和我只需要研究这座大墓里的东西,最差也能成为教授!”
“现在的教授多得都快成鼻屎了。我想起来了,郝嘉从六楼跳下来时,就算不喊共产党万岁,还可以喊之前的口头禅曾侯乙万岁呀!为什么偏偏要山呼鼻屎呢?”
“我也觉得难以理解,郝嘉平时那么儒雅和浪漫,临死时,居然会在跳楼的最后时刻,高喊鼻屎二字,说起来反而像是恶作剧!”
“郝嘉出事后,我也想不通,全楚学院几十号人,可能要出事的人,至少有七八个,为什么要争这谁也不想要的冠军呢?”
曾本之轻轻地叹了几声:“当年,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将曾侯乙编钟仿制出来,郝嘉也是有贡献的。说心里话,我不如郝嘉。郝嘉若是不死,肯定能将曾侯乙尊盘仿制出来。”
马跃之很想说,曾本之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郑雄这样的女婿,个人的名利捍卫得很好,但又为名利所累,重大研究不能拓展,思路也无法拓宽,话到嘴边了,又改为:“你那像尾巴一样寸步不离的女婿,这一次怎么没有跟着来?”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为什么总带着秘书?”
“本之兄到底是个明白人,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趁早做点学问更有意义。”
“跃之兄,你也对我说句实话,郑雄这人给你的印象如何?”
“人家都是正厅级会长了,我能说什么呢?”
“你今天若是不说句实话,往后就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郑雄的名字。”
“哪能这样说话,简直是要焚书坑儒!好吧,我再说一遍,郑雄是比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伪娘还要伪的伪娘!”
“你还是没有说真话,还是在搞弯弯绕!”
马跃之将曾本之狠狠盯了几眼,终于咬牙切齿地说:“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企图了,我就说一句绝对的话。郑雄如果是青铜做的,用我这双只懂丝绸的眼睛来看也是伪器。让曾小安嫁给郑雄,是本之兄这辈子最大的败笔!”
曾本之沉默了好一阵,才说:“我刚才下楼去会务组,将机票改签了,我们提前一天回武汉。不要与任何人说,包括柳琴。也不用叫人接机,我们自己乘出租车,到市内找酒店住一晚。”
马跃之后来才明白,曾本之所说的市内酒店,既不是汉口的香格里拉,也不是武昌的五月花或汉阳的晴川,更不是水果湖和东湖交界处的弘毅。而是一处若不是曾本之带头钻进去,自己哪怕患了老年痴呆症也不会走进去的小招待所。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