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触摸当下乡村的“真实体温”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15日09:52 来源:深圳商报 陈亦然作家杨献平新作《生死故乡》直面“溃败的乡村”
触摸当下乡村的“真实体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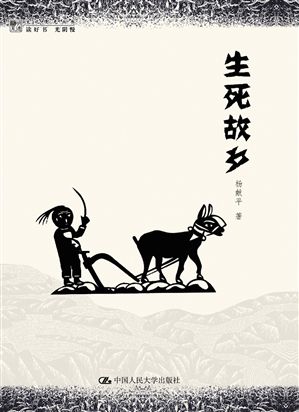 ▲《生死故乡》杨献平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定价:35.00元
▲《生死故乡》杨献平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定价:35.00元 ◀生于河北、客居成都的杨献平,以“不是虚构、也不是纪实”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经生长的土地:南太行山区乡村。新作《生死故乡》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 (受访者供图)
◀生于河北、客居成都的杨献平,以“不是虚构、也不是纪实”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经生长的土地:南太行山区乡村。新作《生死故乡》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 (受访者供图)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作家杨献平选择了与故乡“握手言和”。
此时,故乡已是“溃败的乡村”,而他却成为一位“宽容的游子”。生于河北、如今客居成都的杨献平,以“不是虚构、也不是纪实”的方式,直面自己曾经生长的土地:南太行山区乡村。放下对故土的偏见,没有藏掖,没有伪饰,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
乡村人群一方面自然消亡,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加入到城镇当中,这种剧变酷烈而深刻,前所未有。作为民族文明和风习的主要沿袭地与文化场域,传统乡村正在面临形式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如何审视当下乡村现状及其文学表现,是一个颇具意义的文学和社会的“焦点”。
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生死故乡》中,杨献平以南太行山区乡村及其人群为主要考察对象,真实而艺术地呈现了十多位具体农民截然不同的奇诡命运和人生遭际。近日,笔者就本书内容、乡村现状及当下散文写作等方面,对杨献平进行了独家专访。
我们时代的“乡土之根”
《文化广场》:创作《生死故乡》的缘起是什么?您在《生死故乡》的楔子中说,一个南太行,可以辐射到整个中国北方乡野,您是否期待关照更多?“故乡”前面加了“生死”二字,有了沉重的意味。
杨献平:一个人其实关照不了更多,尤其是平民。处在一隅,能够看到的世界只是它确切的某一处;身在人群,与大地众生齐平,凌空俯瞰绝对是一种虚假姿态,也不可能真切、全面地触及。多年前,对地域及其人群的书写,我也有狭隘、卑小、不值得关切和书写等疑虑,为此也很苦恼。但慢慢地我发现,大地上的人只是所处方位和环境不同,其命运、生存境遇与精神诉求几无二致。
随着老人们的逐渐“与世长辞”,年轻人纷纷进城谋生,乡村自然沦为“正在消失的人类聚居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及其携带的文明不仅在外部逐渐向“废墟”和“遗迹”行进,接续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人也几乎不复存在。目前来看,乡村的死亡不可避免,传统乡野文化和文明的断裂与再造、新生已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乡村的“生与死”对于这时代有着“乡土之根”的这一部分来说,有着文化和精神上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文化广场》:《生死故乡》里,坚韧的生命,卑微的生存,颇具戏剧性。我以为,这里应该是没有“虚构”的,不知对否?人类自身的幽深、复杂、离奇,是不是比小说更丰富?
杨献平:任何的想象力都必然以现实存在为依托。《生死故乡》当中的人及他们的故事、命运,有相当一部分是确有其事,只是在书写当中,适当加强了矛盾冲突,使其更具有感染力。再者,无论哪种文学体裁,让人有兴致读下去才是首要的问题。
有批评家说现实生活和匪夷所思的新闻永远都无法取代文学,这没错。但在这个有意思的年代,作家的想象力和讲故事能力显然弱于这个时代的现实。将来则未必。过于强调文学的艺术性或现实生活的力量,都是偏颇的。好的文学,当是从尘埃里来,到云霄上去;从人群中生发,在精神和灵魂生根。时间、自然乃至人类,其存在、变迁本身就是一部奇诡之书。这世上每个具体人的命运,也都是与之相对应和协调的。
现实只会比文字更生猛
《文化广场》:您的《生死故乡》,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原生态”。这种“原生态”的残酷,破坏了我们想象中的“田园式幻想”,请问这是当下乡村的“普遍真实”吗?我们是不是常常错估当下乡村的温度?
杨献平: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流行甚至被捧了很多年,其主要迎合的是城市知识分子及其精神乌托邦。从文学角度说,这没错。作家建立的是自己的文学高地。但对于乡村和农民是不公平的。
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乡村都如《生死故乡》,但至少北方大部分地区如此,甚至比之更“生猛”。《生死故乡》中的乡村绝对“普遍真实”,还有比之更惨烈的,我想在下本书中写出来。以文学的方式还原当下真实的乡村现状,让更多人触摸当下乡村的确切“体温”,虽然与当下时代文化特征相悖,但很有价值。有人参与“合唱”,也要允许有人“跑调”。
《文化广场》:《生死故乡》中有大量的笔墨,涉及到“乡村里的性”,让人有一种出乎意料的“随意”。乡村人对性的态度,折射出了什么?
杨献平:性是生命源动力。乡村人直接,崇尚暴力;文化信仰混乱,再加上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普遍低劣,在绝望与痛苦之中,唯一可以让他们暂时“幸福”的一个是挣到钱,一个就是性。这两种东西,不仅在城市如是,在乡村亦然。可以说,性是乡村人群借以自我安慰,消解苦痛的最有效的生理和精神活动。
我本质上是一个农民
《文化广场》:您个人的经历很是传奇,农民、打工者、军人、作家,这些转换中的身份,之于今天的杨献平,都有什么意义?
杨献平:农民是根,联结大地与最低层人群,当然还有乡村文明及其文化传统;打工时间很短暂,学过几个月木匠而已;可忽略不提。军人血中有铁,有梦想,是诸多职业中最有使命感与梦想之音的。朴素是生命本身,梦想当中不仅包含个人心性,还有家国情怀。居一隅而望四野,虽一人却念众生。这该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文化广场》:20年前,您就曾经用文学的方式,一次次对故乡南太行及其人群进行书写。但后来,您表示了不满意,去除了偏见,从而有了这次全新的书写。这样的过程,是不是也伴随着一位作家的蜕变?
杨献平:这该是一个促狭到开阔,仇恨到宽容的过程。20年前我以为恶人恶事只有南太行乡村才有,后来才知道遍及全人类。乡村生存资源本来匮乏,有些利益冲突也正常。都是为了生存,只要不伤及性命和尊严,没有什么不可以宽容的。这种心态的不断蜕变,也和年龄与看世界的方式不断自我矫正有关。
《文化广场》:写作者对待故乡常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诗意和美化,一种是讳莫如深。而在《生死故乡》中,却感觉你与故乡“握手言和”,直面自己,直面乡土,没有藏掖,也没有伪饰。与故乡“握手言和”之后,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还会有“变形怪物”之感吗?
杨献平:乡村人争斗,代价惨重,伤人也伤己。他们也很可怜。理解便会同情,无奈也是悲悯。真实呈现他们的种种行状,尤其是苦难遭际,有告诫的意思在内,更多的是期望。这也是一种和解方式。对故乡,我还是爱的。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虽在外省城市,但心还在乡野。我想这是我和故乡最好的一种“关系”和“状态”。
空谷是最好的去处
《文化广场》:杨显惠老师说,读完《生死故乡》后,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称您这部书写出了这30年的农村史。您是否无意中,承接了某种文脉?如何看待杨显惠老师的评价?
杨献平:苦难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一种集体“未完成生命体验”。《生死故乡》初稿完成,我发给杨显惠先生,并替他拟好了一段话。杨老师说他要亲自看。两个月后,他发来一段他自己的话。他这样评价,我没想到。欣喜也很忐忑。我的《生死故乡》确实写了近30年来的乡村人群命运变迁。但距离杨显惠老师的评价,还是有距离的。他无意中给我鼓励,也给了我今后的动力。
《文化广场》:您在序的最后,对自己的文字是否被人接受,似乎有一些疑虑,但也洒脱。您说:“不管这些文字是不是有着与其他文字不同的面目和内质,也不管这些文字会不会得到更多的同感和好评,写和还能写下去,对我来说,就是胜利。”为何会有这样的疑虑,这样的洒脱?
杨献平: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需要的是“物质上的成功”、“迷惘、苦累中的自我娱乐和情感寄寓”。乡村书写基本上淡出文学主流。像《生死故乡》这样一部底层苦难书、乡村人物传,受关注的可能性不大。没人愿意再在纸上获取更为沉重的“他者”经验。另外,不以写作为生,就不必顾虑太多。当一个人不需要喝彩的时候,空谷是最好的去处。
《文化广场》:当下的散文写作,呈现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态,是否也存在一些流弊?您认为文学最打动人心的应该是什么?
杨献平:当下的散文状态可能是30年来最好的。流弊一是历史题材写作没有生命温度,缺乏精神谐振;二是城市题材强调个人精神和思想异化、生活的新鲜感与个人现实主义;三是乡村题材写作过分诗意、美化怀旧色彩偏重;四是坊间影碟解读及读书随笔缺乏人间烟火气息,偏执偏颇。五是散文批评跟风习气浓郁,缺乏全面精准的论说与发现。文学最打动人心的,是让人从中看到自己的“内心结构”、“情感纹理”和“精神质地”。 (深圳商报特约撰稿 陈亦然)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