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许知远:尽管我强调“现实感”,却是个浪漫主义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22日10:42 来源:文学报 傅小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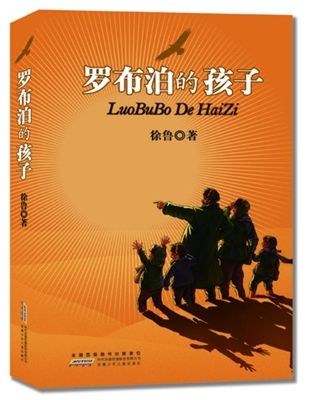
“我的‘中国意识’是自我寻找的结果”
记者:您获此次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作品题为《时代的稻草人》,实际上是对别让自己成了另一个“稻草人”的警醒。而这本书传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抉心自食”的自我审问,这种彷徨迷惘后的反省和思考。
许知远:我想知识分子多少都有边缘之感,正因如此,才令他保持思想的敏感性。自我追问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前提,否则你的思考毫无立足之本。此刻的中国处于一种转型期的混乱,大部分以知识分子名义的发声,却与知识分子无关。我曾对这种状况深感焦虑,现在却逐渐有一种淡然之感。我们都会被虚荣吸引,要学会驯服这人性弱点,它妨碍你对更高理想的追求。
记者:实际上,不管怎样去理解“时代的稻草人”的命名,这个命名本身透露出了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力感。而如何让个人在喧嚣的时代里,发出坚定有力的声音,才是你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否如你所说的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词汇、情感拯救出来,赋予它们本来的光彩,让精神、思想、知识彰显出永恒的力量,并以此确立起自己的内在世界,就可以做到?
许知远:这个过程自然是复杂的、反复的,我也没有好的方案。我只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它也未必导向一个我希望的结果。但是,它是目前最吸引我的方式。因为美好的语言、崇高的思想、纯粹的精神生活对我充满吸引力。
记者:村上春树有一篇题为《高墙与鸡蛋》的演说。他说:人类面对名为体制的坚实高墙,注定毫无胜算,“唯一胜过它的可能性只有来自我们将灵魂结为一体,全心相信每个人的独特和不可取代性所产生的温暖”。
许知远:我们既缺乏宗教生活、也缺乏文学生活,怎么可能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更何谈灵魂?此刻的我们谈论灵魂时,常是置于功利主义框架下的,它很容易沦为心灵鸡汤。
记者:如果把你迄今所有的著作放在一起,会传达出一种特别的焦虑,让人止不住有紧张感,你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于此可见一端。这也印证了你时时刻刻的“在场”。
许知远: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生活啊。对待生活,我有一种明显的轻浮的倾向,常常离场的。正因为这种“轻浮”,我才尤其在书写中寻求紧张。当然,我不是个特别有天赋的作家,也仅仅是在这三四年开始寻求更为严肃的思考。我对“在场主义”的理解,更像是以赛亚·柏林所说的“现实感”,你必须有能力感知四周的环境,而不仅仅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
记者:你的大多思考体现了一种“对于中国的关切”,即使是谈论西方的话题,你的笔触也会很自然地转向中国。
许知远:这与性格与思维方式有关吧,或许我缺乏有些学者对现实的分析热情与能力,却对知识与思想的网络更感兴趣。尽管我强调“现实感”,却是个浪漫主义者,对于超越性的意义更感兴趣。我更希望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纯个人性的、情感性的。对于缺乏宗教感触的我来说,中国这个概念具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征。我记得夏志清曾讥讽中国知识分子太“感时忧国”,这可能妨碍他们的视野。但对我来说,这“感时忧国”却别有魅力,它为我这样的无根者提供某种根基,尽管这可能也是虚妄的。
记者:眼下很多学者会在中西方历史和现实的横向比较中,来探求中国的问题,他们藉以观照中国的思想资源,大多也源于西方。然而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实际上还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让一种观念或思想,在更广泛的群体里产生影响,还是需要激活传统的资源。
许知远: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它总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此刻的最大的问题是多元思想的欠缺,只有在这多元思想的争辩中,人们才可能寻找到某种与此刻中国相关的共识。我的“中国意识”是自我寻找的结果,你在中国成长,不该忽略自身的经验。也只有以此为基础,你才可能理解世界其他的经验。毕竟,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观察世界的立足点。
记者:你出版于十几年前的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一版再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感召力。这似乎也在提示我们,那个时代并不只是等同于现在以为的“理想”、“激情”之类的代名词,实际上还意味着更多?
许知远:每个时代都是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两个名词来概括。同一批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再正常不过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已大不相同了。倘若要有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首先要打破一些禁忌。否则无从谈起。
“与其谴责时代,不如让自己成为逆潮流者”
记者:就精英的坚守和抗争,你在《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里举到的泰戈尔的例子有典范性:泰戈尔婉拒了甘地希望他拿起纺纱车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要求,他说:“我可以纺织诗句,可以纺织歌曲,但亲爱的甘地,对于你宝贵的面纱,我会弄得一团糟。”这一回答实是意味深长。
许知远:每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精英,他们提供这个时代的知识、道德、审美上的坐标。精英团体也必须是开放的,为此能保持其活跃性与现实感。我们的时代的“精英”一词,很大程度被权力与金钱扭曲,它与道德、知识、教养无关。我觉得自己十多年来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参与重建一个精英文化传统,尽管它看起来很不成功。
泰戈尔与甘地之辩,是一个社会内部的思想与行动者之辩,也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辩,它们再正常不过。缺乏任何一方,这个社会都会滑向偏执。
记者:换一个角度,泰戈尔的回答里,也包含了对专业本位意识的思考。
许知远:我们的确处于一个浅薄的时代。但与其谴责时代,不如让自己成为逆潮流者。
记者:同样是在这本书里,你提到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球世界时,世界的人们都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却很少有人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
许知远:或许我们不该如此大而化之的讨论问题,动辄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有亚洲与世界意识的。在文章里所提的谭云山,他能如此促进中印交往,他也不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想,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理解被忽略与低估了。
记者:相比前辈思想者,年轻一代都抱有一种“观念改变世界”的自信。但有些先进的观念为何难以深入人心?为何观念的革新,很多时候都止步于利益、人性的纷争?极而言之,对“观念改变世界”的期许是否太过乐观了?
许知远:观念自然是重要的。但观念常常只能生长,不能移植,这过程充满意外的变数,它的结果常与期待的不同。我想,“五四”一代恐怕对观念的作用更为自信吧,觉得找到了某种主义,就找到了解决方案。
记者:在为同时代思想者能如此深入思考中国感到钦佩的同时,还是不免感到遗憾,这些思考总体上看是碎片化的,缺乏比较统一的整体性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伟“中国三部曲”的写作有着启示性的意义。因为他从容不迫的叙事,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了复杂多义的中国现实。你是否设想过,立足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截取某个历史或时代的片段,书写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
许知远:我也对自己的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满,可能这与早年的媒体化写作有关,也与书籍的编辑方式有关。何伟的写作也启发了我,尤其是他的观察之耐心。但是,写作中国并非只有这一种角度啊,他的方式只是美国的写作训练出的最佳例证,并非一定多么富有原创性。
“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
记者:就中国而言,谈历史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史家书写的历史,给你呈现了“进步的幻象”,实践的历史还是会不断提醒你,别以为你已经走了很远,实际上在不少方面,你很可能是在原地踏步。
许知远:我强调历史感,是因为它的确在中国当下是一种欠缺。对我来说,历史感能防止孤立地看待问题,它也为你此刻生活提供价值与意义———你是生活于某种传统中的。书写历史也是实践历史的一种。
记者:面对历史,我想至少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为现实何以如此寻找理由,另一种是为现实何以不能如此寻求答案。当然,还有一种或许就是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或彻底的漠视。
许知远:首先,历史一定是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是从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化的历史结论,即使存在,也决不能以牺牲对于历史的具体感觉为代价。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
最后,我们应有的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这是说在严格的关于写作和内容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先前设定的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价值的依据。
记者:我们时代的错位,但凡有点敏感的人都会有所体悟。很多作家也乐于把它称之魔幻现实的国度。似乎“魔幻” “荒诞”这样的词汇,就足以做出概括。
许知远:在任何一个价值断裂、意义缺失的社会,荒诞都是必然的,因为人们缺乏言行的逻辑。但要从荒诞的事实里创造出非凡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就必须要创造者本身具有更高的价值与意义系统。我们的作家只占有各种荒诞的现实,而普遍缺乏一种更超越性的内在价值系统。
记者:围绕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争论。我个人比较认同桑塔格的一个判断。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在诸如正义之类的问题上浪费太多的口舌,而是应该执着地寻求真相。
许知远:真相当然是一切的基础。但是谁也不能声称掌握全部的真相。这就需要一个开放多元的思想与言论环境,才可能逼近真相。我的责任感首先来自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比如如何理解中国的转变,理解自己与环境的冲突。我期待成为这个巨大转变的重要记录者。
记者:在没有比较成熟的制度环境下,基于某些妥协而达成的共识,结果可能会导致你所说的“庸众的胜利”。这也是你一篇因批评韩寒而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的题名。
许知远: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紧张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它也必然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在“五四”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一直共存。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鲁迅则感慨吃人血馒头的麻木。
我觉得韩寒们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他们是一个舆论场中的弄潮儿。我从未否定他们的作用,只是不那么欣赏其中的浅薄。我对于韩寒的现象没什么可说的,它已被过度谈论,实在没有什么探讨的空间了。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