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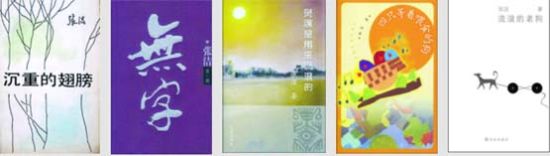
张洁是新时期以来国内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几乎获得了国家级(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所有的文学奖项,被誉为“大满贯”作家,她也是国内唯一的两度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无字》。上世纪80年代,她还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近年,张洁在写作之余游走世界各地,她尤其喜欢只身一人,像个背包客,到一般人不去也不愿去的小地方。她深入到异国城市或乡村的细部,与陌生人交谈,并成为朋友,她希望寻找、发现世界和人生中被人忽略的细节和光彩的一瞬。她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了这些旅行经历和感悟。《流浪的老狗》就是这样一本书。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地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在用自己的脚步叩击大地,就像地质队员用手中的小铁锤,探听地下宝藏那样,去探听大地的耳语、呼吸、隐秘的时候,或将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并力图穿越天宇,去阅读天宇后面那本天书的时候,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对于路上遭遇的种种,他一面行来,一面自问自解,这回答是否定还是肯定,他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是乐在其中。不过他是有收获的,他的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
“有些意义,是不能用戥子称量的”
兴安:能谈谈《流浪的老狗》的创作缘起和历程吗?为什么会选择老狗这个意象?
张洁:你难道不觉得这条流浪的老狗,多么洒脱?对待生活,我的态度可以说是吊儿郎当,或文艺一点儿说,是“潇洒”也无妨。基本不为世俗的价值所左右,基本,当然不是绝对。为何说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潇洒”?可能和我经历的太多有关,不论好、还是不好的,经历都超过常人太多太多,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有则好,无,也没有什么大不好,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人会永远站在舞台的中央,而任何挣扎都是丑陋的:当生命垂危、无可救治、还要为多几天生命而做的挣扎;为挽留不可挽留的爱情所做的挣扎;为优秀的后浪已经来到,而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为这个舞台留下一点光彩,还不肯退出舞台中央的挣扎……
记得有人棒打《无字》,朋友们极力建议我反击,我说何必?世上没有一本人人说好的书,也没有一个人人说好的人。一旦进入这个“自卫反击战”就得耗费很多时间。对我来说,认真写好眼下这部长篇,才是最重要的事。
兴安:非常想了解您人生新近的变化,生活状态、写作状态以及写作计划。您之前好像有写作童话的计划,是否有所进展?写作习惯是怎样的呢?
张洁:如果说人生新近的变化,只是进入了绘画的狂热。就像我从来没有学过写作,也从来没有学过绘画,居然前后卖出三张。第一张所得为没钱的公立学校做了捐献,第二张所得是为了帮助非洲难民。第三张是有个朋友十分喜欢,非买不可。我说送给他,他无论如何不好意思要,只好收了他的钱。
我已经写过一个有关儿童的长篇小说:《四只等着喂食的狗》,你瞧又是狗。我喜欢狗,觉得它们在某些方面比人类的品格高尚。除了绘画,目前正在写的是一部有关义和团的长篇。我很高兴自己有热衷的工作可做,而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什么是“无聊”的事情?你懂的。
兴安:《流浪的老狗》很容易让人想到您的上一本书《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为写作那本书,您在69岁的时候还专门登上秘鲁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能谈谈那段经历以及所获吗?
张洁:因为那本书涉及到印加以及玛雅文化,我必须亲身体验一下。本应去墨西哥采访,但秘鲁比较穷困,更能找到还保留着些许印加文化的、原生态村落。
那次采访很神奇,起始我并没有查看古代印加历史,不知道哪天是他们传统的、祭奠太阳神的日子,可我却赶上了。我不信仰宗教、也不信鬼神,但我总觉得已然在地球上消失的玛雅人,知道我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冥冥之中帮助了我。采访很困难,虽然秘鲁算是当年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在高原上几乎没有人说西班牙语,更别提英语。只得雇了一位懂当地语言的导游,费用不低。高原反应比较厉害,刚走到半途,就躺在山坡上不能动了,只能喘气,那位印地安人不安地看着躺在石头上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一会儿也就适应了。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上,找到一个印地安人的原生态小村,在那里住了一周。吃住上的困难都难不住我,自小就吃了太多的苦,那是难得的、应对困难的基础训练,所以说什么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但奇怪的是得了一种动不动就拉肚子的病,回国后,北京的医生说,你在哪里传染上了我们这儿已经绝迹的细菌?而且说拉就拉,毫无先兆,不论是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还是走在大街上,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使用儿童的纸尿裤。但那一行非常值得,那些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体验,我已经写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那本书里,有些体验真可以说是精彩。
同样,为了写《无字》我三次去到张学良做过抗日演讲的小镇,以及对很多相关人物进行过采访,比如到西安采访当年张学良厨师的女儿。
在秘鲁入关的经历也十分奇特,他们海关对我审查得特别严格,而且我还听不懂他们的英语,真不明白他们为何对我左右刁难,不肯轻易放我入关,出关时更加困难。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个通缉犯与我名字拼音相同,出生于1973年,而我出生于1937年。
兴安:能谈谈您所理解的流浪的意义吗?《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的人物“墨非”所进行的追寻毫无实际功用,书中认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是“世上最豪华的消费”,他身上是否寄放着您对于人生意义的特别理解?
张洁:说到“流浪”的意义,各人有各人的认同。我在书中写了那么一段话,你也许已经看过:“有人生来似乎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他们行走,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想来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许是寻找心之所依,也许是寻找魂之所系。行者与趋至巴黎,终于可以坐在拉丁区某个小咖啡馆外的椅子上喝杯咖啡,或终于可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走一遭,风马牛不相及。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地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在用自己的脚步叩击大地,就像地质队员用手中的小铁锤,探听地下宝藏那样,去探听大地的耳语、呼吸、隐秘的时候,或将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并力图穿越天宇,去阅读天宇后面那本天书的时候,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对于路上遭遇的种种,他一面行来,一面自问自解,这回答是否定,还是肯定,他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是乐在其中。不过他是有收获的,他的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
至于墨非的追寻,我倒要问:什么是有意义的追寻?对自己的理念、价值观(那本书中最突出的历史观)人生观等终极意义的探寻,难道不是意义吗?有些意义,是不能用戥子称量的。
“文学的价值,与被阅读的多寡没有太大的关系”
兴安:在新书中,您提到一个苏联女人的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政治,而非文学。您也曾表示,畅销书不是文学,您会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多数人喜欢而不是文学,好像文学对您来说,有特别崇高的位置,该怎样定义您心目中的文学呢?它和被阅读的多寡有关系吗?
张洁:我认为文学的价值,与被阅读的多寡没有太大的关系,世界上很多好作品至今阅读量并不大,比如我很喜欢的博尔赫斯,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过,博尔赫斯是精品,马尔克斯是大排档。这很正常,任何领域的顶尖艺术品,都是小众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我的文集时,我把《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三个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都删除了,没有收进我的文集。我认为它们够不上文学这个水准,好在责编杨柳女士很理解我的“怪”。我虽不是学文学的出身,但我对文学的敬意不可质疑。
兴安: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写作,这样一种很晚的起步,是否给您的写作带来某种影响。在开始写作之初,哪些人或者作品给了您很大指导或者启发。《北京文学》 杂志编辑傅雅雯老师今年故去,能讲述一下两人的交往细节吗?
张洁:我的创作起步晚,是社会条件的限制。即便我开始写作后,当年也是举步维艰,比如为了《沉重的翅膀》我几乎进监狱。如果不是邓力群同志的干预,我肯定进去了。为那部小说受过的种种迫害,我的德文译者阿克曼先生说,简直可以再写一部《沉重的翅膀》了,好在那些事件都已记存在我的日记里。
我的第一篇小说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骆宾基先生一看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鼓励我投稿《人民文学》杂志社,但被该社王扶女士退稿。于是我便死了当作家的心,不想再试投其他杂志。而骆宾基先生一再让我相信他的判断,说那绝对是一篇好小说,让我再转投《北京文学》杂志。小说得到了傅雅雯老师的欣赏,她把那篇小说放在了那期刊物的头条,小说发表后即得到了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而后她也时常对我的创作进行鼓励,我们常常到彼此家里互访,当我因《沉重的翅膀》受到极大政治压力时,她是同情、支持我的人之一。后来那篇备受当时某些批评家批判的、大逆不道的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的。《北京文学》是北京很多作家的始发地。
兴安:您如何看待名声?会格外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吗?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表决名单里有巴金先生和您的名字,但您一直没有透露这个消息,国内的传媒也对此几乎没有报道,这种态度是你特意选择的吗?
张洁:谁能不喜欢名声?我也不例外,但要让我为此付出自己的尊严,我就得衡量衡量。不是没有经历过名声和尊严的取舍,最后因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失去了很多有关名利的大好机会,但我并不后悔。
1986年被诺贝尔奖提名,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提名而已,没有真的当选就不能算数。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如果你只是穿上了婚纱,只要没戴上那只婚戒,你都不能说新娘就是你,否则就变成了不自尊的吹嘘。
1992年我被选举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电影奥斯卡奖就从属于这个组织。院士只授予美国公民,非美国公民是荣誉院士,全世界只有七十五位,不仅有作家还包括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家。终身制,逝去一位,进补一位。被选之后的两周,他们就给了我一个绿卡号码,而我多年后只在老得站不动使馆外那长长的申请签证的队伍后,才去理会这个号码。
2012年又获得了意大利托斯卡纳论坛奖,这个论坛继承的是古罗马遗风,不限于作家和文学,还包括学界、理论、新闻、金融等方面的专家,会上自由发言、自由辩论,很有意思。回来后有人问我要不要宣传,我说,没什么可宣传的。由于《无字》在意大利的出版发行获得了很大效应,以致意大利外交部邀请我(我还保留着这份邀请函)为2009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八国高峰会议撰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也参加了该会。我想,他们之所以邀请我撰稿,是因为他们看懂了《无字》的内涵,而没有把它仅仅看做是男男女女床上的事。这些事我也从未对新闻界披露过,如若不是今天谈到这个问题,我也不会谈到。
“《无字》除了是文学外,还是一种责任”
兴安:这些年您的写作一直试图在做着各种突破和变脸,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探索的热情的?您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何处?
张洁:如果人家说你有自己的“风格”,我不认为是好事,相反是画地为牢。所以我害怕形成“风格”,总是打一枪换一个窝,当然我还是有重复自己的地方,这说明自己的水平还不高,但我将不懈地为此努力。至于驱动力,很简单,就是热爱。人活一世,有件值得你热爱并投入全部精力、热情的事情,真是幸运。
兴安:您说过您真正的写作从《无字》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张洁:之前的写作,可以说是练习。因为我在大学读的不是文学系,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作,开始写作时毛病很多,比如重复自己、大长句式(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物美价廉的题材……我一再努力改正,加上读者以及评论家对我的宽容、鼓励,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每一步都是对自己的提升,之后我才能动手写这部大书:《无字》。
《无字》除了是文学外,还是一种责任,一种并没人交待于我的、自找的责任。1982年访问美国时,发起中美作家会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顾问诺曼·卡曾斯先生对我说:“我们很欢迎你留在美国,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工作和住处。”我回答说:“听起来真不错,非常感谢您的厚爱。遗憾的是我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必得完成,那是我对历史的责任。”有人肯定认为我矫情,放着这么好的便宜不占。可有什么好得过我矢志要完成的《无字》?!这是我开始创作时就立下了的“雄心壮志”。
20世纪是一个大谎言横行的世纪,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中国人),是一个上当受骗、充满比死亡还痛苦、还可怕的世纪,我有幸(或是不幸)地经历过其中主要的成分,而且自信还有能力描绘出这个画面留与后人评说。为这个重大的责任(我自己封给自己的),我投入了十二年的时间,走访了很多相关的人物,可以说,除非提供资料的人记忆有误,《无字》所引用的历史资料都有可信的元素。
此书在意大利出版后,一位作家代表一家报纸采访我,他说,这是一部哲学的、心理学的小说,在西方很多作家会把它们分开,这一段是小说,另一段是心理或哲学理念,你怎么能把哲学和心理写作、写得那么诗意?我无言以对,心想,你知道我这十二年是怎么过来的?!
兴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苦难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小说家因冲突与折磨而更有创作灵感,您认可吗?美国作家弗兰岑认为一个多产入世的艺术家,创造了自己的冲突与折磨,他认为如果有一段时期,他放弃写作去调和生活,或许他的婚姻可以存续。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否有过对文艺梦的反省,它或许影响了生活?
张洁:中国不是有句老话,愤怒出诗人?也许吧。但我认为艺术很大程度来自天赋。其他工作,只要努力总能有所成效,而艺术如果没有天赋,怎么努力也白搭。
我想我可能天生思路就有问题,在他人看来,我大概神经不正常,总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说是视觉不同也可。加上我母亲从来任我自由发展,没有约束过我。这样一来,我从小就是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进入社会之后领导也没给过好果子吃。这可能从另一方面造就了我。
所幸我改行写作,让我有可能不与社会有很多的接触。在生活中我是个非常笨的笨蛋,所幸我有一个好邻居,我所有的证件、钥匙都由她保管,重要的事务也由她把关,我想,很少人有我这样的幸运吧?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但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关写作的细节,记得有个细节不舍得用,等了十年,终于在短篇小说《四个烟筒》里用上。我经常为思考文学和绘画失眠,我女儿开玩笑说:您还真当您是毕加索呐?我说,我当然不是毕加索,我也不想做毕加索,但我有与毕加索同样的、追求艺术的疯狂。所以男人跟我离婚,肯定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但把创作摆在了家庭之上,还既不会做女人、也不会做女人应该做的,哪个男人受得了!如今,当我看到有些夫妇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磨叽来磨叽去的时候,就心中暗喜:幸亏我没有了这种家庭之累。
兴安:您在新书中也有几句抱怨评论家看待《无字》的角度,认为反而是一些意大利人理解了它,您也不愿意给自己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认为,小说的评论者是最孤独的读者,因为他们需要最特别的路径。您认可这种观点吗?如何看待文学评论的价值和意义?
张洁:有些评论家的文章给我很多教益,我很愿意接受他们诚恳的批评,因为可以改进我的创作,一句中肯的评论可能就有醍醐灌顶的作用,熟悉我的评论家和朋友都知道,我从不讳疾忌医。我有一幅绘画,有个朋友提了宝贵的意见,他走后我立刻撕掉了那幅画,而不是修补它。大家知道,油画是可以不断修补的,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对,修补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而有些评论也许为了保护我,只得把《无字》往男男女女的故事上拽。我羡慕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和评论家的关系,他们是诤友。可是这样的关系,如今已经难找到。
说到女性主义,我认为女人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女人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不仅仅是社会或男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费时,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记得我在法兰克福一个女性主义的会议上论述这一观点后,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炮轰。还有一次与意大利作家讨论文学,一位女作家又因为我的这个观点,非常愤怒。最后我说,今后我再参加这种讨论,我就是傻瓜!但与会的男作家都纷纷与我握手。
“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件事像热爱写作这样”
兴安:很多小说家的作品在某个层面,都倾向萃取自己人格某些特质与成分,然后从笔尖创造出一个角色来,您是否是这样的小说家?您的小说中是否有一个原型人物,您试图通过她做怎样的表达?
张洁:如果把音乐家、画家、文学家等等,一生的作品综合起来看,都可以说是他们灵魂的自传。但每部作品,绝对不能只有一个原型,那样的创作太没有开展的余地了,有那么傻的作家吗?
说到这里,我得提提《无字》中的男性。比如顾秋水,当东北军把所有的武器都留给了延安,在离开延安的前夜,他把留下的枪一一揩拭,一面揩拭一面嘴里念叨着“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写到那里,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些都是靠平日的观察和积累。我从来没有真正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连睡眠中都在写作。他们那个时代的男人(不知如今这个时代如何),很少对女人负责,但并不等于他们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作为。我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阅读的,怎么就看不到作者在大是大非上对那些男人的肯定?包括男主角胡秉宸。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即便一个强盗,也有我们所不知的或许是感人的一面,但不等于他犯了罪不必伏法。至于文学中的人物,更应该展示平时为人忽略的这个道理。遗憾的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惯性难以改变:非黑即白。我甚至想,这种观念与我们民族对颜色的感觉不无关系,我们的颜色总是正红、正蓝、正绿、正黄……没有过渡色,这叫做有颜色没色彩,而法国人的过渡色何其多也,这叫做色彩,而不仅仅是颜色,难怪他们常常引领艺术潮流,人们一定程度上认为那里是艺术之乡并不为过。但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法国人办事没准头也是常事,你如想在九点约见他们,必须说成是八点半,迟到半小时于他们是常事。
兴安:从一个人的儿童时期,往往能看到灵魂的潜伏期的形状,您的童年经验对你日后影响大吗?
张洁:当然有影响。我说过,肉体上的擦伤容易恢复,很多人是无疤痕体,而灵魂上的擦伤,永远无法治愈,直到它被一起带进棺材。
兴安:是什么促使您写作,还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庆祝方式吗?
张洁:当然是因为热爱。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件事像热爱写作这样,当然现在还包括绘画。庆祝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方式?只是与母亲相视泪流。
兴安:您希望你的作品对别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写作会改变他们吗?
张洁:希望那些热爱文学的读者,读得懂我。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小时代”的时代,我们的书绝对不能影响谁了,但我相信还有不多的几个读者,能懂得我。这就够了,人生难得几个知己?
兴安:哪些作家或者艺术家对您产生了深刻影响,你喜欢的画家是谁?如何理解绘画和写作的表达的不同?
张洁:喜欢的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高尔斯华绥、博尔赫斯、杰克·伦敦、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特等等,太多,不一一列举了。画家喜欢过渡于传统和现代派之间的皮萨罗,还有埃贡·席勒、并不喜欢太传统的画家,讨厌宗教画。
兴安:您的作品中对待爱的态度有着时间上的鲜明对比,爱恨皆浓烈,当下,你如何看待爱与婚姻?
张洁:我不认为婚姻就是两性爱情最好的、唯一的方式。“日久”可以说是催生审美疲劳的、无法逃避的毒菌。至于浓烈的问题是性格使然,对很多事物我都是加倍付出。前面已经说过,比如对绘画、对文学。
兴安:作为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非常活跃的作家,您如何回忆这两个时代?
张洁:什么是活跃?出品的数量多就是活跃?思维从未停止。出品不多的缘由当然有,但我不敢说,否则非得让人灭了不可。《流浪的老狗》虽不是小说体,但表达了我的很多思绪,甚至是一些基本的准则。关于小说的创作,我在参加意大利举办的威尼斯世界文学节上有个发言,可能能解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所谓活跃。可是太长了,不便引用。
兴安:回忆此生,您是否有过什么遗憾?如何看待死亡?会因此恐惧吗?
张洁:严肃的回答是: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把我剩下的生命,分于母亲一半,最好比她多一天,等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我再从容地离去。玩笑的角度回答是:结了几次婚,却没有穿过婚纱。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可以补穿后再去拍个婚纱照。我说,可以倒是可以,但你的脸、你的眼神,还是当年的那张脸、那个眼神吗?
我从未害怕死亡,花开花落自有时,你怕又怎样?不如坦然面对。记得有次医生查出我有癌症的可能,在等待复查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死前能否完成《无字》,并且想一定不能告诉女儿,她会非常伤心,反正我在北京,不告诉她,她是不大容易发现的,至少尽量拖延被她知道的时间。
我做过几次手术,因为老了,脊椎间隙变窄,麻醉针很难进入,主治医生只好亲自动手,他后来对我说,这是很疼的,你怎么一声也不哼?我说,如果我哼了之后不疼,我肯定大哼特哼,如果我哼了之后照样疼,我又何必哼哼?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人生哲学?我害怕的是不能咔嚓一下就死,而是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依靠他人,那太可怕了。我甚至打听到,世界上只有瑞士可以安乐死。为什么不可以安乐死?这是关乎人道、人性的大事。
兴安:您多次表达过,人与人之间不可沟通,为何有如此失望?
张洁:错,这不是失望,是面对现实。想想看,你这一生被人理解的有多少?连自己有时都不理解自己,何况他人。任凭你说破大天,人家能理解百分之几?说起来似乎很玄。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