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野夫: 我厌恶一切帮凶文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0月14日09:43 来源:深圳晚报 崔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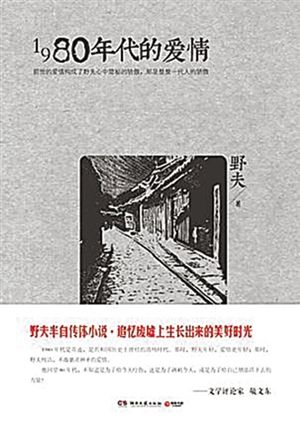
 《身边的江湖》 《80年代的爱情》 《乡关何处》
《身边的江湖》 《80年代的爱情》 《乡关何处》野夫行走江湖多年,最近又出新书了,《身边的江湖》和《1980年代爱情》。我立即去买了回来。当初在飞机上看他的《乡关何处》,震撼又感动,看得泪水涟涟,路过的空姐停下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次,《身边的江湖》依然延续了他在上一本书中为亲友写列传的散文风格,那些人的命运轨迹依然让人唏嘘不已。不同的是,在看这本书时,我居然也笑了很多——野夫写他的朋友,有沧桑,有无奈,也有传奇,但更生活了,似乎你身边也有这么一群人真实存在着。而《1980年代爱情》这本半自传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为了让心爱的男人看见更辽阔的天空,一直拒斥爱情的故事。
采访野夫时,他很客气地回复我,还在德国,只能邮件采访。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篇文章。
性格决定了我
在很多时候的选择
深圳晚报:很多人觉得您是一个传奇。行走江湖半辈子,当过警察、坐过监狱、搞过出版、写过书,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您的命运轨迹,是否觉得是性格、选择造就命运?
野夫:如果人生没有宿命预设的话,那么命运则多半是性格造成。每个人平生都要面对很多艰难的选择,一念之善和一念之恶,都可能带来生死悲欢完全不同的后果。就像哈姆雷特式的选择一般,性格最终将决定其行动以及命运。而性格这个东西,一半是遗传,DNA的密码决定的;一半是后天的影响和教育。转顾半生,我自知性格决定了我在很多时候的选择——是不记功利得失的。如果自问站在了正确的一边,那也就可以笑对厄运了。
深圳晚报:您几乎在每一本书中都提到家乡利川的小镇,有老街、江水和吊脚楼。让人想起高密乡之于莫言,香椿树街之于苏童,是否作家都对幼时生活的地方和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以至于书写背景都建立在那里?对您来说,一直强调的土家族身份又意味着什么?
野夫:至少到我们这一代,还都是有故乡概念的。童年说着本土的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交往着熟悉的乡邻而不是互不往来的小区邻居。各自在一方文化的水土中浸润长大,对人和世界的认识都来源于那个母土。因此,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写作者之时,他往往会以那样的背景地为他的文学舞台;这是经验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虚构领地的一个原生林带。小镇文学,几乎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坐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笔下,也都经营着那样一个或真或幻的集镇。至于我,本身也成长于那样一个土家族小镇,我选择了父系的这样一个民族身份,是因为我喜欢古老的巴人曾经的烈性。巴国很早就覆灭了,但巴文化一直隐约在民间传承。
深圳晚报:我是在飞机上看的《乡关何处》,实在被震惊到,尤其写外婆的那篇,似乎外婆对您的影响最大?
野夫:确实是这样,我一生的教养来自于外婆的更多,情感上对外婆也特别深厚。她是民国初年读过一些诗书的女性,她的父亲又是留学日本学法科的那一批早期海归。外婆的故事,其实我远远没有讲述清楚。最近我正在整理我母亲的遗著——她写的关于她母亲(我外婆)的回忆录,我才从母亲的回忆里,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外婆一生的善良和苦难。
江湖气并非脏污的品质
深圳晚报:在您看来,江湖是什么?真正的江湖精神又是什么?在这种江湖精神的流传当中,是否随着时代变化也发生了变化?
野夫:我对此说过,江湖就是广大的民间社会,是廊庙“体制”之外的草根世界。真正的江湖精神,早在战国即已形成,墨子的言与行都赋予了江湖的核心价值观——扶弱抗暴,兼爱非攻。江湖不是被污名化的黑社会,也不仅仅是传说中的道门、帮会和社团。江湖是底层人民自治自立的世界,是传承古老道义且抱团取暖的弱者的生存门道。在一个完全体制化的时代,江湖精神当然会被挤压和削弱,也会发生一些与时俱进的变化。但根本上说,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真正根除民间社会“江湖”,也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其存在,甚至尊敬其中很多值得肯定的正能量和道义。
江湖气在我看来,并非一个脏污的品质。传统的江湖都是敬五伦——天地君亲师,重五常——仁义礼智信。当然,这样的江湖气,在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难免会受伤。如果一个人在他的青春坎坷中,都没有被打磨成圆滑世故的小人,那他肯定不会在知天命之年后,反而改变他身上的特质。
写作是偿还情感的债务
深圳晚报:能看出来,您在写作时有一种情感的节制,尤其写家人时,这是您在写作时刻意为之么?
野夫:写亲友故事,第一原因是情感的债务,你需要偿还。每个人都是母生父养的,都会在亲人远行之后留下万千遗恨和遗痛。尤其我们这一代的上辈,更多都是血泪斑斑的生涯。你不把他们写出来,他们就像不曾来过今世一样,无辜地消亡在时光背后。第二个初衷是为了历史,历史多数时候是帝王史政治史,是被篡改和遮蔽的宏大叙事。但真正的历史,却是万千平民的生活史,没有这样一些家族故事,我们根本无法窥见这个时代的来历。那这样的写作,不仅仅是我私人的抒情回忆,是对家国历史的一种检讨和审视,我当然需要节制个人情感,需要以更加理性的视角,来打量一个世纪的变迁。这是对自己情感压抑的救赎,也是对被淹没的国史的一种揭示。
深圳晚报:写身边的人其实很难写,想起来前几年读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也是写身边的人物故事,但是吴的感觉有点小温馨,像冬天的火苗,唏嘘的同时更多留下美好,但看您的文字,却像是冬天里凛冽的寒风,个个是行侠,倔强、孤独又悲壮,始终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我理解还是时代的差异造成这种区别?
野夫:吴念真先生是彼岛的文学前辈,是我尊敬的作家。四川学者李亚东也曾经拿我去和他进行比较,我和他的共同之处是,都写了一批身边的草根人物,都以真人真事来让人感动。但毫无疑问,看起来我笔下人物的命运似乎更为惨烈。这种差距实际来源于故事的背景地的不同,即便在彼岛的戒严期,社会也并无那么多可怕的运动等等……
纪念那个干净和纯情的岁月
深圳晚报:《1980年代爱情》您是写于十年前,却在十年后的异国他乡修改,请问再次修改重新看那时的文字,心境有什么不同?
野夫:这个故事压在心头更久,十年前写的是剧本。因为电影脚本的限制,只需要对话和动作,是无需任何描写议论和抒情的。那是第一稿,自己本不满意,因此一直放着发酵。十年的沉淀,青春渐逝,在异国他乡重温这个故事时,依旧发现它的美好。于是决定改成小说,让自己淡定地娓娓道来,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年华。我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更多80年代的时代痕迹。
深圳晚报:《1980年代爱情》让人想到几年前很火的《山楂树之恋》,只是因为那个年代你们正年轻?
野夫:无论是山楂树的60年代,还是我的80年代,毫无疑问都迥异于今天。应该说这两个年代,也并非完全美好的年代,尤其是60年代。至少对我来说,那是我的青春,是一个值得我追忆和祭悼的时代。我在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我心中同时是在纪念那个干净和纯情的岁月,以及我们那一代曾经的奋斗和牺牲。
深圳晚报:您下面还是会继续写“江湖”人和事吗?或者您是否有长篇情结,以后写一本以利川小镇为背景的小说?
野夫:我的江湖故事还装着太多,都会在未来慢慢写出。同时,我也是在写一个利川小镇背景的长篇小说——这个会更沉重,也更有意思吧。
愿与天下真与善男女杯酒订交
深圳晚报: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您提过对母亲当年自我结束生命的选择理解,是让您前行的一种方式,这个似乎和丽雯的拒斥爱情让关雨波前行有点类似,请问现在是否认同书中的那句“不要为路边的花停留,沿着你的道路向前走,鲜花将不断开放”这句话?以您现在的心态看,还会做出关雨波的选择吗?
野夫:这个问题,是真的难以假设。每个人一生都会错过很多情缘和机缘,你无法将走过的人生重新回头再走一遍。甚至更不能去假设如果如果又将如何,爱情是梦话,生活是绳扣,一个可以塑造完美爱情的作者,却未必能解开全部现实生活的绳扣。
深圳晚报:从您的文字看出,您很敏感,家族观也很重,但是您也很赞同朋友对您“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这一评价,很容易理解“一流的朋友”是“江湖气”,但“三流的丈夫”这一说法跟您很浓的家族观有点矛盾?
野夫:家族观和婚姻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家族是血缘关系,是不能选择的注定。婚姻是水缘关系,是无数种选择的可能。家族遗传的是血,婚姻交流的是水。一个家族观浓厚的人,并不一定是婚姻观最注重的人。
深圳晚报:可以谈下您现在的生活方式大概是怎样?交友呢?
野夫:恶习如故,失眠好酒。至于交友,一向是愿与天下一切真与善的男女杯酒订交。
深圳晚报:单从文字来看,似乎您的兄弟很多,实际生活中您的女性朋友应该也很多吧?您怎么看待婚姻?
野夫:实际上还是哥们多。婚姻嘛,是多数正常人应该走的人生程序,但没有也不是过错。有过了的可以再有,也可以不再。戏改老话说——有则加勉,无则改之。不改也不违法。
深圳晚报:您很喜欢沈从文、王朔,理由是什么?您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野夫:沈从文先生是我们那个文化故乡的先贤,影响了我最初的文学品味。王朔是很真实且很有立场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还很好玩。我喜欢很多作家,我不是那种文人相轻的人。我不喜欢的作家,那就不是相轻——多半就会是厌恶,我厌恶一切极权的帮闲和帮凶文人。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