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雷颐:学者就要有一种公共关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8月26日15:45 来源:南方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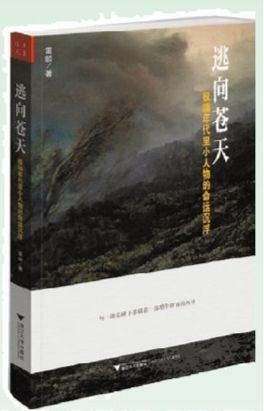 《逃向苍天》 雷颐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定价:32.00元
《逃向苍天》 雷颐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定价:32.00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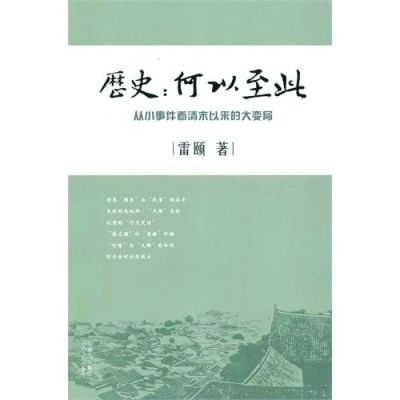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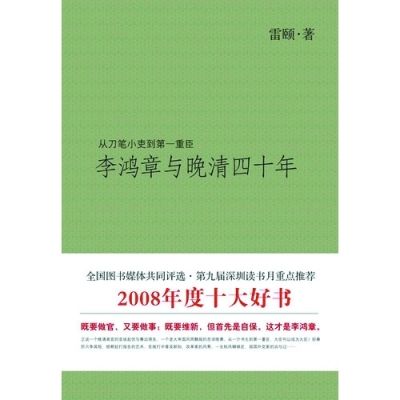
■核心提示
先后当过知青、军人、工人,然后,赶在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那年考上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既往的经历让他在做历史研究时,并不愿意仅仅以宏大视角进行论述,而是更为注重从小事件、小人物入手。由此,他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端:既会研究“五四”历程,研究胡适、傅斯年等那批最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大众的人民生活那一端。
雷颐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对这句话深有感触的雷颐在今年春天,出版了一本关注极端年代里小人物命运沉浮的书,这本书取名为《逃向苍天》。
在北京丰台蒲黄榆附近的一间上岛咖啡里,雷颐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这里是咖啡馆的禁烟区,他挥挥手告诉记者他不吸烟。话题是由这本新书展开的。
他的时间被很多事情塞满了,第二天就要奔赴四川成都,在一家会所里做一场关于晚清改革的演讲。
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深深影响了他的历史研究,也让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敏锐的认识。与沉溺于书斋的学者不同的是,雷颐也在寻找与大众之间的接口。
在他看来,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近些年来,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写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写专栏,也开设大众历史讲座,有人说他就差上《百家讲坛》了。他说,他不在意场域的大小,报酬的多少,只在意能不能酣畅淋漓地表达观点。
◎人物名片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要著作包括《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逃向苍天》等。
大时代裹挟中
小人物难以主宰自己命运
南方日报:将茨威格所写剧本的名字“逃向苍天”作为您这本新书的书名,有什么隐喻?
雷颐:《逃向苍天》是茨威格根据托尔斯泰晚年出走的故事所写的一个剧本。这段“历史特写”,深刻揭示了托翁思想的矛盾与内心的剧痛。我比较喜欢这个故事的隐喻,有几层意思,第一,以中国近代为例,有人说应该告别革命和激进主义,当然“理性”很好,但有时就是不改,革命就很可能爆发,由此带来的血腥场景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最典型的就是“戊戌维新”,很多人希望清政府改改,但统治者就是不改。这也是无解的。第二,这本书谈的是,在大时代的裹挟中,小人物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有的顺应它,有的成为推波助澜者,有的只是为了活下来,最后只能听天由命。这也就是“宿命”了。
南方日报:通俗历史读物中有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之分,文学家著作的优点是可读性强,然多不可信;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
雷颐: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历史学的著作。里面的内容都有出处,尽量让史料本身去发声去表达,不能有文采不能有渲染。比如里面提到的叶圣陶的例子,只是在陈述事实。叶圣陶在政治裹挟下有自己的难处,在批胡风时,他不得不批,又不能完全违背自己的良心,于是颇费一番苦心地写到,他看过胡风的文字但不了解,他是读了一些人的批判文章才认识到胡风有“多坏多坏”。我不能有自己的发挥,而是交给读者去判断,读者做出怎样的判断与自己的阅历有关。前段时间,我接到了很多个岁数比我大的朋友或者读者的电话,他们说看到叶圣陶那篇太好了,说他们都有相似的经历。然而,年轻人看了恐怕没什么感觉,他们不能感同身受。
南方日报:这本书中有很接地气的人物如农民梁书香、初中生何榕森,其他如程贤策、老舍等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小人物”。选择这些人作为个案经过了怎样的考量?
雷颐:当然里面不完全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是相对而言的。从前写历史的,人们写到近代史往往就会写李鸿章、袁世凯,写清王朝;写到当代史的时候会选择毛泽东等。而我这本书选择的人物不是政治性的领导,是凡人。比如乐黛云,虽然她现在作为汤一介的夫人名气很大,但在当年就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青年教师,是小人物。我在书里主要描述的是这些人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的思想变化,以及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那种宿命感。
“档案”文献之外
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
南方日报:您说您以前做历史研究往往着眼大的规律,后来自1998年起就开始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最为重要。这种历史观的转变缘于哪些因素?
雷颐:可以说是慢慢的积累,然后突然形成一种很清晰的认识。在这之前,也包括现在我也还在做一些比较大的方面的研究。我曾经是一个下乡知青,在河南插队了四年,到了农村才知道农村多苦,这是我的经验。可我在1990年代看到有些青年学者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历史运动时,往往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公开言论,有关事件的宣言、主张、纲领等“文本”信以为真。我觉得这样很荒诞,然后再仔细一想,曾经我也没想过这一点。后来我在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研究,研究到1953年时注意到,那时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为了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然而,这只是从国家视角抽象地谈,没有说政策实行后对农民和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后来我写了篇文章整理了思路,认为“日常生活”纷繁复杂,很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而在“档案”文献之外,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于是我搜集了很多资料,各种回忆录。比如梁晓声就写了很多关于知青生涯的文字。不过写来写去,这段历史大都是城里人写的,恰恰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有发声。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就写了一篇文章,是从农民梁书香的故事入手的。
雷颐:对。为什么我很注重辽宁农民梁书香写的回忆录?我很早就写过文章说农民没有历史,农民自己都不写。她看了我的文章,就尝试着写了一本《难忘岁月》,而且是自费写的。我把那本书称作“原生态农民生活史”,虽然写得很粗糙,但从史学角度看反映出她没有经过什么加工,比较纯粹一些。那是纯粹的农民写出来的。我总是强调让我遗憾的一点,在历史话语权力场域中,“农村”是彻底的弱者,甚至可以说“农民无历史”。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没有记录,便无“历史”。
南方日报:那您在做小人物的历史研究时的史料来源有哪些,如何甄别?
雷颐:主要是从大量的回忆录中互相佐证而来。我搜集了很多知青的回忆录,虽然有的知青的回忆录透露出了瞧不起农民的心态,但也有知青当上了小队干部,从不理解、不了解农民到同情、从而开始帮助农民。有的知青在生产队当了会计,在向上面报账的时候帮助农民瞒产,这样农民就可以多分到一些粮食。类似这些史料在回忆录中都能搜集到。有的时候,经过一定的技巧和史学方法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佐证。陈寅恪说过从诗中可以发现史,“以诗证史”,从诗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互相映证。
南方日报:谈到知青文学,您曾经针对知青文学有过一个观点,将其形容为“拍卖苦难的劫后辉煌者”。
雷颐:对。从1979年很是热闹的“伤痕文学”一直到现在,城市插队知青写了太多太多作品,关于农村,有多少小说?只有一本就是路遥的《人生》。我在下乡时特别感受到农村青年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想成为城里人,但最后很多人都铩羽而归,大败而回。路遥是个农村孩子,他是后来上了大学,是奋斗成功人士,但他理解这一代农村青年,恰恰是路遥写的高加林的文学形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乡青年的典范。这些故事在历史教科书上是没有记载的。
“唯文本”阅读
是当前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
南方日报:您个人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于您的史学观产生了什么影响?
雷颐:那段生活经验恰恰能与我所学到的理论相结合。举个例子,经济学中有个很热门理论就是科斯的“制度经济学”,谈的是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纯粹的生产方式发生的改变,而是制度层面的变化。这段内容让我马上想到我在农村的经历。
在当兵之后、上大学之前,我都曾经回到过此前下乡的地方,那里的农民最羡慕的是城里人,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天天吃白面,这种状况多年未变。但在我上了大学的那两年,正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撤销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政策开始推行。在1981年,我很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农民都吃上了白面。尽管他们的生产工具还是此前的那几样东西,但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变化。“制度经济学”学起来很复杂,但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我立刻就能联想到农民生活因为制度改善而发生的变化。它变成了一个很容易消化的概念。
南方日报:您刚才同时也提到了一些学者“唯文本”阅读,您曾强调过这种趋势愈来愈严重,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为何感觉这种学风日趋严重?能否具体谈一谈。
雷颐:“唯文本”阅读的学风自古以来就存在,我自身感觉,这种学风从1990年代开始越来越严重了。从那时起,我发现国内的一些年轻学者,或者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史学研究上只找过去的一些报刊资料、或者是一些文件作为他的立论根据。在我看来,我主张的是要透过文本,看到背后的结果——这才是最重要的
南方日报:随着当下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在记录影像资料方面的情况应该有所改观。
雷颐: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全国能拍纪录片的只有类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这样的机构,连照相机都很少。而影视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因此我想,会不会过了300年之后,当后人查看一段历史时,只能找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些资料。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在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终于打破了权力对“历史影像”书写的话语垄断。对此,我曾经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数码时代的历史书写》的文章,指出以后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许多多不同角度的“记录”。就连我家附近收废品的也有摄像功能的手机了。在“手机随身拍”的时代,如果谁仍想垄断对重大事件的影像记录与阐释,终会感到无可奈何。
我希望
读我文章的人越多越好
南方日报:有人说你开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开设大众历史讲座,就差上《百家讲坛》了。那你有考虑去上类似《百家讲坛》的电视栏目吗?
雷颐:如果能让我完整表达我的观点,上电视栏目是可以的。平时我做讲座比较多,我觉得讲座是一种交流,也是对自己历史观的一种宣传,挺好的。公共讲坛也是这样。前两天我去立人大学(一所基于互联网的民间“大学”)给他们讲课,发现来到这里听课的年轻人求知欲非常强,这很难得。我觉得学者就要有一种公共关怀。这类场合尽管人数很少、没有报酬,我恰恰能敞开着讲自己的观点。这才有意义。
南方日报:您平时也写一些专栏,那您对于自己的读者有哪些期待?
雷颐:我希望读我文章的人越多越好。批评或赞成都无所谓。
南方日报:您在写文章时,会有启蒙意识吗?
雷颐:有一定的。包括去做讲座,如果没有启蒙意识的话为什么要去演讲呢,开个学术讨论会不就完了。
南方日报:您在博客和微博上很活跃。遇到言辞激烈的网友的话,您会生气吗?
雷颐:的确也会有一些人在微博上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公共交流,是良性的互动。当然也会有人来骂,我也会对此表示反感。不过,我已经基本上不会在意这些问题了,觉得无所谓了,看一看笑一笑而已。如果我说了句事实,有人来骂,那我就知道这句话正好击中他的要害了。从他骂我,我可以感觉到一个词:气急败坏。这就可以了。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实习生 吴晨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