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苏童: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美好关系,其实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8月05日10:12 来源:羊城晚报 傅小平 本报资料图片 邓勃 摄
本报资料图片 邓勃 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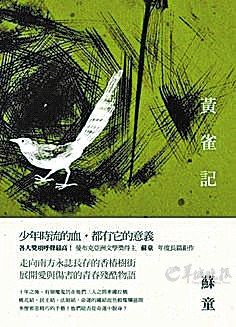 《黄雀记》台湾繁体字版封面
《黄雀记》台湾繁体字版封面关键词:1
造街
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
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
傅小平:读《黄雀记》通篇没有读到“黄雀”,但书名呼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谚语,有着非常严肃的主题——关注青春期成长等社会问题,但显然又体现了更为宏大的关注和追求。请谈谈你写作的缘起和过程。
苏童: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以前的好多中短篇文本,包括九十年代的长篇《城北地带》,都是“香椿树街系列”,都是我造的街景。而这次的《黄雀记》,是“造街行动”的一项大工程,我为这条街道修建了一个广场,还有一座隐隐约约的庙堂,更多的居民停留在此,献上他们卑微的香火,以及卑微的祈愿。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
傅小平:从某种意义上看,白小姐是小说故事的诱因。你的女性人物群像,也由此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调。事实上,你正因为写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而为人称道。
苏童:我从来不认为我善于写女性。假如你没有写出《包法利夫人》那样的经典,假如你没创造过爱玛这样的女性形象,你不可以认为自己擅长写女性。
说到《黄雀记》里的白小姐,那大概是我作品中最接“地气”的一个女性形象。从仙女到白小姐,是同一个人随时代分裂整合的形象。她的身上集合了人与社会的诸种矛盾,在创伤中成长,还未能遗忘创伤,未能解决矛盾,已经随波逐流,与现实握手言欢了。
当然,我也不会贸贸然告知我对女性总体的认知。在社会学的性别研究领域,一切都可以统计概括,而小说不同。我依赖小说观察女性,小说不研究整体,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都要进行个别的一对一的认知。
傅小平:你的小说里通常都有一个像保润爷爷这样的人物,比如《妻妾成群》中是陈老爷,《河岸》中的父亲库文轩等。他们一般不是主要人物,但作为小说不可或缺的结构元素,作为一种背景、氛围存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写作的惯性使然,还是源于你的某种心结?
苏童:你提到的那个父辈的或者说暗指权力的形象,在我作品中的功能其实也有所分工。《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着墨不多,他更多是男权与封建的象征符号,是颂莲们委身的树,也是缠绕颂莲们脖颈的藤。《河岸》中的库文轩则与儿子库东亮形成紧密的双主角关系,这个父亲形象,本身寄托了一部分社会、政治、人性主题的诉求,他与儿子既紧张又亲密的父子关系,是一种隐喻,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依附的伦理纲常。而《黄雀记》中的祖父,是一个丢失了一切的人,甚至丢了魂灵。他是一个受难者,更是一个预言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雀记》的背景是由一个人充当的,是祖父这个人,他俯视保润柳生和白小姐他们的成长,也是所有悲伤、荒诞或痛苦的旁白者。
关键词:2
控制
我只是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
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
傅小平:保润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角。他经受的冤案,连带着让一个家庭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深渊。出乎我预想的是,在小说里,读不到你的同情。保润出狱后也是乖戾而邪门的,甚至有点面目可憎。我总感觉在你笔下,很少能感受到你对被命运捉弄的小人物,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的同情。你是否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本相?
苏童:我自己觉得在保润与白小姐身上,我的同情心已经明显地流露出来了。我只是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
傅小平:这部小说最大的悬念是,保润的“复仇”。这对于他并没有什么难度,他尽可以做个痛快的了断。但在处理“复仇”部分时,你的叙述让保润看上去有些残忍,又有着某种温情。
苏童:毫无疑问,保润是一个有资格的复仇者,但同时也是个不成功的复仇者。他不是哈姆雷特,感官与情感主宰他的行为,而不是思考与理性。他不是天生的暴力爱好者,只是一个捆绑者。捆绑他人,对于他更多的只是一种习惯与爱好,或者是唯一的技能。这个人物身上残留了善良的天性,以及宿命性的空虚,他是愿意宽恕的,也准备与不公的命运和解。但正如我们对生活的观察,伤害是永恒的,宽恕是暂时的,而真正的和解非常艰难。
傅小平:隐藏在小说的深层,是关于罪与罚及自我救赎的主题。支撑起这一主题的重心在柳生身上。如果说小说受到了《罪与罚》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对照反差是否体现了你的某种思考?
苏童:事实上我在创作《黄雀记》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罪与罚》。但是在写完之后,我问自己,你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描述这部小说?我脑子里想起的竟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两部小说的名字,一部是《罪与罚》,另一部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但我必须强调,这两个名字仅仅从某个侧面描述了《黄雀记》的主题特征,其实要是换个思路,似乎还可以挪用果戈理《死魂灵》这个名字。柳生这个人物,来自我所熟悉的香椿树街街头,柳生不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无宗教信仰,无抽象的思考习惯和能力,他是以人情世故对待一切的,包括赎罪。他自以为无所不能,其实没有能力完成自我救赎,他所承受的“罪与罚”,因此也无可赦免。
关键词:3
写作
把写作作为了最重要的生命体征,
一旦放弃,会怀疑自己放弃的是健康
傅小平:这部作品在《收获》上刊出时,你删去了多达5万字的枝蔓性的细节,是不是说这些细节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必要?我因为没有看到足本,没法做出判断。但从写作经验上看,有些看似“不必要”的闲笔,却能为整个篇章增添特别的华彩。不妨由此请你分享一下“删除”的经验?
苏童:我其实很高兴有这一次机会,为一部长篇小说做一个剪枝版的后期。这是因为,自己给一个文本留下了两种阅读可能。剪枝与未剪枝的,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可以让一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去比较判断所谓枝蔓的意义。当然,我自己也将成为这些枝蔓的鉴赏与评判者。
傅小平:总体而言,评论界对你的短篇小说创作比较有共识,甚至认为你是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圣手”,对你的长篇创作却存在一些争议。最为极端的一种观点认为,你的长篇小说像是拉长了的短篇小说。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苏童:坦率地说,我不认同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背后不是对我个人作品的偏见,而是对短篇或者对长篇文体本身存在着偏见。偏见的本质是对长篇与短篇的容量、信息和结构方式,有了一厢情愿的量化标准。但无论什么文体,都不应该有什么容量标准和结构标准的。另外从技术上说,我也不认为一个短篇小说的故事,可以拉长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否则,读者应该读不下去。我在写长篇与短篇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搞建筑,唯一不同的是短篇建筑酷似一个亭子,长篇建筑酷似一座宫殿,材料有多寡之分,所耗费精力也不一样。
傅小平:很多天才的作家,在早期就写出了一生的代表作品,他此后的创作常为读者忽略,在文学史上也被一笔带过。有些作家比如胡安·鲁尔福等就比较洒脱,他大概对自己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很难再写出超越性的作品,干脆就放弃了写作。你如何克服写作的惯性,而力图有所超越呢?
苏童:金盆洗手,不一定立地成佛,何况什么时候洗手,是否成佛,都是悬念。鲁尔福是一个写过伟大作品的人,但很明显,他对失败的恐惧,远远大于对写作的爱,这样的作家生涯,有点令人生疑。我觉得一个作家写多久,有时候取决于他对成功的理解,有时候则仅仅取决于他是否足够热爱写作。很多人一生坚持写作,只是因为他把写作作为了最重要的生命体征,一旦放弃,会怀疑自己放弃的是健康。作为我个人来说,写作价值的自我评判很重要。在长篇方面,近期的《河岸》与《黄雀记》都比之前的那些长篇要令自己满意,这对于我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持续写作的理由,不需要别的任何理由支撑了。
傅小平:这部新作面世后,我看有网友感叹,这一回苏童总算胜了余华一局了。言下之意是在他看来,《黄雀记》总体上超过了《第七天》。你读过余华的新作吗?对于同时期出现的先锋作家如今各个不同的写作与生存状态,做何理解?
苏童:作家不是牙膏生产商,不必担心读者用了你的牙膏刷牙,就不用他的。喜欢文学的读者也不是歌星的粉丝,一般不会有什么排他性,所以,我也不觉得文学的市场存在那么严酷的竞争,都是各取所需罢了。《黄雀记》和《第七天》只是凑巧都在2013年完成,其实没什么可比性。我从不对媒体公开评价朋友的创作,这次,同样没有评价的理由。唯一要说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对余华始终充满由衷的敬意。
关键词:4
现实
是否维护读者推敲真伪的热情?
我不反对,同时也不鼓励
傅小平:在我印象中,你写的长篇,只有《黄雀记》如此切近地写到了“正在发生”的当下现实。这意味着你写下的很多细节,都会有读者拿来与他们正置身其中的现实一一对照。
苏童:《黄雀记》的写作没有预设“写实”或“超现实”的宗旨。说到表现手法,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在冒险。祖父爱找魂,保润爱捆人,都不可信,只是可行,我是在可行性中探讨人物与故事的意义,以及这意义衍生的能量。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所以,由此造成的阅读审美上的某些矛盾,我一并奉献给读者了。那么,是否要维护读者推敲真伪的热情?我的态度很明朗,不反对,同时,也不鼓励。
傅小平:很多作家写当下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妖魔化、荒诞化。比如你写到的暴发户郑姐、郑老板,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古怪的事件,就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我想,据此简单地批评作家无法把握现实会有失偏颇。这大约类似于西方绘画史上的印象派,作家们要摹写的是他们“看”到的、感受到的现实,未必是客观事实层面上的现实。但这样的真实往往不符合读者对“作家要直面现实”的期待。
苏童:对于作家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拥抱现实这个话题,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不妨再说一遍,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地“飞起来”过,更没计算过那距离是否符合三公尺的理想。
苏童,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作家代表之一。本名童忠贵,1963年生于苏州。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园艺》、《红粉》、《离婚指南》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河岸》 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黄雀记》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十八岁的保润与轻浮帅气的柳生都在香椿树街上长大,来自外地的少女仙女,与管理花圃的祖父母在医院生活。一起错综复杂的强奸案改变了这三个少年的一生。保润在水塔里一次失败的约会中捆绑了仙女,随后进入现场的柳生情不自禁犯下了罪行。仙女背井离乡漂泊各地以色相诱人,保润因冤被囚,柳生逃脱了法律制裁,却备受良心煎熬。
苏童说:“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是‘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所谓街区生活。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青少年强奸案,通过案子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说是这三个受侮辱与损害的人的命运,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