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因写作《出租车司机》,薛忆沩常被认为是深圳的代言人。
因写作《出租车司机》,薛忆沩常被认为是深圳的代言人。在书评周刊的夏季好书评选活动上,在场的一位嘉宾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城市文学?他拿出九九读书人不久前出版的《格兰塔》一书做反例。《格兰塔》是英国的一本老牌而又新锐的文学杂志,中文版从《格兰塔》杂志各期中摘选出18个有关英国的故事,以杂志书的形式出版,定名为《格兰塔:不列颠》。
或许,类似“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城市文学”这样的问题太过武断而刺耳,在我们的文学宝库中,关于城市的书写未必算少。远的有张爱玲、苏青、施存蛰、老舍,近的则有王安忆、陈丹燕、孙甘露、王朔、韩东、苗炜,还有近年来“重新”被文学界发现的“迷人的异类”薛忆沩……只是,当我们将“城市文学”放置到整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宏观视域中去时,我们必然能够同意,当代中国作家对于城市的书写,在体量上确实不能算多,在丰富性与深度上,确实也仍有待提升。
本期我们采访了薛忆沩,他为我们奉献了“深圳人”系列小说——“深圳人”是此前很少在文学上被加以整体探究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便借机,顺着“城市文学”的话题说了开去……
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1)
 薛忆沩,小说家,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90年代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2年起移居加拿大。薛忆沩近年密集在国内推出作品,获得学界和读者关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遗弃》、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Han Han Xue 摄
薛忆沩,小说家,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90年代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2年起移居加拿大。薛忆沩近年密集在国内推出作品,获得学界和读者关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遗弃》、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Han Han Xue 摄过去一年中,在书评周刊的编辑会上,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出现过好多次。我们当然并不认为中国缺乏城市的书写者,当我们讨论当代“城市文学”时,我们谈到了王安忆、陈丹燕等人笔下的上海,王朔、叶广芩笔下的北京,池莉笔下的武汉和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他们构筑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阅读记忆。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对微小的,它的声音是相对薄弱的。而对照当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事实,越来越多人正离开乡村、在“城市”这一生存空间上演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对于这一时代最剧烈且最具普遍性的变化,并没有做出足够及时、丰富和有力的回应。
当我们看到薛忆沩打着“深圳人系列小说”旗号的短篇集《出租车司机》时,我们自动调动起了阅读经验中有关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或白先勇《台北人》的存储,它们同样有着为一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代言的宏大视野。而薛忆沩的小说,也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打量“城市文学”,思考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良好契机——有关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它的历史、它在现下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或缺席,以及与它相关的诸多误解……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它无疑应被纳入“城市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它又确凿无疑地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城市文学”产生差参。在“深圳人系列”中,薛忆沩极少提到在众多“城市书写”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地标,也回避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记忆。在此,“深圳”成为一个面目不清的场所和背景,成为一种制造压迫和不安的来源,成为一个让作家笔下的许多小说主人公想要逃离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些以深圳为背景的小说虽然并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明确地域的深圳,但它们却无疑帮助我们理解了“精神上”的深圳——这个精神上的深圳和当下中国的许多城市有着如此强大的相似性,它足以成为任何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每天吸纳着无数移民却并没有很好地承接他们、让他们找到精神皈依的当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本期,我们围绕“城市文学”的主题,刊发了作家薛忆沩的专访以及《出租车司机》的评论文章,记者还就此采访了上海作家陈丹燕,北京“中生代”作家苗炜以及文学研究者丛治辰。当他们谈论“城市文学”时,他们谈到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维度上的城市以及精神向度上的城市。作家和评论者们共同意识到,文学的最终出路是返回单个人的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的复杂风景,为环境和时代所局限,也在寻求突破环境局限的努力中,呈现出动人的千姿百态。
【对话薛忆沩】
关于《出租车司机》 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
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
《新京报》:你在一篇文章里称“深圳人”系列小说是你“用十六年时间孕育而成的十二胞胎”。在完成这次奇特的分娩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薛忆沩:十六年前,当《出租车司机》(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作品)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登出来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位权威小说选刊编辑的电话。他称赞很少见到作品能够将“城市”写得那么有“诗意”。他说他想选用这篇小说。他用的“城市”和“诗意”这两个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三个星期之后,这位编辑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小说没有选上,因为杂志的二审说“看不懂”。对一个羽翼未丰的写作者来说,这权威的“不懂”当然会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当然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城市”还是出在“诗意”,或者是出在“城市的诗意”?我没有想通,所以我没有退缩。三年之后,一个小小的电脑操作错误让《出租车司机》通过《天涯》杂志再次面世。奇迹接踵而至:它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当然也包括了那家选刊)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用。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这真是神奇的进化。后来,“深圳人”系列小说陆陆续续刊出,一路上叫好声不断。最后的一篇《神童》是在今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刊出的。我有时候觉得,“深圳人”系列小说这十六年的市场反映是一个社会学的案例,它从审美趣味这个特殊的角度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文学作品的命运是写作者与阅读者较量的结果。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出租车司机》做小说集的书名?
薛忆沩:《出租车司机》是“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第一篇作品,也是其中最出名的作品,它当然最适合做小说集的书名。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出租车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宫里穿梭,它不断接近街景,又不断抛弃街景,它与城市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出租车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总是在等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再下一个目的地。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掌握着方向盘,实际上他却无法主宰出租车的方向。在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中,忧伤的主人公是通过逃离城市和职业来逃离“出租车”设定的这些悖论的。
关于深圳 在地标和历史贫乏的城市,只有关注普通人的内心
“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
《新京报》:我知道,在全部作品中,除了《出租车司机》一篇属于“在场写作”之外,其他作品都是在远离深圳,甚至远离中国的地方完成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执着地将小说的空间圈定在深圳呢?
薛忆沩:首先,所有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在场经验。如果我没有在八十年代末定居深圳,如果我没有十三年的深圳经验,“深圳人”系列小说不会成为我的创作业绩中一个板块。要知道,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们不是媒体上歌颂的改革者和弄潮儿,他们是我在深圳遇见的普通人。他们的叹息和迷惘惊动了我的感觉,刻画了我的记忆。是的,我在2012年初离开了那座城市,随后的十年在那里的停留累计不到两个月,但是,我的在场经验并没有中断:我与深圳还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深圳的报纸上还不时会出现我的近照和动向,我还曾经为那里的报纸写过一年的专栏。而远离让我用记忆去打磨从前的在场经验。那些原型通过这种打磨获得了美学的形式。那些摇摆在我记忆中的深圳渐渐凝固成了文学中的“深圳人”。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没有呈现一般城市写作容易堆砌的城市地标或者城市的历史,它们关注普通人物的内心,用你的话是关注“个人情绪的震颤”,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就像荣誉是对生活的简化一样。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关注人物的内心是我全部作品的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呈现“深圳人”似乎更是得天独厚。“个人情绪的震颤”是所谓新现象学的说法。当生活面临着转机或者危机的时候,人的内心会有各种奇特的反应。这些反应是观看生活、认识生活的最佳角度。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这可以说是“乘人之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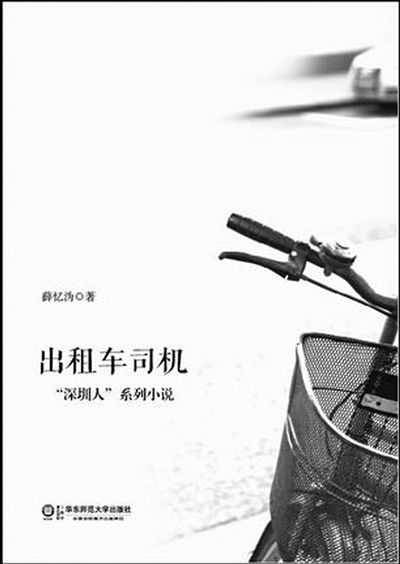 《出租车司机》 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年6月
《出租车司机》 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3年6月关于“城市文学”
中国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
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城市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
薛忆沩:我不喜欢这个概念,尽管现在经常听到人说中国文学正在转向,转向“城市文学”,甚至还经常听到人说我的作品是这种转向的代表之一。我不喜欢这个概念。我不喜欢给文学加上地域、职业或者性别的定语。所有那些定语都是狭隘和霸道的,它们轻则是学术的花招,重则是政治和集团的偏见。鲁迅的文学属于哪一种文学?托尼·莫里森的文学又属于哪一种文学?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城市文学”就像“乡土文学”一样,一旦成为时髦,成为主流,成为文艺政策扶持的对象,就很容易丧失它的同情心和辨别力。文学是孤独的事业。文学风格是写作者的财富和气质。重要的是要坚持个人的风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我看来,文学永远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去认识人,寻找人,发现人。而指引写作者的罗盘必须具备三种“原件”:考究的美学,批判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应该将那些多余的概念统统扔掉。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跟不上中国城市的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薛忆沩:中国的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有不少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了,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与农业人口持平了。因此,大家也就开始关心起中国文学的“城市化”问题。其实中国文学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只是这种“开始”在“乡土文学”受官方保护和学术偏爱的年代不容易被读者看到。以我自己的《遗弃》为例,那应该就是一部有强烈城市意识的作品。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热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带来的问题:空气的问题、饮水的问题、食品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4年前出版的《遗弃》里都已经暴露出来了。……我相信,《遗弃》并不是个案。我相信,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有更多的写作者就写下了思考和反省“城市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只是它们不够幸运,没有能像《遗弃》那样在“城市化”的狂潮中留下痕迹。《遗弃》本身也是被冷落了许多年之后才被读者看到的。我想,问题还是要从体制上去看。如果我们的文学体制诚恳地保护创作的自由,文学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辨别力。文学就不仅会跟上时代的发展,甚至还能引导时代的发展。
城市的悖论
我的作品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
“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将你对城市的感觉更彻底地呈现了出来。你怎样理解城市的特性?
薛忆沩:城市本来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安全和乐趣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现在却变得很不方便、极不安全、也了无乐趣了。它成了生活的污染源,精神的压力源。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悖论,它强化了历史的荒谬感和人的异化感。“深圳人”系列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城市的悖论不可能解决,只可能逃避。
《新京报》:本雅明有提及过,就是文学对于城市的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反城市化进程的,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薛忆沩: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深圳人”系列小说就是我的认同。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在想要逃离自己的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离自己的城市。这个观点肯定了文学的批判功能。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视野内,让你印象深刻的关于城市的书写作品有哪些?
薛忆沩:首先要提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在我看来,那是关于所有城市的“必读书”。它激起了我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野心。当然还有他的《尤利西斯》,我从那里知道了城市与个人关系的许多奥秘,比如广场和卧室是城市生活的两个最极端的空间。高端的广场代表的是历史的抉择,低端的卧室代表的是个人的困惑。《尤利西斯》最后死守住的是低端的卧室。“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样遵循类似的立场。当然还有许多的随笔作品,如本雅明的那些作品。当然还有布罗茨基。他的《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对彼得堡(列宁格勒)地标和历史批判可以“拿来”,值得“拿来”。“更名”是饱经浩劫的中国读者熟悉的革命手段,现在又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商业行为。它对一座城市心理的伤害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反映出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谁是真正的“深圳人”?
【评论“深圳人”】
谁是真正的“深圳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出租车司机》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提出了新命题。城与人的关系是现代都市文学的永恒主题,都市发展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尽管现实中的城市与文学想象中的城市不可能重合,读者却常常将两者互为参照,重构自己心目中的“那座城”。但是,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去阅读薛忆沩历经十六年之久创作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一定会在“深圳”的迷宫中迷路。
都市繁华背后的恐惧
关于城市的书写是一种精神的返乡。所以,指向过去成为都市小说的重要向度。读者往往在作品中发现许多“返乡”的路径,如熟悉的巷道和著名的老店。在文学作品中,“北京人”代表着远逝的故都遗韵,“上海人”代表着百年的世纪风华,“香港人”代表着本土的殖民风情……而薛忆沩笔下的“深圳人”却不仅指向未来,还试图囊括“所有”:“几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小说集的护封上留下了薛忆沩自己对“深圳人”的解读。
像许多其他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一样,深圳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在迅速都市化的同时进入到后大都市的阶段。丧失时间向度的深圳只能在当下和心理的空间中建构。
我们在小说集看不到深圳的“地标”,也几乎看不到“社群”。薛忆沩笔下的“深圳人”甚至全都没有名字,仅使用代词(如他、她、我、父亲、母亲、姐姐、妹妹等等)来指代。如果说“地标”提供了物理空间的位置感,那么“名字”则是社会性存在必需的认知符号。薛忆沩刻意抹去这些回归的“路径”,残酷地将他笔下的“深圳人”放逐到一个个完全陌生的空间,使他们都丧失安全感与归属感,让他们都面临着迷路的威胁。《文盲》中的“文盲”是最突出的代表。小说的叙述者最后“终于明白了她害怕的不仅是去‘医院’,而且还包括‘去’医院。她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街。她说她害怕迷路。”在全国白领最集中的城市里,薛忆沩让一个文盲说出了这座城市(以及所有城市)繁华后面的恐惧。这恐惧不是来自物质的匮乏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等,它是城市本身的痼疾。薛忆沩在“文盲”的身上设置了一个深刻的悖论,让她从城市的内外两个向度呈现现代城市的恐惧和堕落。“烦死了”是文盲的口头禅,更是现代都市人的集体体验和日常的精神状态。
薛忆沩的“深圳人”:孤立、禁闭和逃离
没有地标,没有边界的深圳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充斥着不稳定的伦理关系:《母亲》中的母亲为了一个性幻想而不去送父亲去边境那一边上班;《父亲》中的父亲在婚礼后的第五天,就遭遇婚姻带给他的巨大羞耻,开始对婚姻充满恐惧;《女秘书》将与老板在一起的私生活简单地视为她工作的一部分;《两姐妹》中的最“可靠”的男人变成最可恨的男人,他曾经“百依百顺”的女人变成了“那个女人”,她的沉沦没有激起他的任何同情。
城市这座现代迷宫,不仅因地理空间上的复杂引发对迷路的恐惧,同时也激发无限的想象与窥视的欲望。薛忆沩笔下的“深圳人”基本没有生活在其他都市小说写作中经常出现的公共空间。小说集中的故事都发生在隐秘的公寓、宿舍,或是半封闭的空间,如楼道、小区、甚至出租车里。人物与人物之间充满对对方的窥视、互窥、试探、揣测,猜谜与揭秘成了都市人际关系的日常模式。薛忆沩回避“深圳特色”的地标和公共空间,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个更私人的空间,同时也褪尽了“深圳人”的公众形象,将他们还原成一个最原始最质朴的身份:父亲、母亲、儿子、姐妹,准妻子、准丈夫……这样的逼近不仅有利于展示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也有利于对生存状况提出最残酷的拷问。在《同居者》中,最亲密的接触也无法撬开心灵的黑洞。作品避开通常的婚姻伦理,残酷地揭示人类生活中最近的接触与最远的距离之间的荒谬关系。这种荒谬关系也是《剧作家》的靶子。这篇作品将叙事的迷宫与窥视欲望相结合,追求最大的戏剧性效果,是“深圳人”中显得最“雕琢”的作品。
《物理老师》、《同居者》、《神童》三篇都属于成长小说,都涉及了青春型的自我如何走向成人的自我认知。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的主题在这里继续深化。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新兴都会的人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偶然性、短暂性,随时都面临解体的可能。每个人被城市“禁闭”,每个人也都自我“禁闭”。每个城市人都孤立无援,无所归依。“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避难所,甚至反而是矛盾斗争最激烈的风暴中心,荒诞感成了“深圳人”的宿命,也就成了“所有人”的宿命。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当然是基于他十多年的深圳生活经验的。而他对深圳“去历史化”的表现,无形中解构了这座城市的凝聚力,让“深圳人”都具有“逃离”的精神取向,都面临着重新选择,面临着再一次的无家可归。薛忆沩对城市未来的理解理性而残酷:“几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他想将别处变成我们所有人的此处。
有人说,“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而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实际上又“已变为一座城市。”从城市书写打开一条通往世界的路,借城市小人物的日常精神状态表现世界性的普遍忧虑,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借实际存在却又难以产生地方感的深圳,隐喻了“看不见”的城市的普遍命运。
□陈庆妃(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众议 城市文学 City iterature
城市中的人都是有限沟通
在很早完成城市化的其他国家,城市文学不会是一个鲜明的印记,而中国之所以分得这么明显,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乡村文学在那里对抗。有人为黄河边的中国呕心沥血,但看不到有人为城市做同样艰苦而重要的工作,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太平洋边上的上海,远远不及黄河边的中国重要。
城市文学写什么?
中国的城市文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描写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文学,还有一种是描写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文学。后一种形态的城市写作,以为在写城市,但其实是写一种物质的欲望。像当年那本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写上海的书,对于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人看来,这本书叙述的更像一个小市镇的孩子到大城市看到并追逐物质的经历。当然,这个过程,抽离好恶来看,也非常有趣。它写出了中国当下的一种现实,农村萎缩,农民进城成为新的城市人,田园价值观崩溃,失去根的人来到城市,首先接触到城市的物质,然后要面临一些文明的冲突。在乡村,没有市民的公共空间,他不需要遵守市民公共道德,但是到了城市,就不同了。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城市写作也很有趣,是一种历史的进程。
茅盾写《子夜》,尽管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在我看来,它也属于成熟的城市文学的体系,因为它在写城市由什么的人构成,它的金融系统怎么运作,等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单就上海而言,城市化停顿了很多年,这个停顿的过程中,城市是要向农村看齐的,都市的气氛被当做是反动的,农村的价值体系是革命的,直到后来,才有所平复。所以九十年代出现的城市题材作品,会触及怀旧,因为这个城市的形态曾经衰退,如今再出发,自然会以过去为参照物。其实,上海城市文学中的怀旧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就已经开始。我以为对城市的追忆,是承接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描写和表达的最自然的抒发。
另外,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天香》,金宇澄的《繁花》也都是有意思的城市文学的文本。有个年轻作家,路内写的《云中人》在我看来,它反映出的精神也是非常城市化的,在城市中,年轻人群体其实是被都市文明挤压得很厉害的一个群体,他们特有的颓废和彷徨感是一种典型的都市青年的状态之一,很像三十年代,巴金、丁玲、茅盾、施蛰存、刘呐鸥等人笔下的青年主人公,被挤压,非常愤怒。其实我们的城市文学还是有承接,有传统,有发展的。只是不够强大。
相比,那些着笔于物欲和商业层面的写作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东西,他们即使每个字都在写我是上海,也称不上是成熟意义上的城市书写。成熟意义上的城市写作,是一种立足于工业世界观的写作,它不是田园的,而是工业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工业化,我写《成为和平饭店》的时候,慢慢发现故事里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是工业的,经济的人物关系,他们都不能非常了解对方,个体是封闭,独立的,人和人之间,是在一种有限的,虚弱的沟通下,奋力寻找一种联系,几乎所有的城市文学,他们在描写人际关系时,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不完整沟通。田园文明下对于自然的描写,也被替换成对于人造物以及对于被人造物所包围的人的描写,可以说工业性元素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城市文学缺什么?
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会有漫长的路。它一定要突破田园意识形态障碍,另外,对于城市文学,中国的作家也显然是准备不足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写作,受到很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而在中国,因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代表本土的现实,而产生于本土的城市调查,城市分析,城市哲学很少,更多是批判和田园哲学分析下的种种误解,总之,它是不被鼓励的。我们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农业国家,农业文明过于灿烂,这难免会影响到城市文明的发育,当然,任何一种文明不可能长生不老,面面俱到,它是会变化的。
当年曹锦清先生写《黄河边的中国》,带回成箱白酒去田野调查,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常请他去谈调查的情况,也给予许多切实的支持。他与我先生有许多讨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就发生在我家客厅里。我得以旁听。后来,我先生将这本书稿在他工作的出版社出版印行。他们确定书名时,正是晚饭后,我端茶给他们。他们问我,一个书名,两个词不能缺少,黄河,中国,书名如何才能起得好看?我随口说,那就是黄河边的中国,或者中国里的黄河。他们就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关于城市的文学,在另一条路上
我有一阵住通州,每天开车走高速上班,在分岔口,会看见两个指示牌,一个指向北京,一个指向山海关,我开车,当然是朝北京方向走,但我觉得小说应该背道而驰,往山海关那个方向。现实是一条路,心里想着的另一条路是虚构。
“城市文学”可能是评论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对写作者来说,写作中会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写作,生活在乡村就会写乡村,生活在城市就会写城市,是很自然的。就我个人趣味来说,我不太喜欢现实主义小说,无论是写乡村的,譬如“陕军东征”那一批,譬如白鹿原,也不太喜欢描绘城市的小说。当然,也有喜欢的,譬如《莲花》,我就觉得挺好看。
生活在北京,也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完成对这个城市的一些认知。譬如老舍和王朔的作品,包括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种明褒暗贬,装傻充愣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非常市井气,是你对这个城市的一种认同。很多人的作品里,这种北京腔调非常强烈,但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还是避免北京腔调,会提醒自己别那么油滑,别那么毫无节制地聊。上海的一些作品中,我看过小白的《租界》和金宇澄的《繁花》,觉得有趣,特别是《繁花》,尽管我不懂上海话,用普通话读也挺有意思。我们这代人中很大一部分,不像老一辈和中国的土地有那样深的情感,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看萨特,弗洛伊德,会看外国小说,所以和土地没有那么深的连接,在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生活里,他可能和尼采更有亲近感。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更高的精神生活的产物,更多要诉诸内心。
如果给城市文学下个定义
在中国,城市文学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由于乡土文学的传统太过于强大。针对乡土文学,才有城市文学,而实际上,如此抽象地讨论关于“城市”的文学是很可疑的。一个“城市文学”的概念,无论如何精辟,怎么可能既包容上海的十里洋场气派,又指涉北京的千年帝都韵致呢?
大家谈到城市文学,总是要以西方的文学传统为参照,会谈到波德莱尔,谈到巴尔扎克,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城市的传统与西方未必相同,而城市文学自然也不可一概论之。何况同一座城市,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变化。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作为概念的城市文学,而是作为一个个文学现象的城市文学,是城市与文学具体而微的互动。
以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段历史时期来看,城市文学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为指导,书写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其次,是在新时期之后,一些具有独特城市文化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其文学表达当中逐渐寻找和确认城市自身的历史渊源和主体身份;后来,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城市文学一方面大量书写欲望与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对于城市底层人群的书写,对于城市新居民的书写,都逐渐出现并成熟起来。
其实无需去向世界文学搜求,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城市文学写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自己所在城市的独特精神面貌——尽管是以个人的理解,却成为读者们想象该城市的最佳入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铸造了该城市的文化。比如写北京的王朔、陈建功、刘心武、汪曾祺、叶广芩;写上海的王安忆;写武汉的池莉。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出很长,我不过是随手列举。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