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叶曙明:我所做的都是与历史聊天而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4日10:07 来源:南方日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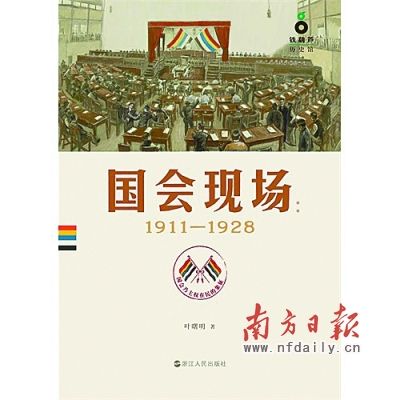 《国会现场》 叶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价:42.80元
《国会现场》 叶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定价:42.80元 叶曙明
叶曙明◎人物名片:
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著作包括“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以及《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中国》、《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之城》、《广州旧事》等二十多部。
◎核心提示
30多年里,叶曙明有了越来越多的侧面像:从曾经疯狂迷恋写小说的那位先锋小说作家,到辗转多家知名出版社的出版人;从热衷于清末民初历史的近代史研究者,到因一本《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在国内掀起广东人现象讨论、从而被誉为广东文化代言人的写书者。
日子久了,来自出版商的邀约也就纷至沓来。
已经出版的非小说类历史书里,叶曙明自行命题的只有两本,一本是24年前的《草莽中国》,一本是最近出版的《国会现场》。其他均是应邀而作,也就是“命题作文”。
很多人认为,“命题作文”是御用文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但在叶曙明看来,是否“命题”实在无关紧要,“这世界上没有不值得写、不可以写的题目,关键看怎么写。”
到了现在,叶曙明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历史说书人”。
他觉得自己所写的,都是与历史人物对话的结果。在与历史的聊天中,他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无论是陈炯明、梁启超、孙中山,抑或是章太炎、陈独秀。“我也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陈竞公’了,只不过在他们的朋友里没有我叶曙明而已。”
关于青春
在工厂的四年里
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南方日报:1980年您到花城出版社工作,能谈谈您此前的情况吗?
叶曙明: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但后来听说国家不承认文革时期的毕业文凭,要重新考试,我没有参加,所以我的学历应该是幼儿园毕业。我1974年去了从化民乐茶场种茶叶。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便整天躲在被窝读《列宁选集》,在世界地图上标记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的驻地。1976年我离开茶场,去工厂当了一名车工。在工厂的四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职业革命家的梦想荡然无存。工人阶级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出工不出力,做车间金鱼,迟到早退,装病骗假条。我一个月几乎旷工20天,有时发工资时只有几块钱。旷工不敢呆在家里,也没地方去,就整天待在中山图书馆南馆看书,看《东华录》、民国报纸和各种历史书,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那四年做的笔记估计有几百万字,后来全扔掉了。我对清末民初历史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0年底,因为我写了一篇《卖假药的老头》,被花城出版社总编李士非先生看中,就调到了花城,我总算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就是当编辑。这篇小说写一个人从年轻时开始收集茶叶渣,一直到老,却忘了自己当初收集茶叶渣是有什么用了,最后只好把一生的收集当垃圾全倒掉。这也许可以作为我自己人生的一个寓言吧。
南方日报:您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是怎样的?1988年您发表了第一篇长篇小说《军阀》,这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叶曙明:四年工厂生活对我影响非常深。1980年我第一次接触卡夫卡小说时,便完全被他迷住了,我觉得我就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所以那时我非常迷“现代派小说”,像卡夫卡、杜拉斯、加缪这些人的小说,每个标点符号都能引起我的共鸣。当时有人说,意识流小说是因为一句话不能完整地说,所以要打碎来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这句话只能这样说,用任何其他形式都不是这句话了。1980年代以后,我已基本不看国内作家所写的“现实主义”作品了,但我并不排斥它们,《军阀》就是我的一次现实主义尝试或者说是模仿,初稿甚至是章回体的。我当时颇为自得,觉得自己虽然讨厌现实主义小说,但还是能写得出来的,但现在回过头看,基本上是失败的。
南方日报:作为那个文学潮流迭起时代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文化圈那些人和那种氛围吗?很多人觉得,80年代被过分“符号化”了。
叶曙明: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当然是与50、60、70年代比较而言的。把前三十年的蕴结一次性喷发出来,随后又在短短十年里挥霍殆尽,这种情景自然很华丽、很壮观。我到出版社时,很幸运还能与最后一代的文人编辑共事。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着四五十年代老文化人的“范儿”,学识丰富,能诗善文,有性格,有风骨,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处充斥着被成功学训练出来的人。现在做出版,开口闭口都是能赢多少亏多少,有没有企业赞助,能不能申请政府资助,能不能评国家级大奖。与80年代相比,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所以我不知道80年代有没有被符号化,不关心有没有被符号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符号化,我只知道,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十分怀念那个有激情有梦想的年代,尤其是编辑上班不用在摄像头下打卡。
南方日报:后来您开始了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这缘于怎样的契机?
叶曙明:1980年代我写了不少小说,主角大多是精神病人,越写越觉得语言苍白无力,到最后有一种崩溃感,文字已经没法表达出我内心的想法了,写出来的每句话都不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再写下去就要疯了。那时我经常每写完一篇小说就发一场高烧。1980年代结束时,我有一种从九万尺高空直坠深渊的感觉。我决定不再写小说了。于是我重拾起历史,与历史人物对话,这能让我获得一点平静。
我爱好历史,但从不在意它的学术性,我读正史不多,读论文更少,我宁愿读原始档案。直接读奏章、上谕、文告、书札之类,好过读什么通史、全史。因为读原始档案有一种与古人直接对话的感觉;读通史、“略论”、“试论”的话只是在看别人的聊天记录,试问除了想要揪辫子之外谁有兴趣读别人聊天记录?我在微博上把自己定位为“历史说书人”,因为我写的都是我与历史人物对话的结果。我没打算推翻什么,也没打算建构什么,一切都是与历史聊天而已。
关于写作
任何题目都可以写
关键是怎么写
南方日报: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国会现场》?以“国会”为写作对象诠释告别帝制后的中国历史有什么特别之处?
叶曙明:我把我的“现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和《中国1927:谁主沉浮》概括为:第一部是出发,第二部是转向,第三部是锁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在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就基本锁定了。在“三部曲”后我感觉意犹未尽,因为在现代中国始终有两条线并行:立宪与革命。革命这条线从同盟会那儿传下来,还有另一条线,就是立宪、民权、自治这条线,从清末新政那儿传下来。我想理清这条线在民国时代是怎样延续、嬗变的。我原来的构想是写一部“民国制宪史”,从1912年的约法写到1947年的宪法。但后来考虑出版会有困难,便只写了北洋时代的制宪。在我看来,民国的真义在于“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的最高体现在于国会。民国初年的纷争,都是围绕着国会的。
南方日报:我注意到您在新作中用了很细节的描写,文献“愈近愈繁”,您对史料的价值有着怎样的甄别态度?
叶曙明:历史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相,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找出相反的“证据”都是轻而易举的,区别只在于你采信谁的证据而已。我并不是一个考据家,我很少旁征博引地去考证一条史料的真伪。
我甄别史料的办法,基本就是靠海量的阅读,读官方档案、稗官野史、私人笔记,一直读到我对这个人像老朋友一样熟悉,对他的举止言行,已没有什么意外了,他会不会说这句话?会不会做这件事?他是怎么想的?动机是什么?我凭对他的了解就能判断。我承认这样取舍史料,会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历史本身就是带感情色彩的,不是显微镜下的毛毛虫。我的原则是我不捏造史料,不虚构情节,但我采信哪条史料,则是根据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作出的纯主观判断。如果有谁想改变我的看法,最好不要以史料的真伪来质疑我,因为你也无法证明你掌握的史料就是真的,你只能说:我还有别的史料,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呢。这样,我会非常乐意听,然后再作出我的主观判断。
南方日报:近几年您出版的著作数量与前些年相比更密集,这可否理解为您在大量前期准备基础上的厚积薄发?
叶曙明:在我已经出版的非小说类历史书里,只有两本是我自己定题目想写的,一本是后来改编为《大国的迷失》的《草莽中国》,一本是《国会现场》,其他都是应出版商的邀约而写的,也可以说是“命题作文”。这几年出版商约得多,所以就写得多。很多人不屑于命题作文,好像那是御用文人干的事情,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其实我觉得任何题目都可以写,这世界上没有不值得写、不可以写的题目,关键看怎么写。
以为写命题作文就一定要顺着命题者的意愿去写,那是作者的无能;如果自我设限,即使不是命题作文,估计也难写出什么好东西。比如2008年广州市文联约我写一本有关广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这是命题作文之中最主旋律的题目了,但我觉得一样可以写,于是写了《万花之城》,对广州的城市建设提出我的观察和忧思,说想说的话。是否“命题”,实在无关紧要。
关于研究
我不太清楚
“主流学术圈”在哪里
南方日报:从近代史到广东地方史,您关注的这两个领域有什么关联吗?
叶曙明:中国要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关键不在于戊戌变法,不在于朝廷的预备立宪,甚至不在于同盟会革命,而在于地方自治。自治是国家迈入现代化的一个门槛,一个突破点,清末民初谈立宪也好,谈改良抑或革命也罢,能否实行地方自治是这个国家健康与否的一个基本指标。广东有悠久与深厚的自治历史。广东的自治,既不像湖南以传统的士绅为主,也不像上海以洋买办为主,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一向是由商人主导的。我对广东地方史的兴趣,实际上是受着对地方自治史的兴趣驱使。
南方日报:在写关于广东的著作时如何避免伤害别人的地方感情?您又如何看待地域歧视这一现象?
叶曙明:我写广东地方史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地方自豪感,保持一点点的地方意识,从来不想去伤害别人的地方感情。我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值得自豪的地方,我希望都有人把这种感情发掘出来,好好培育。与其把宏大的国家观念高唱入云,倒不如先养成淳朴的乡土观念。打个比方,什么是中国菜?就是由粤菜、湘菜、鲁菜、川菜、京菜等等地方菜组成的,如果把这些地方菜都抽走,中国菜还剩下什么?什么也没有了。你在广东生活,不了解四川、安徽、贵州都情有可原,但你至少应该了解广东,应该对它有感情,一个对自己生活之地都毫无感情的人,说对国家有感情,那都是假话。
中国最可宝贵之处就是地方文化的多元性,饮食、语言、习俗五花八门。地域歧视是一种幼稚的心态,其智力大约在三岁左右。试想还有什么比“只准我自豪,不准你自豪”更幼稚的呢?曾经有出版商邀请我写老北京,我父亲是北京人,我对老北京也有很深的感情,很想去写,可惜我没法去北京生活一段时间,感受不到现在的北京,所以不敢去写老北京。我写《国会现场》时,对联省自治运动中的湖南,心怀敬意;我写《李鸿章传》时,对安徽也充满了神往之情。这些地方,有机会我都想去朝拜。
南方日报:研究历史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这么一句话:“某人某事在历史上已有定论”。在您看来,为什么大众觉得历史有定论?
叶曙明:历史是什么?就是一堆史料。谁都可以去翻一翻,读一读。对同一条史料,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没有谁的手里握有终极真理,正如没有谁可以规定酒一定是香的,更没人可以规定甜一定比辣好吃一样。打个比方,对康有为,有人把他捧得很高,有人贬得很低,我觉得都很正常。可怕的是只准捧或只准贬,或者只准捧多高,高一分不行,低一分也不行。他说辣好吃,谁说不好吃就是想抹黑川菜、打倒川菜,这个罪名也太大了吧?所以,一切声称历史定论不容质疑的,百分百是为了维护现实利益,与历史根本无关。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您似乎刻意在心理上保持一种与“主流学术圈”的距离来分析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您赞同吗?
叶曙明:我在写《草莽中国》的时候,就是试图从地域的角度去解读中国近代史的演变,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东南打不赢西北?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阎锡山这些人的矛盾,到底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还是东南与西北、西南的矛盾?中国的很多疑难杂症,用正统的学院理论说不清,最后只能归结为生理结构、内分泌、饮食习惯以及这个地区的降水量、气温等原因了。
我并没有刻意与“主流学术圈”保持距离,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主流学术圈在哪里,所以谈不上亲疏。我说过,我读学术研究文章不多,这不是对学术抱有什么成见,而是纯属个人兴趣而已。今人写的“主流学术作品”中,我唯一爱读的,也许只有年谱。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长欣 实习生 栾相科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