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正文
林贤治:存在使我愤懑 把自由精神引入文学批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24日09:45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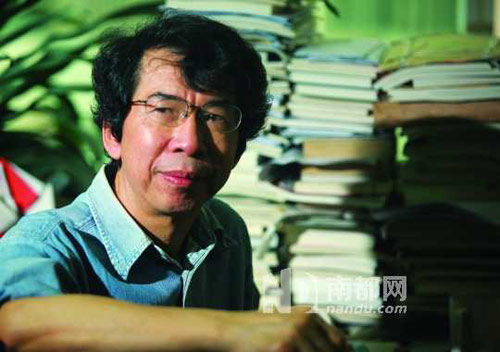 林贤治
林贤治 作家,学者,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花城出版社编审。编书之外,业余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著有《人间鲁迅》、《五四之魂》、《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国新诗五十年》等,曾获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从广东阳江的一个小乡村中一路走来,林贤治经过“农民”、“乡村医生”等身份的变化直至转变为出版社“编辑”。他没有经过学院的熏陶和培养,靠的是自己兴趣和阅读积累,林贤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写作者”。“他们在客厅里,我在野地里”,林贤治对记者这样说,他把自己的写作与学院派知识人的书写区别得很开。他现在仍不会上网,也极少参加学者间的公开活动,保持着他的“洁癖”。
青年时期被“恐吓”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写作充满“自由感”和“政治意识”,而随笔式的写作无疑是他认为能够表达的最好方式。底层出身的经历造就了他的“底层意识”。“写作或是编书,只是不同的途径而已,一个成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目标,还是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林贤治说。
阅读鲁迅让我更加清醒
南都:家庭环境对你走上学术有何影响?
林贤治:我父亲只是乡村的小知识分子。他虚岁十七岁就跑到外地当私塾教师,后来做乡村医生,这两重身份使他在乡下深孚众望。他非常重视和支持我读书,从我小时候认字开始,一直到后来他去世,我们家厅堂贴的对联都是他写的,其中一联就是“书田无税子孙耕”(好像孙犁家里也贴这对联)。我父亲对于我今天走向这道路是起了启蒙作用,他叮嘱我跟这个社会和谐相处,希望我收敛锋芒,不要得罪权势者。但是我没有做到,结果我因思想出轨影响了他。
南都:因为言论受到批判?
林贤治:我是1962年上的高中,阳江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刚进学校我就向学校语文科组上书,说这样的学校应该有校刊,后来我就创办了“新苗”文学墙报,刊头还是我设计的,编委会由语文科组按级别推荐组成。定期开会,让大家投稿,我是做审稿定稿的。当时写了一篇《梅花赋》,据说有老师批评,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后来我受批判是因为我的三个册子被同学告发,那时候“四清”工作队进驻我们学校,把我这三个册子拿走之后,他们认为我是“和平演变”的典型,思想反动,于是让一个姓廖的副队长找我谈话,写思想汇报,开始天天写,以后每周写一次,一直到毕业。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南都:每天生活在恐怖的氛围里面?
嘉宾:对。“好在你没有18岁,如果你够18岁,以你现在这种思想,就要到监狱里去了。”这是副队长亲口给我说的,非常恐怖。同学们疏远我,当时提倡“反修防修”、“跟坏人坏事做斗争”,跟“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做斗争。
南都:青年时期的兴趣是什么?
林贤治:当时最大的兴趣是阅读,至于我对出版的兴趣,在初中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我自己“编书”,喜欢的新诗抄写下来,分成四册装订,取名《中国新诗选》。还编过几册古诗词。当时有旧书摊,淘书、补书,重新装订、糊裱、做封面,都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我来自乡村,对于乡土,有一种宗教徒式的感恩。高中毕业之后我回家种地六年,然后做了十年的乡村医生,乡村医生面对的就是民间疾苦。乡村缺医少药,农民没钱买药,相信巫婆,自己采挖山草药治疗。这种情境最重要的是影响了我对一个社会的观感,对一个体制的认识。农村的生活引导我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培育了我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感。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林贤治:《南方周末》创始人关振东先生是我老乡,他最先推荐我的诗作,有一组发表在《广东文艺》上,后来《广东文艺》又约我写评论,我写了一万多字,他们准备用,调查我的政治面目,公社组织部门的人把我的过去写得一塌糊涂,导致文章不敢发表,这是后来关振东先生告诉我的。我还写过一首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期间,我有一个从有所追求到完全绝望的心路历程,我开始阅读鲁迅,鲁迅促使我更加清醒。这期间,我写了大概十一二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包括《鲁迅论〈水浒〉》、《鲁迅论秦始皇》等。这些都是地下写作,一个木工朋友帮我把抽屉面改了,放了一个夹板把稿纸放进去隐藏起来。
南都:这些文章算是你研究鲁迅的开始,文章后来发表么?
林贤治:没有,这些意在“反左”的文章多少还带有“左”的色彩。我最早写的是《鲁迅论秦始皇》。“文革”后,我把文章改好,跟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商量投稿,他批评我,这种文章是你有资格写的吗?应该是上面写的。后来见到陈铁健批秦始皇的文章,也就再没发表的兴趣了。然后是《鲁迅论〈水浒〉》,我把它寄给关振东先生,他转交给著名的杂文家牧惠(林文山),他当时在《学术研究》当主编,觉得文章不错,提出合作,以改稿的名义请我来广州。我借了一块表,第一次来到广州,跟牧惠先生讨论了两天,由我改动之后再给他定稿,后来发表在北京的《文学评论》丛刊上。
鲁迅传记的书写,就是与鲁迅对话的过程
南都:正式调来广州工作是什么时候?
林贤治:1981年,环境改变了,发表东西不再考虑到阶级出身和政治面目了。《花城》杂志创刊时缺人,岑桑、李士非先生看过我的长诗,就设法把我借调上来。一上来,正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苦恋》、《人啊人》。我为《人啊人》写过两篇辩护文章,一篇在《南方日报》发表,一篇在北京《作品与争鸣》发表。因为《人啊人》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或许是为了这两篇文章的缘故。据说经过出版局党组讨论把我留下来的,因为我是乡下人,没有城市户口,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民工,只是做文字编辑,不做苦力而已。直到1985年我才辗转把户口迁了过来。
南都:一开始在出版社做什么?
林贤治:我先是在《花城》杂志做诗歌编辑,后来把我调到诗歌编辑室编《青年诗坛》杂志。做了一年,《诗坛》就倒闭了,这多少和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有关。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受了批判,点名说我是“广东现代派的代表”,当时差点要遣返乡下了,报纸上有四五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居然说我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在这种苦闷之中我开始写鲁迅的传记。好在当时花城出版社的领导对我有保护,有一个从部队转业过来的罗兰如副社长在批判我之前知道了风声,私下告诉我要沉得住气,我非常感念他,但他已经不在了。李士非先生当时也挨批,他是《花城》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对我很好,却没办法保护我。
南都:除了鲁迅之外,在八十年代你还有哪些研究?
林贤治:基本没有。我原意写《人间鲁迅》之后再写“胡风传”,这个时候我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后来没写成。倒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舒芜的一篇长文带出了我的长文,就是《胡风集团案:20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1999年,当时《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约我写“五四”80周年的纪念文章,限期交稿,编辑天天打电话催我,结果我用了十多天写了8万字,当时的名字叫《五四之死》,却不准公开发表。同年年底,《书屋》杂志主编周实主动要我这篇稿,原文一字不动,只是把题目中的“死”字改为“魂”字,他有策略,11期他只发一万多字,剩下全部在12期发。当时,《书屋》杂志每年评奖一次,由读者投票决定,我的文章换了一套《全唐诗》,算是奖品。
南都: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初你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
林贤治:1983年有想法,准备从1984年开始。大概1984年、1985年开始写,1986年开始出第一部,一直到1989年,《人间鲁迅》的尾巴还有一点悲壮的感觉。
回过头看,在目前已经出版的鲁迅传里面,我自认为《人间鲁迅》对鲁迅表现得还算比较准确,从形到神。其次可以说理清了鲁迅跟左翼文坛的人际关系,包括“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个东西一直是笔糊涂账。第三部我认为是较坚实的一部,里面很多材料是过去根本没出现过,对邹韬奋、茅盾、郭沫若、夏衍都有严厉批评,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另外订正了部分史实,像流行的关于鲁迅加入同盟会,鲁迅给陕北红军致贺信等,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
南都:《人间鲁迅》算是你第一部代表性的作品?
林贤治:应该是,在那之前只是写诗,鲁迅研究在我准备和写作过程里改造和提升了我。研究他的思想来路有好几个问题,但问题是过去的知识不系统。在写的过程中必须研读有关方面的书,比如说中国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汇撞击的大背景。第二个,鲁迅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你怎么看?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条线要拉出来。第三,鲁迅的现实感很强,他跟共产党、国民党的接触、认知,政治跟文化的互动等。这些也为后面这20年我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打下一个基础。
南都:研究鲁迅的时候,跟你当时的精神状况应该是很相似的?
林贤治:鲁迅传的书写,就是与鲁迅对话的过程。与其说我去完整地表现我心目中的鲁迅,不如说更多地去警戒我自己,把自己从一种孤独、无助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展现鲁迅一生的工作,跟现实的东西联系起来。我还是强调写作的那种主观性,或者说主体性。我非常讨厌所谓“客观”的这个词。
南都:在写作方法上,《人间鲁迅》跟其他鲁迅传记有区别吗?
林贤治:我在《人间鲁迅》叙述、描写和议论中极力求保持一种风格,追求事实、思想和诗意的融合。为了加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我在书里也尝试使用内心分析的方法,还借鉴意识流小说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鲁迅传记所没有的。从前过多地强调外部的社会环境,而忽视内部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的孤独、苦闷、寂寞。外部环境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事件的叠加,而忽视周围知识社会的状况,精神氛围,人际关系,种种分裂与冲突。我特别看重分裂———统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学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联的分裂,兄弟和众多朋友的分裂,从不断的分裂中观察和表现鲁迅的特异性的生成。我把鲁迅当成一个伟大的矛盾统一体来处理,当成一个冲突的“场”来处理,也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面“镜子”来处理。
南都:除了《鲁迅全集》之外,还有哪些书对你研究帮助比较大?有参考作用的?
林贤治: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看西方的书。我在《三十年:阅读与写作》那篇文章里面,回顾了阅读的过程。鲁迅是个跨学科的人,尤其是西方的思想、文学和相关的知识,它的来龙去脉,你要了解,你就得找那些书来看。其实在写鲁迅的那几年,我觉得他也带动了我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阅读。而且这种阅读,主要是放在西方。这个对八十年代后,我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重建有一个巨大的帮助。近二十年来,看文学书较少,主要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
南都:在80年代初的环境下写鲁迅的,当时应该会有很多干扰。
林贤治:我写鲁迅是一种挑战。写之前看了11本鲁迅传,全看了,我才有信心去写。挑战就在于,鲁迅生前的很多事情,一直到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鲁迅传记出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对鲁迅早年的介绍很多,篇幅很大,到后期介绍却非常少,什么道理?他们回避问题。晚年非常难搞,一个就是鲁迅跟左翼文化人的关系,再一个就是鲁迅跟党的关系,第三,鲁迅个人思想的内部矛盾和转化问题。到底到晚年,他有什么新的“知”?这些以前没有人去探讨,见诸文字的很少,所以写起来很兴奋。
我自认为我的书基本上把从1928年跟郭沫若他们创造社里面的关系,一直到进入左联的关系,最后跟周扬、茅盾的关系,这个人际间的线索理得比较清楚,在此前,那是笔糊涂账。比如鲁迅跟茅盾,实际上他们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在“译文”问题上,他对茅盾是非常有看法的。后来我到鲁迅家乡绍兴,见了黄源(鲁迅晚年的青年朋友),他特意从书架上把一包鲁迅的信件取下来,抽出其中给萧军的给我看,里面提到“资本家及其走狗”。他第一次跟我说“资本家就是邹韬奋,走狗呢就是指茅盾、郑振铎”,这是黄源亲口跟我讲的,这印证并坚定了我的看法,鲁迅晚年的思想是复杂的。
南都:类似于黄源这种采访得来的资料,在写作鲁迅传中如何突破材料上的限制?
林贤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材料放着不用,不敢用,第二个是史识的问题,面对同样的史料,认识可以有霄壤之别。
南都:包括《五四之魂》、《散文五十年》等重要文章在90年代末期已经发表,这可以说是你创作最高峰的时期?
林贤治:90年代后期写了长文,应该说有点小影响,《散文五十年》属于当代文学史的范畴,但里面还是带有思想史的痕迹。因为对于作家、作品、现象的观察,归根结底是对体制的质询。我后来做《鲁迅的最后十年》也一样,我有“史”的情结,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给现实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经验。
在我个人的写作中,文学史是其中一个分支,鲁迅研究和知识分子的研究算一个分支,另外政治思想史方面研究也算是一个。这里讲的“研究”只是寻问、探索性质的阅读和思考,与学院式的研究大不相同。
南都:《散文五十年》当时的写作状态和缘起是十分偶然的,在短时间内写作如此大的文章,材料在你之前研究过程中已经完全具备了?
林贤治:这篇文章的写作非常偶然,邵燕祥先生要我和他合作,编一部新中国成立五十年的散文选本,要我作序,还说序文可以多到3万字,结果收不住,一气写了13万字。有的材料靠平日累积,有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接触的,像王蒙、余秋雨、贾平凹之类。这篇文章我很看重开头“根”和最后“其他”部分,我思考的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再就是批评标准问题。我一再把“自由精神”、“自由感”引入文学批评。
南都:鲁迅研究带动了你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而后是对中西方知识分子对比研究,到现在的政治思想研究,这个中间建构起来的脉络可否梳理一下?
林贤治:我很高兴看到有人注意到我写作中前后一贯的脉络,或是交汇点,那就是一个“存在”。哲学家说“此在”。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我关注我的存在,当然,我的存在和众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里,对生存境遇要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命运等也得有切合实际的认识。存在问题使我不安分、愤懑、悲哀,于是我写作,我不考虑我的写作算不算“学术”或“艺术”。在我的观念中,永远是存在大于学术,存在大于文学。
我很反感所谓的学术规范
南都: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林贤治:我对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所谓学术规范很反感。八十年代中期非常时兴盛方法论,我认为,价值论是第一位的,方法论是其次的,是派生的。你要了解某个观点,自由、平等、民主、正义,这些价值观念是最基本的,严密的规范妨碍到一个人的精神模式,思想、观念不自由,不可能有独立的创造。我们现在缺乏创造性,泯灭个性,我们要回到自然法,自然神那里,这跟现代意识没有冲突。
南都:2000年之后,你个人经历和思想上的过程是怎样的?
林贤治:2002年出版了我的随笔集《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后来是《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等等。这些年读书多了,在写作方面径直走自己的路子,更多是写一些短文,收集在《孤独的异邦人》、《旷代的忧伤》等集子里面,基本上是文化批评类。我还是从鲁迅那里取法,用“随笔”的形式,他叫“杂感”“杂文”,其实一样。我并没有想到要做成什么学术专著,为教授专家所认同,也不太乎读者怎么看。重要的是我在写。
我喜欢“随笔”这种文体,阿伦特说随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跟她在头脑中的思想操练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本雅明也高度推崇这种片段式的文体。可以断定,“随笔”与自由有关。任何热爱自由的人,都会追求一种反体系、反规范的写作。
南都:2003年写成的《中国新诗五十年》可以算是《中国散文五十年》的姊妹篇,为何要为文学史梳理脉络?
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的导论里面,我提出“怎么评价伟大的诗人?”,诗不是重要的,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唯有自由的诗人才能写自由的诗篇。我是把文学作为人文产品来看待,同时还要把它放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看待,这种大的眼光我觉得是必需的。认识一个时代,需要多方面取证,所谓“见证历史”,文学史是一个方面。
南都:《人间鲁迅》和《漂泊者萧红》研究算是文学史的个案研究,而《中国散文五十年》、《中国新诗五十年》则是全面的历史总结,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林贤治:我的写作全凭个人意志进行,响应内心对自由的召唤,所以也没有严格的规划。但大方向是存在的,古人说“文章大抵不平则鸣”,我有不平之气,所以充实、饱满,写作状态好。
我的两本文学史论确实与时下出版的文学史观点和写法都不一样。说到文学史,除了《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潮》,我欣赏的只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尤其是其中的迪克斯坦和考利。
南都:在随笔集《旷代的忧伤》和《孤独的异邦人》等书中,旁征博引,知识量丰富,是否和你做读书笔记有关?
林贤治:写短文无需做笔记,写长文或是专著时,我把几十本、几百本书摞到一起,集中读,有时候一天可以读十几本。
南都:写作上还有没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
林贤治:20年前想写王实味,他是因政治问题被禁锢的知识分子的原型,我会慢慢写。巴金我要写一本,不是写巴金的传记,而是以巴金为经,以他的朋友曹禺、冰心、萧乾、沈从文为纬,展示中国知识分子100年间的变化,看知识分子如何与政治、体制互动的。再就是一部关于“革命”的书,在世界范围内,革命是不是已经终结,可以“告别”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说到底,学术、文学都是第二位的,首先我们是中国人,然后我们是中国的文化人。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鲁迅全集》,我看的还是1981年的版本,全破了。
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自由、真实和真理的探索。
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谈不上最好的,《五四之魂》自觉略好一点。
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半夜两点多睡觉,早上九点多起来阅读,下午编书,晚上写作。
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哼哼歌,散散步,乱翻书。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