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文学机构访谈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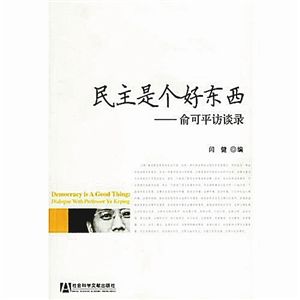
提 要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我们这几代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很重要,但政治文明同样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复兴。
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没有创造性,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那些政府改革,不属于政府创新的范畴。政府创新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也从根本上关系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因此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作为横扫数千年封建专制的启蒙利器,民主与科学化身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一百年前被中国先锋知识分子从西方请来,曾经那样地所向披靡,为铁屋中的民众呐喊而振聋发聩,给黑暗的旧世界撕开一线缝隙,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一百年后,一位北京学者再次急切地告诉国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本来只讲常识的文章又一次成为海外舆论的关注点,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学者,俞可平也因此越过一般理论工作者领域而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之一。
近日,许多深圳大学学子携带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等著作,在他作完“官本主义”学术讲座后,蜂拥而上请他签名指导。俞可平边走边与学生就“官本主义”未尽话题作一一回答。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告诉记者,这个话题是俞可平最近研究的一个题目,尽管这个问题有些尖锐,但他还是答应给学生来讲讲,很多观点都是以前没有提及过的。
这次俞可平是应邀参加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主办的“地方政府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他就政府创新等热点问题作了发言,而额外的学术讲座也给学生们带来另外一种新鲜的学术享受。在研讨会期间,俞可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A
民主与法治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一体,密不可分。我们要在已有政治存量的基础上,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这就必须鼓励政府创新
深圳特区报: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争议最大而又无法绕过的概念,大概就是“民主”。近代以后,民主已经从一种少数政体变成多数政体。在当代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对民主的争论依然成为热点话题,作为研究民主理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您最近几年对此有什么新的研究发现?
俞可平:对民主问题有争论是再正常不过了,从总体上说,对民主问题的严肃讨论有助于澄清在民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例如,有人说,我们要先法治然后再要民主,这种观点将民主与法治硬生生割裂开来。其实,民主与法治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一体,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法治是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离开法治当然没有民主。但民主还有其他要素,例如竞争性选举、公众参与、政治透明、对话协商、权力制约、权利保护等。又如,有人说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民主,这其实就像说我们要自由贸易而不要市场经济一样而不得要领。
当然也有极少数蛮不讲理的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而痛恨民主,喜欢专制。其实,从我第一篇讲民主的文章开始,我就反复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践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世界各国的民主既有共同的要素,又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实现民主,必须具备相应的现实条件。这些都是常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几代人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很重要,但政治文明同样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复兴。
我们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要在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即在已有政治存量的基础上,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鼓励政府创新。也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因此,我把它称为“增量民主”。
深圳特区报:许多人认为,您提出的“增量民主”,是一条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推进增量民主?
俞可平:所谓“增量民主”就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权益。说到合理路径,我们主张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和高层民主。党内民主意味着民主从权力核心向外延的扩展,基层民主意味着民主从下层向高层的演进。
从方式上来说,增量民主强调“点”和“面”的同时突破,强调“以点带面”的制度创新,试图通过政府创新所新增的政治利益,来确保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最优”,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
深圳特区报:在这个增量民主的推进和制度创新中,您一直强调政府创新的作用,有人说,政府创新首先是一种改革,那么政府在其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的理念对于21世纪的民主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类的政治理想正在逐渐从传统的“善政”转为现在的“善治”。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从长远看,“增量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善治”的理想。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治生活中的理想状态。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因此,政府要改变以往大包大揽的做法,要鼓励政府创新。而创新首先是一种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的改革,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进行的创造性改革。没有创造性,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那些所谓的“政府改革”,不属于政府创新的范畴。政府创新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也从根本上关系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政府创新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事关价值理性;但政府创新的直接目标是改善国家的治理,更是一种工具理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民众支持。因此,政府创新为各国政府所重视,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深圳特区报:一般而言,任何改革创新都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您说政府创新不是一般的改革,这是为什么,它与一般的改革相比有什么不同?
俞可平:这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关,政府是法律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所以政府创新自然具有极端重要性。
政府创新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创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公共服务,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它具有公共性。与其他改革不一样的是,政府创新的受惠者,主要不是政府公共部门自身,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政府代表社会掌握政治权力,因而,政府创新的结果通常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府创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直接涉及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十分敏感,风险性也比其他创新行为更大。
政府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民主法治,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因此,一个创新型的政府,不仅应当是民主的、法治的和文明的政府,而且应当是变革的、进取的和高效的政府。
C
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的需要,任何国家要顺应人类政治进步的历史潮流,就必然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对其政府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
深圳特区报:改革创新需要动力,尤其是对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更是如此,那么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俞可平:谁都知道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突破肯定需要更大的动力,没有动力,突破便不可能发生。改革创新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利益的驱动、经济的发展、危机的推动、环境的压力、民众的需求,还有国际的变局,这些都是动力。除此以外,还有要对我们的民族、国家、老百姓有信心。自信来自于使命感,我们民族的近代先贤以及我们党初创时期的优秀分子,都是舍生取义的,他们身上有一种使命感,一种要为国家民族奋斗、敢于承担责任的使命感。
改革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主动的精神。
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的需要,首先,经济体制的变化直接地要求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例如,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必然是“全能政府”和管制政府;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只能是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其次,政府创新是社会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从长远看,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民主化、法治化和分权化便是一种普遍的规律。任何国家要顺应人类政治进步的历史潮流,就必然要根据时代的政治要求对其政府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第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日益觉醒,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也日益提高,政府只有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才能逐步满足公民的政治愿望,增进公民的政治利益。最后,在现今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外部的国际环境也日益成为政府创新的强大动力源。
深圳特区报:由于现行机制等原因,一项新的改革举措出台,往往是先从中央的布置和动员开始,随后地方政府才开始实施,地方政府主动创新的动力不足,那么,如何加大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
俞可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的确存在明显的动力不足。有人认为,多数政府创新的直接推动力来源于上级部门和领导,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各个地方政府要转变思想,要有战略眼光。其实,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可帮助地方发展经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助于社会和谐。第二,目前官方的GDP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改革,需加入政府创新的内容,这样才能在体制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创新动力。要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社会,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创新型政府。第三,政府、公众、学界和媒体应给地方政府的创新以足够的包容心理,要善于鼓励各地的创新行为,而不要一味地挑毛病。任何创新都会有风险,也都会有代价,地方政府创新也不例外。其实,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不足,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广东,特别是深圳等地,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有许多先进的案例。
此外,政府创新必须注重实际,不能搞政绩工程,切忌搞“政治秀”。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那就不是简单的劳民伤财,而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政府的创新必须脚踏实地,少说多做,重在实际效果,重在落到实处,重在人民群众的满意。还要善于总结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创新的动力问题,用制度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
学人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1959年出生。
著名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
代表著作:已出版中英文专著编著30多种,其中包括《敬畏民意》、《民主与陀螺》、《民主是个好东西》、《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全球化:全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社群主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以及《政治学教程》等。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