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作家访谈 >> 正文
梁鸿:整个社会都在抛弃乡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5月07日10:08 来源:羊城晚报 梁庄旧屋
梁庄旧屋 梁鸿
梁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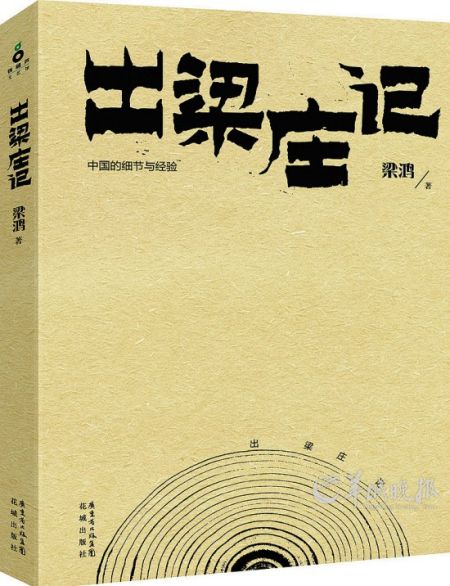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乔献萍
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多部学术专著。
其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出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
4月28日,梁鸿新书《出梁庄记》的广州首发式在学而优书店举行,这本新作或许可视为作者前一本书《中国在梁庄》的姐妹篇。
2008年寒、暑假,梁鸿从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穰县梁庄,前后住了5个月,写下一个个梁庄人留守梁庄的故事。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
2011年,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她花了两年时间,沿着梁庄人的足迹,走访了在郑州、信阳、西安、内蒙古、东莞等城市打工的“梁庄人”,并以梁庄四大家庭的子孙为轴心,描述进城农民工的命运和生活、精神状态。最后以《出梁庄记》为名出版。
梁鸿从小就喜爱文字,小学三年级开始写周记,别人写一篇,她自己要写两篇。喜欢写作,是因为她觉得,“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单面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它能把人性深处的奥秘和人心深处的思考揭示得非常深远。”
而《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展示的不仅仅是梁庄的世界,它也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用当代作家闫连科的话说,这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
如果社会都不爱乡村,凭什么要这些年轻人爱?
羊城晚报:《出梁庄记》里写了很多人,在采访他们时,您觉得他们对故乡是怎样的情感?
梁鸿:我在采访时几乎都问到了他们这个问题,答案各异。老年人,只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他必须爱那个地方。这不像我爱梁庄,我是自由的,在城市生活得很好,我可以回,也可以不回,是有选择的。他们的爱是真爱,但这种爱是单元的、逼窄的一种东西。老年一代回梁庄,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命只能在那里了,所以必须回去,那个地方有他的爱恨情仇,有他的家族生活,有他的尊严身份,有他的房屋。
年青一代对梁庄的情感有点复杂。他们可能从小寄宿在外,也没干过农活,对农村的印象是模糊的。但那也是他们的归宿,人心总要有个安稳的地方。比方说你一家人在一块,夫妻或男女朋友在一块,一起租个房子也挺好的,心是安稳的。但你在城市里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你就会想到那个遥远的家乡,想到可能有一天我要回去。不过年轻人对乡村其实是不爱的,我们整个社会都不爱乡村,凭什么要这些年轻人爱乡村?远离乡村是很正常的。
不能责备他们,因为我们整个社会,不论道德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在抛弃乡村。你为什么不回你的家呢?你为什么来城市抢我们的资源?这种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所有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统统都在朝城市倾斜,你不能要求一个个人来做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年轻人对梁庄的感情既是一个遥远的梦,又是一个切实的不得不做的梦。
羊城晚报:你笔下的那些人,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多少年,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永远都会说自己是梁庄人。
梁庄: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复杂的。农民说他是梁庄人,因为他只能是梁庄人;但是,现在我有北京户口,我说我是梁庄人,是很骄傲地说那是我的故乡,我的籍贯,这两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虽然表面的话语一样,但要看到它背后的价值、身份、归宿和在社会的定位,只能是梁庄。如果他在西安有个家,有个房子,他说我是梁庄人,那他是在幸福地说我的故乡是梁庄。
但像我在西安采访的那个人,他说打死也不在西安住,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农民,喜欢农村,而是那么多年在西安的经历告诉他,这个城市不要他,所以他也不要这个城市。他们不断被驱逐,卖个菜,随时有可能被踢倒,三轮车被没收,这个城市不断通过各个方面,政策、眼神、态度来告诉你,你就是个农民,你就是梁庄人。如果他在西安非常自由幸福地生活20年,他再说自己是梁庄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感。不是他简单地想念梁庄,爱梁庄,所以要回去,这里面是复杂的被塑造出来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详细地写他们生存过程的原因。
羊城晚报:在《出梁庄记》中你写这个外出打工的群体,他们渴望致富,其实也很渴望平等。但看完书后,发现大部分人还是很难在城市真正立足。您觉得农民工的未来在哪里?
梁鸿: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也有对平等自由的渴求,如果我们的历史一直忽视他们,就太不正常了。他们的这种迷茫,其实不是每时每刻的,他们也有正常的生活,该卖菜就卖菜,该拉车就拉车,该笑就笑,该吃就吃。但这种对尊严平等的要求一定存在,可能老农民说我自己这辈子就算了,但他会想自己的儿子孙子,将来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人的基本要求。
除了吃饱喝足之外,他们还需要像一个人那样存在,需要被尊重。比如我们常看到,工地很脏,建筑工人上了公车会自觉蹲在角落。这种风景谁看了也会多少有点难受。可如果工地上有两个浴室,谁不愿意洗干净换身衣服再回家?这就是尊重,可没人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只想着你来干活给你发工资就行了。
职业是不分高下的。有人说农民工没有上升空间,我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需要这样的职业,需要有工人,需要有拉车的。哪怕我一辈子没有生长空间,但我在这个职位上干得快乐,很有尊严,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源,下班后可以散步、聊天、谈恋爱,一家人相对自由自在地生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的,不必要非得学知识、考大学。可我们的社会恰恰连人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夫妻不能在一起,孩子和父母很难在一起,基本要求一个也没完成。难道我们可做的少吗?可做的太多了,只是都没做。不只是钱的问题,包含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国度里这么大的群体的问题。
我把最重要的五年献给了梁庄
羊城晚报:我感觉《出梁庄记》没有前一本《中国在梁庄》的抒情性那么强,您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吗?
梁鸿:《出梁庄记》处理的题材不太一样,我有意识地做了一点疏离。因为这个题材太大了,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它不像我回到梁庄,一草一木都是非常熟悉的,情不自禁地抒情。但书已经出版了,也不可能修改,所以第二本书就稍稍控制了一下,免得在某些层面失控。但是,“有情”对梁庄是必要的,我一直说这不是客观的社会学调查。梁庄对我来说,不是陌生而没有关系的村庄,它就是我的故乡。它是以双层空间出现的,我看到你就想起你的童年,看到他就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看到她想起她的孙子去世了,她的老头也不在了。这是叠加的空间,有时间和空间的痕迹,是有情的。
羊城晚报:写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之后,您感觉自己有变化吗?再回头做学术研究,会不会觉得特别枯燥艰涩?
梁鸿:我自己的变化非常大。从2008年到今年,五年时间我一直在做这个事,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五年,中年初期,我全都献给了梁庄。我不但幸运,而且幸福,找到了自己喜欢做、能够做、并尽可能可以做好的这样一件事。以后回到学术研究上,我对中国大地上的事情,会有一种更独特的深入和思考,这应该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写这两本书是非常好的积淀,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今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从中吸取很多。
其实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不是完全对立的,我毕竟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学科训练。这两者本身都是文字,而且文学研究本身是情感和理性相结合的。另外文学创作的深层也需要理性认知的支撑,这两者并不相悖,就看你能力有多大。
敬佩前面一定加上两个“非常”
羊城晚报:您怎样看待邱建生他们这些立足乡村搞建设的人?
梁鸿:邱建生是当代乡村的建设者。我非常非常敬佩他们,一定是两个“非常”。因为他们是实践者,进入到乡村内部,从文化上、政治上改变乡村。在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试图找另外一种可能,逆向地寻找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可能性,他们试图挽救乡村,通过文化来创造经济。
他们非常深入地在做这件事,但遇到很多难处,比如资金的问题,比如政府的不作为。当然自己的理念上也有一定偏差,不见得他们做得都对,也还在摸索的过程中。但他们这种逆向的探索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我们这个社会太单一了,十分需要这样的人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而不是让乡村也成为城市。
羊城晚报:人民大学的温铁军老师也在做乡村建设。
梁鸿:对,我是温铁军老师团队的志愿者,尽可能参与他们的实践活动。但这毕竟不是我最擅长的,因为他们做实践需要深入一个村庄管理,非常艰辛。我还是比较擅长文字工作,我得承认自己的限度,不能什么都做。
羊城晚报:下一步您会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某些问题吗?
梁鸿:我下一步会做关于乡土中国的理论研究。我本身也是搞学问的,会从理论层面关注乡土中国,其实也是重回梁庄,只是用不同的途径。从晚晴时期开始,人们就想到乡土自治,认为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和现代化相融合。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乡土中国就成了落后的、愚昧的、一定要像肿瘤一样割掉的一种存在。这种话语逻辑很有意思,我们的政治、文化思维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乡村是一定要抛弃的。我想从理论上来梳理这个话语生成的原因和背后的源流。
“非虚构”只是主观个人的真实
羊城晚报:这几年以非虚构方式写的作品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梁鸿:何伟他们比较早,因为国外一直有人类学考察这样的传统。中国这几年出现非虚构,一方面“非虚构”只是个概念,另一方面“非虚构”中有某种真实的东西。这种真实的东西正好和我们社会的某种情感和思考暗合,所以才引起一些反响。但是,我认为健康的文学生态是多种多样的,“虚构”文学也有其好处和用处。
“非虚构”不能说是真实,它只是主观的真实,个人的真实,不是纯真实。纯真实是不存在的,只要经过你的眼睛,经过你的文字,文字本身就是有次序的,先写你后写他,为什么?这个问题永远也说不清。真实只是主观的真实,所以我说梁庄是个人史,不是社会学意义的调查。
羊城晚报:您看过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吗?
梁鸿:看过,但没看完,很多记者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写打工群体的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它需要一种互文性。不要说谁好谁不好,它们是从不同视角进入的。张彤禾是华裔,她用的是外在的眼光,用不同的知识体系揭示打工女孩的内在逻辑。而我,是内在的眼光,因为我长期在这条河流里一块沉浮,可能看到的是另一种细节。这些都是需要的,是互补的。
当然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打工女孩》里的人一样从流水线上升到文员白领,文员只有那么几个,而流水线工人成百上千。能上升的女孩,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当然非常棒。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些没机会的女孩男孩怎么办呢?难道就应该被挤压被剥削?这是不对的。我们恰恰需要关注这样更广大的存在。哪怕她没有上升空间,但她能比较有尊严地获得生活资源,这样才好。我们缺的不是向上的空间,而是这个平面的空间太被压抑。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