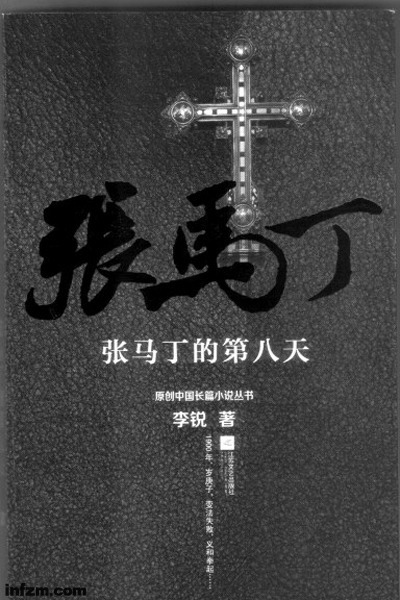中国作家网>> 综述 >> 年度综述 >> 正文
2012年中国长篇小说微观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4月07日15:57 来源:南方周末 张英 “文学的改变需要每个人往前跨上一步”
2012年中国长篇小说微观察
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文学》做编辑后,他停顿了很多年小说写作。2011年5月,他开始在上海弄堂网的论坛里写《繁花》,2012年小说在《收获》发表后,迅速成了中国文学圈的热门话题。 (金宇澄/图)
传统文学复兴?
“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那些很少读传统文学的读者发现,中国还有这么有想象力的小说;很多人看了《白鹿原》很惊讶,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样有深度的小说。中国文学需要重新评价,重新认识,重新发现。”评论家雷达感慨说。
从开卷全国大众畅销书榜可以看到,此前,名人书一直是大众畅销图书的市场主力,基本上被白岩松、蔡康永、孟非、杨澜等人占据。但到了2012年10月莫言获奖以后,莫言的8本小说全部上榜,成为市场上热销的图书,在媒体推波助澜下,11月份莫言的小说更是包揽了全国大众畅销书榜的前十名,一个人占据了虚构类榜单前30名中的25个席位。在两个月里,仅当当网莫言作品销量就突破2000万码洋,其中莫言的最新小说《蛙》销售了80余万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当当网的作品年销售量在1万册左右,得奖后,一天的销售量就超过了1万册。莫言本人以2950万元的版税成为“2012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冠军。
因为同名电影、电视剧的拉动,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原著小说也持续热销。而刘震云2012年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机印刷50万册。出版人金丽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刘震云写作认真,作品精打细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
除了莫言和刘震云外,路遥、贾平凹、余华、陈忠实、王朔、麦家等作家的长篇小说销量基本上都在四十万册左右,而格非、阎连科、毕飞宇这些作家的销量也在10万至20万册之间。
一直在主编《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的评论家白烨则感慨,“莫言的获奖让人感觉到传统文学现在热闹起来了,其实传统文学这些年一直在往前发展,只不过不被媒体关注,一般读者不真正了解文坛,他们对文坛的了解是媒体所描述的文坛。”
传统文学作品的销售正在升温。据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文学类图书在上半年增长速度是4%左右;而到了下半年11月,和2011年同期相比,文学市场同比增长24.67%,是图书市场里增幅最大品种。
评论家白烨对南方周末记者公布了一个数字:2012年,他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到,在书号中心出版登记的长篇小说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长篇小说,内地的原创作品应在4000部左右。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直面灵魂,二是思考生命,三是进入深度的文化反思。”而评论家孟繁华的看法则相反,“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坍塌了,不再有史诗性、整体性的长篇小说出现,作家们不再有在小说里建构整体世界的野心,像《白鹿原》、《尘埃落定》、《古船》那样的小说越来越少,写作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个人化,依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感受写作,文学这面镜子越来越碎片化。”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邱华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几年长篇小说确实迎来了繁荣期,发表长篇小说的刊物也在增加,《人民文学》、《作家》等原来不发长篇小说的文学杂志也开始扩版增加页码发表长篇小说,而原来发表长篇小说的《收获》、《钟山》等大型文学杂志则干脆定期出版增刊;像《十月》、《当代》、《江南》、《中国作家》等原创文学杂志干脆改成了半月刊,一年拿出12期内容专门发表长篇小说,连《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也专门创办了长篇小说选刊。
(南方周末资料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
上访与截访
有意思的是,2012年有两部小说涉及上访的主题。
为钻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规避生二胎面临的经济处罚,村妇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原本说好生下孩子就复婚,他们刚离婚,秦玉河却娶了新妻子,不理李雪莲了。李雪莲开始走上了告状和上访的不归路,最终成了一个不屈不挠的二十多年的上访专业户,多次到北京上访,甚至撞到了全国人代会场里,因她的“壮举”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市长都拖下马。
“起初是一件特别小的家务事,李雪莲跟她丈夫离婚的事,但没想到这个事很快演变成她跟法院的事,跟县政府的事,跟市政府的事,一直变成跟北京人民大会堂两会有关的事情。”刘震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小说,它主要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一个芝麻会变成葡萄,接着会变成苹果、甜瓜,最后变成了西瓜?一个妇女告状,一串贪官全部都倒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变成了一个国家大事,这个荒诞的过程是怎么演变的?”
评论家们感兴趣的是刘震云用了18万字,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绕来绕去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敏感词:上访。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个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没有简单化、概念化,戏剧性很强,通过极简主义的叙事表达庞大复杂的主题。李雪莲不是潘金莲,是‘孙二娘’,她通过偏执的举动,牵动了社会的神经,让内部的秘密得以掀开和暴露。”
出版人安波舜感叹,“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写‘文革’、童年、历史,很少有像刘震云对现实这么敏感,有勇气和胆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
《我不是潘金莲》因为“上访”题材,出版犹豫了两年之久。它也未能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而是发表在《花城》杂志上。出版以后却获得了来自评论界的好评。这是在刘震云意料之外的。“这给我的启示是:写作的尺码不一定老靠别人来定。每个作者往前跨一步,写作的尺码就能大一些。文学的改变,社会环境的改变,需要每个人往前跨上这么一步。”
刘震云笔下写了上访人,而贾平凹201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带灯》的主人公“带灯”却是负责维稳的“截访”者。
《带灯》反映了当下拆迁、上访等各种问题,这是这些年贾平凹唯一面对当下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大学生“带灯”到秦岭樱镇政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她接触了因为经济纠纷、房屋拆迁、农田占用补偿不公、治安问题的上访者。
《带灯》里所有的故事却都有现实依据。“这些年我一直在社会基层跑,从东部到中部,从西部到南部,我跑了很多地方,在基层看到很多社会现实问题,让我忧心忡忡,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我积攒了很多感想,在《带灯》中我想把它表达出来。”贾平凹说。
和贾平凹所有的小说一样,带灯在现实生活里确有其人。贾平凹经常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一位深山里的乡镇女干部经常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她看见、听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什么都写什么都讲。她还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核桃、蜂蜜,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等。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写的检查草稿。”
《古炉》写完后,贾平凹去了深山看望这个基层女干部,一起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随她去堵截上访者。“通过写《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知道了乡镇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我写的是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我思考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事。”贾平凹说,“我是共产党员,从小受的教育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对当下的许多问题,更应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写带灯这个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中国社会最现实的问题。”
评论家李星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
(南方周末资料图)
地域性的繁花
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上海文学》做编辑后,他放弃了小说写作。作为这份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现在小说里的相同经验太多了,语言、叙事,如果遮掉小说作者的名字,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人写的。”
2011年5月,金宇澄开始在上海弄堂网的论坛里写《繁花》,他以 “独上阁楼”为网名,写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几百字地发文章,没想到很受网友欢迎,不断跟帖“爷叔,写得好”。
“有一天写到陶陶和沪生在菜场相遇,陶陶说‘你进来’时,我忽然有了感觉,这不再是纪事和漫谈,已经是长篇小说,于是开始故事结构,逐渐变成每天一千字,甚至后来的五千字,一直写下去,11月份完成了初稿。”
《繁花》2012年在《收获》杂志长篇小说增刊秋季卷发表后,引发了像当年陈忠实的《白鹿原》似的效应。半年时间里,它成了中国文学圈的话题。
《繁花》以沪生、阿宝、梅瑞几个人的视角,记录1960年到2000年之间的上海三十多年历史,描写了一百多个人物,一万多个故事,用大幅改良后的沪语描画出上海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历史沧桑。
评论家阎晶明说,“《繁花》是2012年中国小说界的最后一抹亮光,照着小说里手绘的‘上海地图’查看小说人物的方位,会觉得这些人此时此地仍然穿行在这些弄堂与灯火中。真实的地名、路名、店名铺陈,夹带着特殊俚语词汇的对话,将其不可复制性和真切感推到极致。这是只有深谙上海生活纹理的人才能写出的小说,是熟悉不熟悉上海都会被其真实性折服的小说。不再是带着粗疏的故事直奔主题,而是绵密的故事、细致的描写、耐心的勾勒、不可替代的语言让人读到人间烟火,也读出历史变迁。大历史只是‘小人物’的附着物,也是这部小说的原创性体现。”
评论家汪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品躲开了将怀旧作为时尚的书写风格,反对将地方作为知识的方志化话语,而是努力让地方和城市回到生活,回到现场,在活泼泼的‘对话’和方言‘腔调’中,显出书写对象原初的生命质感。”
女作家叶广芩的“地域性”不是陕西却是“老北京”。其祖先是叶赫那拉氏,但叶广芩否认网上关于她是“慈禧太后的侄孙女,清朝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太后的亲侄女”的介绍,只以同一支中的纳兰性德为荣。
1968年,20岁的叶广芩被迫离开北京,告别双目失明、绝症缠身的母亲,赴陕西农村插队。今天的北京城变得越来越新,而叶广芩却用她的笔在建构还原她心目中的“老北京”。
《状元媒》讲述了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婚姻,其间穿插了金家及其亲友自清末至今众多颇有味道的故事。
(南方周末资料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
灵魂的安定
2008年是周大新的“最黑暗的日子”,8月3日,在忍受了长达3年病痛折磨之后,儿子周宁离开了这个世界。儿子周宁1979年11月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学习,本科毕业后进入郑州信息工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北京,在总后勤部某部通信自动化站工作,2008年8月,因脑癌去世,差3个月才满29岁。这一年,周大新56岁。
周宁的病情与精神压力有关。和大部分父母一样,周大新为儿子规划好了人生道路:中学读的是竞争压力巨大的名牌中学;为了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周大新不让儿子看电视、打篮球;本科毕业又催着他读研究生。
在给儿子买墓地时,他把自己和妻子的墓穴也一起买了,“将来,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葬在一起了”。他给儿子设计的墓碑是一本书的形状,意味着他的人生之书还未完全掀开过。儿子离开后,周大新在痛苦和悲伤中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发现,因为计划生育,有很多父母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变成了失独家庭。相当多的家庭,此时已经无法再生育孩子了。“在我儿子长眠的那片墓地里,就埋葬着不少去世的独生子女,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车祸,有的是自杀。在清明节祭祀的时候,我会碰到那些失独的父母,大家彼此点头致意,不敢深谈,都怕引得对方伤心流泪。”周大新说。
周大新花了3年时间,“为儿子,为自己,也为其他失去儿女的父母”写了对话体小说《安魂》。除了回忆儿子,小说还谈论了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反思养老制度,涉及了孤独、天国、命运,以及“人为什么要活着、人该怎样活着、人该如何做人、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的观察与思考。
2012年年底,周大新和妻子向老家河南省邓州市捐献了100万元人民币,以儿子的名字命名建立了一笔助学基金,用于资助邓州市每年升入大学的贫困学生。
另外一位河南作家李佩甫在2012年出版了《生命册》。这部38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一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吴志鹏”的故事,他从乡村到省城,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操盘手、上市公司负责人,最后迷失于物欲横流的生活。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追求的反面。
“作者试图从城与乡、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的对峙和互渗中揭示鼎革时代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可能性并逼近历史、人性的真实,因而这部触摸城乡时代变迁与人物异化,书写当下残破信念与生命真谛的作品,既是自省书,亦是心灵史。”评论家冉冉说。
和《安魂》不同,辽宁作家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借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形式,讲述的是作者跟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项目课题组,深入辽宁农村,记录因各种原因自杀者家人的故事。
“我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中国自杀百分之八十都发生在乡村。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孙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生死十日谈》呈现了农民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遭遇的物质、精神方面的困窘。这些农村的自杀者真正的内在原因是贫穷导致了绝望。“我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追问。”孙惠芬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