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小说 >> 今日作家 >> 正文
陈忠实: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06日15:13 来源:中国文化报 杨晓华 陈忠实先生近影
陈忠实先生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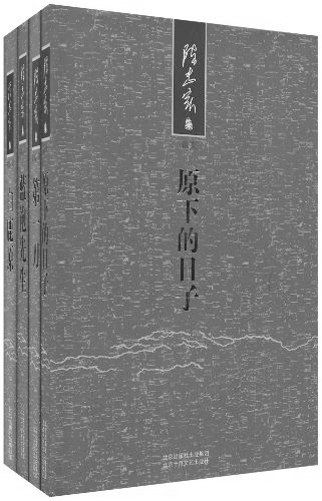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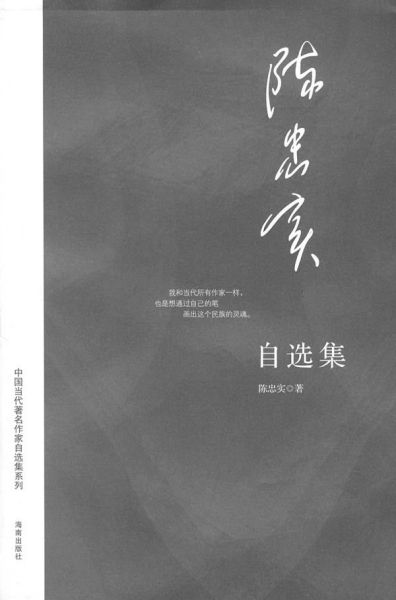
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康家小 院》,散文集《告别白鸽》,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 卷”,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自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2013年2月25日,陈忠实先生在陕西西安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杨晓华:《白鹿原》出版以来,持续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您掌握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包括外文版在内的发行数的准确统计?
陈忠实:《白鹿原》具体发行了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几种版本一直都在发行。电影《白鹿原》上映,又一下子发行了六七十万册。去年人民文学 举行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说,这个小说从1992年出版到2012年,一开始就热销,后来持续每年各种版本发行十多万册,这在当代文学 中是很少的。我自己也很惊讶。20年,两三代人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白鹿原》最早翻译成日语,然后是越南语,去年是法语。英语的翻译来谈得很多,但有一个问题卡住了。法文版签合同时,他们出版社的总编提出还要 代理其他语种,还有德语、西班牙语等,他们号称法国第二大出版社,和各国出版社都有往来,对其他语言的翻译出版有好处。我就直接签合同了。所以,现在各种 语言要翻译,我都不能谈了,得和法国出版社的代理商谈。
杨晓华:雷达先生在《废墟上的精魂》一文中,认为《白鹿原》正面观照了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养育的人格,从而探究民族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是新时 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飞跃。您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浓郁的文化意识的?是什么样的契机和动力促使您要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传统社会做一个史诗性的观察和 描述?
陈忠实:应该说,就是创作《蓝袍先生》引发的。在《蓝袍先生》之前,我主要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变革,写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的思想、家庭、人际关 系的演变。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到了现代生活潮流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撞击,但是文化的意识并不明确。到《蓝袍先生》,这个意识就较为明确 了,我就是要写一个人的精神裂变,写精神裂变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个中篇触及到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我才感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一个大的人物 活动的背景。后来就开始关注那一段历史,就是1949年以前,从封建社会解体到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关系问题。
杨晓华:如果说您之前的创作,重心都集中在单个人物的刻划上,到了《白鹿原》面对的是受到类似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人物群体,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陈忠实:我从来以为我对农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前后几十年。我不像柳青,他挂职县委副书记去深入生活,实际上 就是深入我这样的生活,我本身就是这种生活的人,我的这种体验是最直接的。但是写1949年以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自信。对1949年之前太不了 解了,尽管有些感性经验,但那是很幼小的生活记忆,所以我就渴望了解这块土地的昨天。
当时我还有一个逆反心理。我本来对寻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后来看到几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写荒山野岭、荒无人烟的地方,写小土匪,小酒店发生的怪事 情,我就感觉到,寻根寻到最末梢去了,这个不好,应该寻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城市或者古镇,因为一个城市或古镇,是一个地方工 业、商业包括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民族文化的根应在这里,而不在荒山野岭。
有了以上这几种因素,我就开始全面了解白鹿原。白鹿原只是一个具体的小原,实际上西安周围的几个县都有原。先开始查县志,西安周围三个县长安、 蓝田,还有已经消失的最古老的咸宁县的县志(辛亥革命后和长安县合并)。一边不停地查,一边一笔一笔抄,抄了厚厚一本子。我还搜集了后来很多人写的革命回 忆录。蓝田这个地方的山里头有过一个红军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都呆过,出了很多革命家,一个小小的蓝田县,解放后光部长级、军级干部就四五个。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926年白鹿原上的一个镇就建了党支部。我感慨,过去光知道瑞金是红区,延安是红区,从来没有想到我生活的白鹿原上也是最早 闹过革命的地方,我就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这些回忆录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好多事件后来都写到小说中了,当然都化成我的人物了。
我想西安周围农村的变化和西安和全国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读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我想把关中的事件和大的背景联接融合起来,那就不 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至于到原上,到民间去找村子里的,包括我们村的那些老人聊天、调查,那就多啦。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物情节就开始冒出来了,大概有两年的 酝酿,人物关系和结构就浮出水面了。
杨晓华:后来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您是从白嘉轩娶七房女人的描写开始的。小说发表的当时很有争议。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提 出 “身体叙事学”“身体文化学”“身体社会学”,回头再看,《白鹿原》当初从这个角度入手开启作品,是很深刻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整个作品的一个具有很大 文化隐喻功能的结构性安排。
陈忠实:对我来说,当时没有太复杂的考虑,很简单,在白嘉轩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具体的人身上,他父亲去世使他遭遇了家庭灾难,尽管事前事后他开 始承继族长。但纯粹说他的家庭灾难,意义不是很大,这个灾难可以集中体现在连续死几个女人这个事情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白嘉轩这样的一个人 看来,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妇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当时社会中是怎样一个存在形态?写了那么好几个女人,各有各的不 幸,连白嘉轩自己也丧气,说要不要再缓一段,他妈说:女人就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再糊一层。女人心目中的女人就是一张破纸!演绎几个女人的形象,就是 要让白嘉轩的母亲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要告诉读者,在封建社会里头,女人的社会生存是什么形态。这是一层意义。
还有一层更切近的意义就是,在封建社会,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权社会你没有儿子继承,你就是有万贯 家财,死了以后没人继承,就变成别人的了,就旁落了,你还有什么心思去积累财产?所以对男人来说,最大的人生恐惧就是绝后,所以必须要有人继承,他才有再 生产的劲头,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核心的社会理念,是宗法社会的关键支柱。
所以,是人物的精神心理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开头。我没有想到其他的开头方式。而且,一旦完成这样一个对人物心理特点的塑造,我就再也没有写白嘉轩和他后来的夫人怎么样。
杨晓华:您在讲文化视角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传统文化”,没有用“儒家文化”这个词。关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作为一个作家,您在自己的作品里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呈现,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陈忠实: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宋代出现了学派林立的现象。其中张载以关中为基地讲学育人,号称“关学”,历宋元至明清以后, “关学”已经深入八百里秦川的文化心理。为了创作《白鹿原》,我查县志,看到了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定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 ——《吕氏乡约》,我大为震动。这个乡约,用来指导乡民做人、做事、处世,是关中人精神心理上的一个纲领似的东西。《吕氏乡约》在这块土地诞生,后来传播 到南北各地,成为明清乡村治理的精神纲领。《吕氏乡约》的作者就是关中大儒张载的嫡传弟子、号称“蓝田四吕” 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兄弟。
我当时就想,刚解放后的50年代初,各级政府要给每个农民家庭订立爱国条约,在关中农村,每个家庭的门楼旁边,没有门楼也要在房子的墙上用白灰 抹出一块来,让有文化的人写5条爱国条约,比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劳勇敢什么的,家家都有。你看,宋代的儒家给农民定下乡约,那个内涵要比我们的简单 的5条要丰厚的多,而且很具体,容易教化民众,所以这个乡约就成为我理解那个时代原上人精神心理结构的纲领性的东西。
我并不研究儒家,我的作品也主要不是评价儒家,我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封建社会解体,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 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 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迁移或者裂变?不仅是大的社会运动的内容,更深层的是人的心理结构被打乱,甚至被打散。我是写这个的。实际上不要说那个时代的人, 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民众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没有完全解构完那些传统思想。不管是传统文化中美好的,还是腐朽的东西,都仍然在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理 结构。
杨晓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价值缺失和紊乱问题凸现出来,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重建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对此你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实:儒家文化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我的理解,“五四”主要是否定这个东西。解放以后,一味要接受新思想,我们整个 文化系统都是厚今薄古,发展到后来就是全面批判儒家,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把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了。从学校到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几乎都断 裂了。“文革”期间,那种残酷的批斗,把我们文化中美德的东西几乎全部毁掉了,真是惨不忍睹。这种摧残可以说比战争还厉害,战争主要是物质上的,死很多 人,但对活着的人没多大影响,可是“文革”对活着的人进行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后患无穷。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在“文革”期间也受到破坏。 新时期一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很自然就被商业利益驱使,很多干部贪污腐败,数量之大,不可思议。我确实也看到很多人提倡传统文化的东西,但这个构建相当 困难。
杨晓华: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语言上都格外追求创新,您对自己的文学语言也是下过很大功夫,有着高度自觉的,这种思维习惯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陈忠实: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我小时候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赵树理的。看完后,我也开始在作业本上写小说,我看赵树理那些人物都有外号,就也给我的 每个人物起个外号。后来,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在报上连载,我当时在初中三年级,认为柳青把关中的语言提炼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 语言,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必须在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个创作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 不长苗”,大树的叶子把阳光都遮住了。在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形成中,鲁迅对我启发很大。作家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写他的所有生活体验,他必须根据他体验到的内 容和人物,作品人物的气质独特性,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鲁迅写阿Q的语言不可能用来写祥林嫂。作家语言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精神气质。作家必须找到适宜于他 要表现的那个人物的精神气质的一种语言。这应该是语言创造最生动的东西。
《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对语言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描述性和叙述性语言的取舍问题。描述性语言容易把作品写长,叙述语言凝结性比较强。不 管写人写事情,如果用描述性语言写,需要100字,如果用叙述语言可能一句话就形象化地叙述出来了,这是我选择《白鹿原》语言方式的最要害之处。用白描语 言去写,《白鹿原》起码要写两部,91年、92年,中国文学开始冷下来了,如果有两三部那么长,读者读起来容易厌倦。所以我就想通过各种途径压缩篇幅,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叙述语言。为此,在写小说之前,我还写过两三个短篇,纯粹用叙述语言,其中一篇,从开篇一直到完1万多字,只有两三句对话。叙述语言难 度更大,如果功夫不过硬,不能做生动形象的叙述,那就干巴巴的,味同嚼蜡了。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