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科幻 >> 新闻 >> 正文
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科幻文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17日09:03 来源:吴岩 鲍德珍中国科幻作家一直盼望着21世纪。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明确地把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投放到2062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量作品描述过21世纪的中国。其中由郭沫若、华罗庚、茅以升等参加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 纪》,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但是,由于科学本身并非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包含着科学、想象力和未来憧憬的科幻作品在中国受到 过种种质疑。这些质疑除了认为小说中存在着与科学相悖的“错误”之外,还被认为背离社会主义理想。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文化和政治上的“水土不服”,科幻小说 在中国几番起落。新中国成立后它甚至一度从成人文学转化成儿童阅读的科普文学。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还曾被纳入“精神污染”范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科幻文学才基本摆脱政治束缚。那么,在一个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状况进行概况描述。
市场化中的科幻文学
世纪之交科幻文学创作的发展,虽然初步摆脱了政治干扰,但却遭受到市场压力的严重冲击。从2000年 起,受到英国作家罗琳的小说《哈里·波特》系列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科幻文学都进入退潮期,奇幻文学占近了幻想读物的风骚。这期间,除大量翻译了西方奇幻小 说之外,中国本土的奇幻文学创作也方兴未艾,出现了《幻城》、《诛仙》、《搜神记》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年热衷科幻出版的单位,此时此刻都已转向奇幻 领域,只有《科幻世界》杂志等很少几个出版机构仍然坚持科幻原创力量的培植。
世纪之交科幻文学经历的另一个发展瓶颈是如何在上一代作者普遍停止写作之后,尽快培育新一代作者,提高他们的创作质量。在此期间,成都《科幻世界》坚持每年一次的银河奖发奖大会,给作家相聚讨论创作问题的机会,同时,通过奖掖优秀作品鼓励新人进入领域。2003年,北师大文学院将科幻文学设置为现当代文学中三级学科,此后连续召开了“科幻与后现代学术报告会”、“科幻与创造力、想象力学术研讨会”、“2007中 美作家科幻峰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全面对科幻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国家社科基金也首度对科幻文学研究进行 了项目资助。在这些会议、研讨、项目执行中,人们逐渐理清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脉络,也对作为第三世界东方国家的科幻文学到底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有个更多 把握。
在出版和研究机构努力为科幻文学恢复地位营造条件的同时,科幻作家也积极地适应市场的发展。例如,以潘海天、今何在、江南等作家为首的一群作家,积极 地将科幻与奇幻文学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所创造的《九州》系列作品,想象出一个全新的奇幻宇宙,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充满了科 技进步,而有些地区则停留在古代甚至魔法时期。这种将科幻与奇幻结合的设计,巧妙地在奇幻文学风潮中保护了科幻文学,更为科幻小说发展找到了新的空间。科 幻作家并非简单地适应奇幻文学的入侵,他们也利用自己的独特表现手法试验性地改造奇幻文学。例如,女作家钱莉芳的小说《天意》,采用科幻作品的时空旅行手 法重述历史,这一行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穿越小说在中国的兴起。当然,更多作家坚守科幻文学的基本领地,深度耕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逐渐恢复人们对科 幻文学的兴趣,在奇幻文学走向退潮的同时使科幻文学复苏。在这些作品中,王晋康回顾文革的小说《蚁生》深度发掘了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潜力;韩松的远未来小 说《红色海洋》从人类学角度检讨了中国历史和未来人的生存状况;刘慈欣的技术突破小说《球状闪电》和《三体》将笔触深深介入当代科技前沿,展望了宇宙的发 展;江南的《上海堡垒》针对1970年之后出生的读者,借助卡通电影重返一代读者以往的记忆。还有更多中短篇小说也分别在相关领域中获得了读者的认同。营造了一个科幻市场逐渐回归的局面。
在上述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韩松和刘慈欣。
韩松和他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
韩松,1969年 出生于重庆,现为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参与创办《瞭望东方周刊》。担任记者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文化动态的专访,他还参加过中国第一次神农架野人考 察。由他参与或单独创作的长篇新闻作品包括政论性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韩松的科幻文学写作起源于大学时 代。早在1991年,他的小说《流星》和《宇宙墓碑》就曾经同时在海峡两岸的科幻征文中获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或火星照耀美国》、中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等。1999年他出版的《想象力宣言》,至今仍然是中国科幻文学领域见解独到的作家独白。近年来,他还提出“中国的现实比科幻小说更加科幻”这一独特的科幻现实主义理论。
韩松在新世纪最著名的作品是《红色海洋》和《地铁》。两部作品内容不同,构造不同,但却在同一种风格之下演绎了当前的中国现实。《红色海洋》应该被定 义为一部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篇科幻小说,期间后共分四部。第一部描述在遥远的未来中,人类全面退化并移居海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恐 怖、威胁和压力之下的严酷的世界。此时,分散于海洋各地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种族,在生理构造和文化传统上都显出惊人的差异。就连个体之间也差别惊人。但生与 死、抵抗与逃避、吃人与被人吃则是所有种族都无法逃避的命运。超越万亿年的历史流动、那种覆盖整个地球的宏大场景、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精彩较量, 已经毫无疑问地能将该书载入中国科幻文学的史册。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重点回答了红色海洋的由来。作者着力给“第一部”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起源假 说,每个假说都具有寓言的性质,都复杂异常,充满了不可能的灵异,但都貌似有着现实合理性。于是,整个人类的过去被悬疑,被质问,所有的行为的起因和结 果,都成了某种可能与不可能、是与不是之间的摇摆物。小说的第四部的标题为“我们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一部中讲述的都是有关中国过去的“历史故事”。从 郦道元开始巡游全国试图为《水经》作注,到朱熹兴教,再到郑和七下西洋发现欧洲非洲甚至美洲,历史再度从某种不稳定状态回归稳定。如果说作品开始于宏伟壮 丽,开始于血色斑斓,那么它就结束在清新优雅,结束在竹林中的清丽水珠。如果说第一部中的血与死是浑浊的,那么最后一部中的希望与失落则充满了幽深感和隐 蔽感。对历史和未来的质疑是作品的核心。《红色海洋》看似科幻实则现实;看似倒序实则顺序;看似未来实则历史;看似全球实则当地;看似断断续续前后不接, 实则契合严谨。作家所尝试的颠倒历史、循环历史、多义历史的叙事方式,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显得非常少见,它所描述的东西方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和个体 生存的关系,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当代科幻、甚至主流文学作家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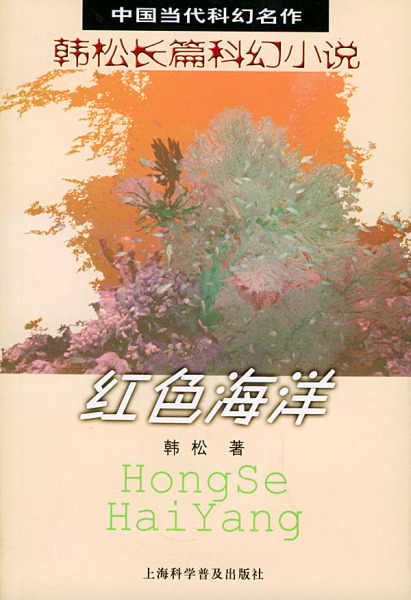
与《红色海洋》一开始就营造“大尺度+远未来”的史诗气氛不同,《地铁》初看起来是有关当代城市生活的作品。小说由一些按照正常时序发展的小故事组 成。下班回家,主人公在疲惫的眼花中看到了一些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随着陌生化的逐渐升级,列车也逐渐失控,在甬道中疯狂地飞奔。于是,封闭的接车中上演 了种种人间闹剧:乱伦、杂交、未婚先孕、未孕先生子,种种超出理性的行为和实验猛地爆发出来,地铁世界映射了一个社会的爆炸性发展。车厢之外,蔓生的恐怖 植物“地铁之友”包裹过来,老鼠也成群地出现。这些内外之战、人鼠之战,不断让人想到今日的国际对抗和经济体内部的阶层对抗,而对抗中的惊变,震撼了整个 世界并重塑了世界的格局。小说最末一章描述了这一奇异的变态发展的遥远后果。韩松在小说中再度跳出民族/国 家这个束缚人的既定视角,打乱内外差别,观察了异族、鼠族等不同种族的可能发展。作品是以家园毁灭结束,简单的乘坐地铁回家之旅,最终演化成为了无家可归 的恐怖现实。《地铁》是韩松式科幻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虽然其中充满了后现代式的多义和多疑。作者采用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多点投射,给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 可能性。
刘慈欣和他的新古典主义创作
刘慈欣生于1963年,现为山西娘子关发电厂高级工程师。从80年中后期起,刘慈欣就在不同的场合尝试发表科幻小说。他的风格多次变换直到90年代中期才逐渐定型,并开始赢得读者的喝彩。1999—2004年,继刘慈欣蝉联《科幻世界》杂志读者评奖的冠军。刘慈欣的主要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阳》、《带上她的眼睛》、《微纪元》以及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和《球状闪电》等。从2006年到2010年,著名作家刘慈欣用四年时间创作了长达90万字的“三体”三部。作品第一部《三体》于2007年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由于其宏大构架和涉及文革、冷战、军事争霸、外星球生命探索等内容,立刻获得了读者的交口盛赞。此后,三部曲正式出版,部部刷新近年来中国成人科幻小说的发行记录。仅以《三体III:死神永生》为例,该书出版后仅仅一个月已经重印数次,创造了新世纪10年中科幻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三体系列》小说由《三体》、《三体II:黑暗森林》、《三体III:死 神永生》组成。系列的文本构造、叙事风格、语言使用、甚至人物命运等的复杂程度都达到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当代顶峰,而作品对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强烈兴趣,其中 所包含的前沿科学技术理论,无可置疑地将作者推向当代作家中最为博学者的宝座。小说针对中国在未来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由近及远地设想了种种发展的路 径,这其中隐约能感受到一种大国兴起的躁动。所有评价都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具有可读性的、让人浮想联翩和深入思考的作品。
与韩松吸纳后现代风格的批判性作品不同,刘慈欣的创作仍然沿袭古典主义科幻的轨道进行。这里所说的古典主义,是指他继承了英美黄金时代、苏联派30-60年代和中国50-80年 代早期的作品风格。这其中,英美黄金时代小说充满经典的现代性特征,表达了人类对科技发展的未来憧憬。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通过自 己的生活引领着未来发展,也把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英美黄金时代小说故事结构完整,社会生活背景壮阔,叙事跌宕起伏,对科学技术描写细致入微。最重要的 是,小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会在结尾升级为一种哲学探讨,给人深远的意境。以亚瑟·C.克拉克为例,他的小说《童年的终结》、《2001:太空探险》、《天堂的喷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他在《2001: 太空探险》中所摸索的精神物质相互转换的宇宙生存模式曾经使许多人为之赞叹和倾倒。《三体》系列的作者曾刘慈欣多次表示,他是克拉克的学生,他受到克拉克 的强烈影响。在《三体系列》中,以宇宙探索为核心的创意故事引领着读者的阅读。而三体生命的发现、以及随后而来黑暗森林中的形形色色的外星生命的存在,把 读者带向了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在此同时,人类对宇宙灾难的反应方式、反应的过程,则又是读者渴望了解的焦点。到小说的结尾,整个宇宙竟然在中国文革中的 某个偶然过程中发生了彻底变化,人类在巨大的毁灭之下获得了全新的宇宙认同。所有这些都已经超越了对物质世界的思索,进入到对生命和宇宙目的性的终极追 问。也恰恰是这种对英美黄金时代的继承,导致刘慈欣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跟西方世界对话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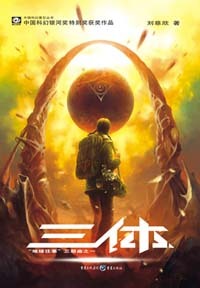
但是,刘慈欣不单单是黄金时代的继承者,也是对这种风格的批判者。由于英美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在处理民族/国 家关系方面存在着强烈的东方主义和自我优越感、习惯于按照简单的进化关系描述全球对抗,刘慈欣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尽力铺陈出社会关系的复 杂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国际主义原则也在此处发挥了积极作用。谈到国际主义,不得不提到刘慈欣对另一个现代性强烈的科幻资源的继承,这就是苏联科幻小 说。在前苏联,科幻小说保有跟英美黄金时代作品一样的对大工业文化和科技的崇拜,但用积极的情绪营造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情怀,则起源于他们的共产主义背景。 在苏联模式中,集体主义没有被认为是一个贬义的词汇,恰恰相反,考虑到共产主义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这个意识形态前提,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常常表达出对其他 世界不同文化的偕同性。在苏联作品中,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与亚非拉人民共同开发宇宙的故事常常会出现,而恰恰是这种各民族平等的情绪情感带给刘慈欣 另一种有价值的营养,协助他处理了小说的情绪和国际关系。当然,刘慈欣也对苏联模式的简单化和幼稚病进行了批判,例如,他尽力不使自己的作品落入简单意识 形态判断,尽量将复杂的道德冲突展现出来的努力,都获得读者的认可,更引发了读者的思考。
在有效继承东西方各种优秀的创作模式的同时,刘慈欣还力图对中国科幻小说中已经消失的、仍然具有活力的部分进行挽救和发掘。由于20世纪70年 代末期开始,中国科幻作家的主流群体否定了鲁迅等人所定义的科普发展方向,转向一种反思社会、批判现实、淡化故事的全新文本构造形式,造成了科幻作品对科 技创意丧失了关注。这一点在刘慈欣看来是一个极大的失误。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出,以科普为核心的科幻小说并没有错误。它是一种适合于中国的作品风格。在刘慈 欣的陛下,这种风格“有些象凡尔纳和坎贝尔倡导的小说,但它们更现实,更具有技术设计的特点。同时在写作理念上也同前者完全不同:这些作者是为了说出自己 的技术设想才写小说的,看过那些小说后你会有一种感觉:那些东西象小说式的可行性报告,他们真打算照着去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创造的科幻!” “我并不主张现在的科幻都象那个风格,但至少应有以科普为理念的科幻做为一个类型存在,在这个类型中,科普是理直气壮的使命和功能。要让大众了解现代科学 的某些领域,可能只有科幻才能做到。科幻小说向神怪文学发展,被人寇以向主流靠扰的美名;而来源于科学的科幻向科普倾斜却成了大逆不道,这多少有些不公 平。” 《三体系列》正是刘慈欣用实际行动继承中国科幻的古老科普传统的一个有力行动。在小说中,高深的物理学和宇宙学分析、对外星生命存在形式、对电脑技术和宇 航技术发展的描写,都强烈地向读者证实,科幻文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不但能展示给作品强烈真实感的科学技术细节,还能展示中国社会的发展新阶段。从上面的 三个源泉可以看出,恰恰是继承了古典主义的科幻风格,才导致了刘慈欣的作品真正回到了科幻文学最核心的魅力点上。这也为将来的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借鉴。
以上简单介绍了新世纪10年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随着2010年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人如何思考未来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各国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科幻 文学的复兴,无论对中国读者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都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养分。可以展望的是,受到当前出版市场复苏的影响,在未来的10年,中国科幻文学还将有所发展和创新。
本文最初是吴岩和鲍德珍(JANICE BOGSTAD)为奥克拉和马大学主办《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6月号所做介绍当代中国科幻发展的文章,中文版由吴岩进行了较大改动且发表于《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第四辑)。王鹏飞翻译了全文。写作中还参考了郭凯为《2009中国最佳科幻作品集》提供的部分序言章节,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评论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