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香港电影工业最令人惊喜的bu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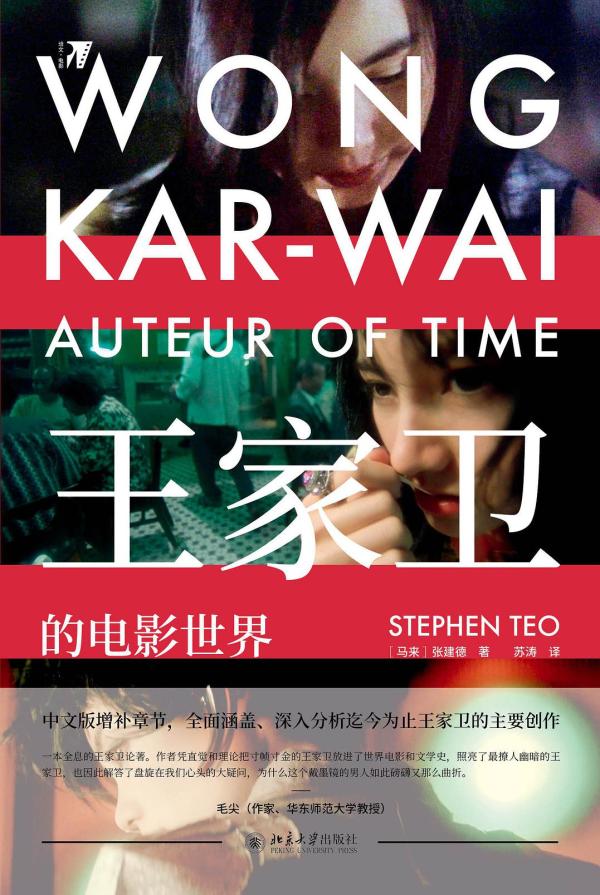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马来]张建德著,苏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288页,60.00元
1977年夏,香港,地下步行街的牛仔裤店。
不到二十岁的陈以靳在这打工了大半个夏天。她有点郁闷,同在店里暑假打工的高个子男孩显然对自己颇有好感;可已是暑假实习的最后一天,他仍旧没什么表示。
终于,他还是走过来,问她要电话号码。
“电话可以给你,但六位的号码,我只能给你五位——最后一位数,要你自己去猜。” 陈以靳留了最后一丝矜持。
可本应在当晚就响起的电话,她却等了整整三天。当时她或许还不知道,这个大男孩日后将会以“拖延症”闻名于世。她更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个男孩,她不乏小小心思的浪漫举动将会被改编到电影中,她自己不仅为近十部香港电影的女主角提供了灵感与原型,也成为后者几乎大部分电影的出品人。
某种意义上,陈以靳成就了“那个男人”——王家卫。
一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需要调动情绪去感受,却很难付诸文字去分析。他的电影中充斥着暧昧的创痛、不可见的伤痕、斑驳的色调、后殖民的隐喻,这些原本都应是学院化电影研究最擅长、也最热衷探讨的视听文本——但欧美研究者往往会透过《花样年华》的滤镜来检视他的所有作品,以至于那些充满历史感和离散气味的愁绪会被消解在矫饰主义的审美愉悦之中;而具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往往又因自身的美育传统,过分在意他电影中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或彻底拥抱、或嗤之以鼻,非黑即白地将他推向褒贬两极,全然忽视了王家卫电影中那种不可捉摸的暧昧与歧变。
由新加坡学者张建德于2005年英文初版、2021年增订后中译的《王家卫的电影世界》(Wong Kar-Wai: Auteur of Time)一书,则悠游于王家卫电影中的文学性、拉美性、后殖民语境和身份政治之间,试图触达墨镜镜片之后的电影视界。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学者张建德(Stephen Teo)早年曾赴美学习导演,结束学业后便长期服务于香港国际电影节;之后从策展逐渐转向研究,先是在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从事香港电影研究。多元的文化身份使他既得以跳脱欧美世界对王家卫纯审美式的异域迷醉,又不至囿于华语学界的小布尔乔亚迷思。
相较于香港精打细算、成熟高效却高度复制化、流水线化的电影工业,王家卫简直是个异数。他的拍片过程精工细作,依靠现场灵感和即兴的创作习惯;他完全不按照类型片套路去创作武侠、警匪、爱情、科幻等题材的文艺片;他将顶级明星晾在一旁,从事现场编剧,在胶片时代用昂贵的胶片打着草稿,在剪辑台上才开始真正的创作——凡此种种,都与香港电影工业体系当时的创作环境格格不入。王家卫成长于工业体系内部,但本人却是一个极端反工业的存在。他的原创性的个人表达与创作习惯,与工业体系所要求的流水线化生产南辕北辙——既无法制作出符合观众预期的类型片,也几乎无法以低成本量产来维系片厂对盈利的要求。
然则王家卫仍得以生存,无疑是仰赖以欧洲电影节为中心的电影分销市场及其背后的全球化影视消费工业。VHS、VCD的兴起使得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这样的影痴有机会接触来自东方神秘的视听术士,并将之介绍给美国最重要的独立发行商米拉麦克斯(Miramax),使王家卫在海外得享大名。欧洲电影节选片人刁钻的口味让影像质感如此独特的尖沙咀流民的电影从卢加诺、戛纳走向世界各地。而2000年《花样年华》的全球流行不仅使得那个永远戴着墨镜的男人步上神坛,更是让他成为包括索菲亚·科波拉(Sophia Coppola,《迷失东京》)、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月光男孩》)在内的诸多导演所推崇的导演。《2046》入围戛纳时,倨傲如戛纳甚至为了《2046》的拷贝运输而调整了原定的放映计划,虽然临场调整与制作周期和突发情况等因素高度相关,但在戛纳历史上只有《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等少数几部电影才能享受这等“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待遇。
自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创立以来,欧洲三大电影节都有超过七十年的历史,战后也一度将关注视线转向欧洲本土的电影传统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在三大节上也偶有斩获,但直到1980年代后,非欧美的第三世界电影才真正越来越受到欧洲电影节评价体系的重视。反香港电影工业性的王家卫正是这一波电影节审美视野外延的受益者。建立在电影节评价体系之上的国际电影发行市场的销售繁荣和口味驳杂,给予了各国反工业化、反商业化、去国营片厂体系下的艺术电影以商业化的可能。广阔的国际市场和慧眼识珠的“老欧洲”使得热衷于精雕细琢的王家卫有了足以维系公司的潜在市场和源源不断的投资人。
王家卫能够在成王败寇、速食文化的香港电影市场存活下来,更多依靠的是香港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电影舞台。当然,他既深谙东亚观众的文化基因,也能用炫目的影像惊艳欧美观众,这使得他更是超脱于传统流水线工业体系的束缚,拥有令其他创作者嫉妒的、奢侈的创作自由度——甚至他的拖延、任性、超支、对大牌明星档期的挥霍、扣下护照的雷霆手段都成为令人莞尔的谈资和老梗,而非濒临破产的资方对艺术家的指控。这些“光辉事迹”之所以会定期被拿出来调笑一下,其根源无疑是王家卫身上根深蒂固的反工业属性。
二
相比反工业的商业生存之道,王家卫更受关注的无疑是他独特的美学风格。无论是他破碎、含蓄的叙事风格,还是华丽、丰富的影像风格,乃至文艺腔的独白、对白,对音乐、光线、色彩和造型颇显另类的使用,都使他成为一代影人反复揣摩和琢磨的对象。
然而王家卫的风格也并非一蹴而就。与普通观众所线性理解的“故事-编剧-立项-拍摄-剪辑-成片”的大致顺序不同,王家卫的创作缘起往往来源于一两个概念,在《春光乍泄》中是1997年前后的“承认”,而《2046》则关乎“承诺”,到了《一代宗师》就在探讨“承继”。王家卫的创作以主题概念为创作起点,然后再寻找适合展开主题的情境、人物,最后其实才是故事(或曰情节)。所以在他的电影中,情节往往是破碎的、片段的、吉光片羽的、惊鸿一瞥的——他的故事像摔碎一地的精美屏风,每块精致碎片都能让我们对故事的端倪管中窥豹,但总也无法将整块画屏拼合完璧,甚若这幅屏风完好无缺,反而少了余味、缺了韵致。
王家卫这种将碎片化的情节、情绪、情境合缀一处再敷衍成篇的能力,受到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的影响,尤其是《伤心探戈》(Boquitas pintadas)。后者看似随机的、如七巧板般的、时序错乱的多视点叙事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所以无论是国族的历史叙事,还是个体的生命经验,在王家卫这里总是会被打散成切片状的剖面,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不是因果逻辑明晰的情节故事,也不是时序如年谱般齐整的线性时空,而是好似烟圈慢慢飘散却又绵延不绝的情绪。概念生发出情绪,情绪引动了人物,人物勾连起故事,这就是王家卫电影叙事最基础的创作方法。
但在王式影像叙事中,仍存在着断裂与转折。2000年前的王家卫更加粗粝奔放、元气淋漓。他与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张叔平的铁三角以相当激进甚至莽撞的艺术姿态,试图捕捉殖民时代香港的仿徨、游离与孤独。《阿飞正传》结尾处为满足发行合同条款的信手涂抹的余笔、《重庆森林》里的拖影抽帧、《堕落天使》里的鱼眼镜头——虽然很多都是限于客观条件下无心插柳的被动发明,但却形成了相当鲜活、率性、斑驳的强风格。
但自2000年《花样年华》之后,王家卫却变得愈加精致繁复、含蓄婉约,影片在细节层面越发纹理细密、颗粒精微。如果说新千年之前的王家卫可以在穷街陋巷的破败中发现绮丽、在物欲横流的场域中发掘情感,那新千年之后的他则唯美得近乎空洞。早年主人公近乎自毁的残酷转为缠绵悱恻萦绕着的情丝,暧昧的历史隐喻为私密化的个体情绪消解;在前期作为底色的后殖民时代的香港逐渐铅华褪尽,而包装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下的主题最终止步于矫饰主义的个人生命经验。
王家卫的世界变得更美、更深,但也更小、更薄。
三
然则从全球接受的角度看,正是更美、更深的精致与浪漫使得王家卫得以在2000年后行销全球。2000年前的他,虽是塔伦蒂诺的心头好,但却只能作为学院影史评价体系中奇异的东方代表;但在2000年之后的他,却变得更加大众流行。他镜头下既有让西方人目不转睛的东方符号,也有能让他们充分理解共情的爱情故事,而韵律独特的拉丁化音乐(纳京高[Nat King Cole]、哈维亚·库加[Xavier Cugat])更是让本已极度东方异域化的情调增添了探戈式的勾魂和撩人。
王家卫电影中体现出了一种审美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与同作为当代华语导演代表的李安不同,李安电影不仅在工业技艺上异常工整规范,在故事的内核和叙事上也极具普遍性(universal),这使得他可以同时驾驭华语题材和西方题材,而观众不至于有太过出戏的感觉。而当王家卫深入西方话语体系中拍摄《蓝莓之夜》(My Blueberry Nights)时,却无法像李安那样自在地表达几乎没有东方色彩的视听影像。
但王家卫的电影一方面极度在地化、本土化。他将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的后殖民与地方生活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面既有符号化的旗袍、麻将,也有人情世故上讲面子、懂隐忍、喜含蓄的东方处世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度全球化:其中虽不乏窥探奇巧淫技的东方主义式目光,但王家卫也或通过东方符号、或藉由拉美风情、甚或借助致敬、暗合以接榫西方人影评人所熟知的欧洲影史传统,成功地使得自己的电影具有了被国际接受的可能性。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王家卫的电影天生具有(或也不乏刻意为之)一种西方影节评价体系与东方电影美学之间的“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这使得他的电影在保持东方面貌的同时,也能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这与张艺谋《红高粱》、陈凯歌《霸王别姬》作为欧洲三大节体系新奇异质的闯入者、以及备受欧美文化精英青睐的、隐喻符号学式的贾樟柯作品在接受广度和深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果将香港电影工业比作一套运转高效的软件程序,王家卫可能是它最令人惊喜的bug;如果导演工作是一项具有可重复性的科学实验,王家卫或许是一个不符合预期、但却误打误撞的美妙发现。他如此特殊,却又如此让人共情,他的全球流行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到了一隅二者兼擅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在他历史叙事的隐喻与时代精神的弥散中各取所需,却又能在其碎片化的唯美表达中体认到共享的感知。尤其对自诩孤独的现代都市男女而言,王家卫的电影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情绪致幻的奥德赛——虽然电影并不长,虽然离开影院又会回到那个真实世界,但在这一刻,真的好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