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周恺 2019年06月13日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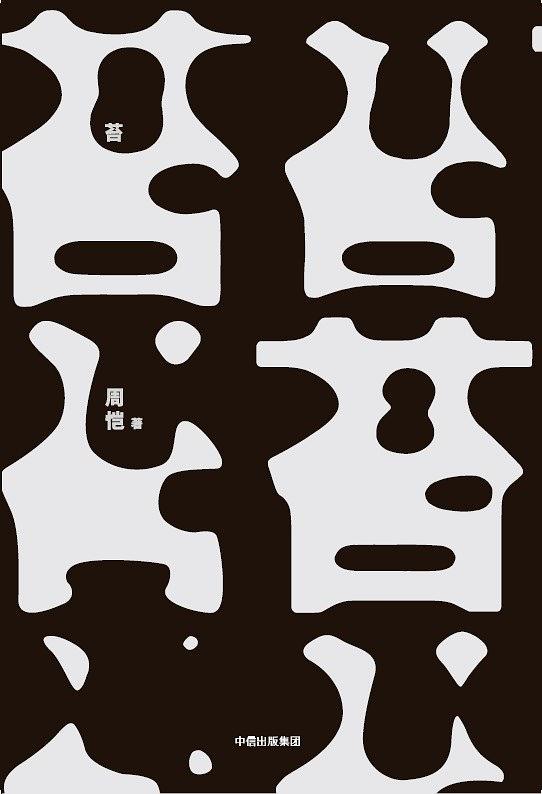
《苔》
90后新锐作家周恺的史诗级小说;一个晚清家族,一出袍哥传奇,一场历史风暴,一曲时代挽歌;著名作家苏童、叶兆言、于坚、韩东鼎力推荐
作者:周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ISBN:9787508691923
定价:68.00元
内容简介
历史如风,
众生如苔,
听江水拍岸,
见人间无常。
本书作者周恺披阅群书,跋涉山川,以大悲悯之心,为当代人讲述了一段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家族故事。
话说晚清年间的四川嘉定(乐山),富商李普福家财万贯,妻妾六房,却无一子嗣承续香火,正巧碰见一户桑农生了对双胞胎,便抱养了其中一个,取名李世景,而另一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为刘太清,从此两兄弟际遇悬殊。
小说以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再现了蜀中百年前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茶馆、染坊、饭铺、酒肆、青楼……市井之气,喷涌而出;袍哥、山匪、买办、纤夫……江湖之上,人来人往。阅读此书,如闲坐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千头万绪,真假莫辨。
作者简介
周恺,1990 年生于四川乐山。2012年在《天南》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2013年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前 言
方言之魅,职人之作
文\欧宁
这是一部30 万字的“巨构”,时间跨度从光绪九年(1883)到辛亥革命(1911),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几乎相同。《苔》的故事发生地为嘉定(乐山旧称),周恺显然下定决心来写一部他家乡的断代史。隔着这么久远的距离却又要写出“临场感”,这正是小说要迎接的挑战。它与历史研究之类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不仅要求作者收集和研究原始素材的能力,更考验作者的想象力和重新组织叙事的能力。不像很多从个人经历出发的年轻作者,周恺一开始就偏向用第三人称讲述“他人”的故事,他没有被自己的肉身体验所限,而是依靠阅读和考证去拓展自己的眼界,到方志、族牒、传奇、掌故、旧闻中去开挖他的文学矿藏。
这部长篇从一个回乡重整家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寻找新生儿承续家族香火写起,以桑农刘基业的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为两条线索(李世景被抱入李家成为土豪继承人,最后资助革命党;刘太清则留在底层成为石匠,最后变成绿林山匪),中间穿插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把大清政权的危机、反对派的滋长、秘密会社的活跃、地方秩序的迭代、大家族没落的故事,渐次编织在周恺的家乡地理的经纬网络上,把嘉定这个地方的二十多年的嬗变浓缩于一册书写。相对于王笛和司昆仑那些以真实和科学为准绳、聚焦于四川特定时期的微观史学著作,这样的文学书写能把读者更深入地带到更逼真的历史现场。随着叙事线索的展开和文学细节的放大,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Kuhn)等时常也要收纳文学作品这种非信史材料,甚至汲取文学叙事的写法。周恺在这部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
各个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他在这方面下的苦功夫,夯实了他的虚构写作的历史背景,为故事的叙述铺设了清晰可见的时代底色。而对那个时代的乐山方言的进一步淬炼,更是加强了这部小说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苔》对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的师承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但让周恺区别于李劼人的,正是他们各自写了不同的“地方”:李劼人写的是成都地区,周恺写的是乐山地区,尽管共享了四川一省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但它们分属两人文学世界不同的“原乡”。每个“地方”,大至一国、一省、一城,细至一个街区、一个村庄,都有各自的DNA,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非常细微。通常辨识一个“地方”的依据是“地方知识”,古希腊称之为“米提斯”(metis),它是指一个地方独有的无法被转译为通识的经验。例如方言、地方性的度量衡、未经规划自发形成的社区地理、历史记忆、邻里关系、身份认同、食物偏好、传统手工艺、以身体进行记忆的秘诀等等,它是匿名的,没有个人著作权的,它会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适,但始终根植于一方水土,帮助形成地方风俗和地方性格。对这种地方知识的获得,来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经历以及后天继发的研究,它对人的长期濡化,进而会使人形成对家乡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个词由英国诗人约翰• 贝杰曼(John Betjeman)首创,后来被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普及,用来指称人与地方或环境的情感纽带。正是这种指向不同的“恋地情结”,形成了李劼人和周恺文学世界的差异。
《苔》可以称得上是乐山“地方知识”的集大成者,而周恺对乐山的“恋地情结”,则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发育生成了一个闭合自足的地景系统。如同《繁花》一样,它是对全球化无差别文学生产线的抵抗。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众多语种写作中的一个小的系统,而地方性题材的方言写作又是更小的系统。从国族差别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写作,都要从他们共享的中文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养分,这样才可以形成与其他国家或语种不同的“中国性”,而不同国家或语种的流通,则要交给翻译来完成。从《苔》和《繁花》往前追溯,可以看见的是一条从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到曾朴的《孽海花》,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明清话本的清晰的营养链,不同时期的文学风景扎根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但它们血脉相通,共处于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的同一生态位。诚然,地方性的写作会提高交流成本,一部30 万字的中文小说可能不符合英语出版市场适当可控的字数标准,但作家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写作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方印记,才是真正有机的世界文学图景的构成要素,它们是从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千差万别的植物,而非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
阅读《苔》如同欣赏一件职人手作,它以经年累月的劳动打磨而成,你不知道它的窍门在哪儿,但光滑的语感和复杂的故事肌理让你惊奇不已。又如同在市井街头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只见七嘴八舌,人声鼎沸,但说法千头万绪,真假莫辨。它涉及的人物五花八门,都是动荡时代里如苔草般附土求存的生命,在方言和地方环境的包裹下,个个都带有川人的性格因子:从精明的富商李普福,到狡黠的蚁民刘基业;从懵懂成长的李世景,到沦为匪寇的刘太清;从道貌岸然的书院山长袁东山,到激进勇猛的革命党人税相臣;还有数不清的次要人物和众多的女性角色,但小说没有女主角,唯一着墨较多的是李普福的幺姨太,因与刘基业私通而被溺毙。如同徐皓峰的一部民国小说《大日坛城》一样,《苔》写的也基本上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里面的女性人物在故事主线中没占多少篇幅,或者写到了,但人物欠缺主体性,这恐怕也要和徐皓峰一样遭到女性主义读者的诟病。幺姨太虽然敢于越轨,但并不像李劼人《死水微澜》里的邓幺姑那么火爆激烈。李劼人写邓幺姑,是自然主义的写法,并不是对流行的妇女解放观念的图解。读者大可不必执着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的政治正确,也不必用今天的性别理论去要求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产生的文学流派,主张超级真实,作家要隐藏自我,力求客观,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写作,不强加观点,不塑造典型人物,不追求戏剧性。这个在二十世纪已不是什么新手法,它甚至被引申为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绘画和雕塑,以及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基本原则。
《苔》继承了李劼人的自然主义笔法,孜孜以求一个地方历史的真实。为了保持客观冷静,它甚至去掉了《阴阳人甲乙卷》中那种带有历史书写者口吻的评论和感慨。乐山和四川的读者应该感谢周恺,他为自己的家乡写作了一部充满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的大传。《天南》曾经的作者阿乙和任晓雯最近出版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和《好人宋没用》也是展开地方书写的长篇作品,前者聚焦江西瑞昌,后者聚焦上海,都是他们各自的出生地。这令我想起小时阅读的黄谷柳的《虾球传》,尽管带着我那时尚不能辨识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对珠江三角洲泛粤语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却令我备感亲切。我们的生命被造物主投放在一个不能自择的地理上的小点,随着我们的成长,这个陌生的空间慢慢变得熟悉,慢慢变成承载记忆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离乡远行,它变成了我们不断思念的原乡。在全球化无远弗届、人与事激烈变迁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来保存我们的地方知识,激活我们的地方记忆。
2018 年4 月23 日,芝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