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星球》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彭扬 2018年09月30日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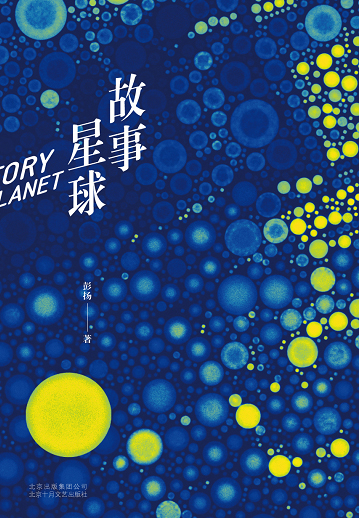
《故事星球》
作者:彭扬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编辑推荐
《故事星球》是80后新锐作家彭扬的长篇新作。这是一个寻找故事的故事。一个赤子追梦的童话。一部普通人的创业史。一幅科幻世界的浮生绘。作者紧扣“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时代主题,将现实的创业理想与心中潜藏的科幻梦想融于一体,同时注入现代青年精神。在作品中,我们得以体味独属于青年一代创业者的困惑与迷茫、抗争和奋进,一代“伟大的失败者”永不言败、绝不放弃的豪迈和对于心底自由生活的无限想往、永恒追求。
“中国在长高”——“故事星球”的创建者意识到了自己创业不败的信心前提和源头。他们的梦想有多大?“大得刚好可以实现”。这部作品,让我们从青年创业生活的视角,真切地感知用真本事,靠诚实劳动和拼力奋斗构筑的“我的梦”,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梦”踏实又飞扬、沉稳又活跃的青春质地。作者也借由写作,创作了一个由真挚、美善、理想、尊严编制而成的“故事星球”——在这个星球上,“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
2018年3月,《故事星球》获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奖。
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故事星球》讲述了从职场裸辞的青年阿信决定自己创业,并集结了自己的小伙伴组建创业团队“梦之队”,打造手机软件“故事星球”App的故事。作品洋溢着青春气息,时代感很强,年轻人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勃勃生气和运用新科技手段创业的故事框架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的关键词是“天真”,在想象力的一路盛放与目标落成并无限延展的颠簸之旅中,那份要做一个“干净的公司”的有所秉持、那份不做“土豪”的有所谢绝,是其态度,也是时代与青年相契合的能量,令作品有神、有力。在这部《故事星球》的创造过程中,作者彭扬试着把生活变成文字,去书讲述一个让无力者重新找回力量,让悲观者再次上路前行的故事。而本书的创作,也是一次“个人的情感”向“辽阔的体验”的出行,是一次与周遭的俗世生活温驯相处的记录者向到世界上去的探索者的转变,也是一次让无力者重新找回力量、悲观者再次上路前行的尝试。
作者简介
彭扬,青年作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中学时在《当代》发表小说处女作。至今已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多篇,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并被译成英、法、意等多种文字。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提名奖、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奖、首届Prada费尔特里内利文学奖等。2015年,专著被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
目录
1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群比自己还笨的人创造出来的呢?
2有需求就有生意
3故事的人
4董事长这种生物
5“鸟笼”里的公司
6英雄帖与“猪鼻子”
7黄金眼
8魔女的晚餐
9站着的和趴着的
10彩蛋学
11王国之心
12疯狂的劳励士
13价值与估值
14失败大学的优等生
15进击的新人
16天真终结者
17船长之心
18创新的基因
19人不是一个复数的词
20失败者的美丽
荐语
《故事星球》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中国在长高”——“故事星球”的创建者意识到了自己创业不败的信心前提。他们的梦想有多大?“大得刚好可以实现。”这部小说,让我们从青年创业生活的视角,真切地感知用真本事奋斗构筑的“我的梦”,而这,恰便是“中国梦”踏实又活跃的青春质地。
作品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做递进式解读:首先,可以当作“创业怪咖”的“经书”,对科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对前沿科技的新颖应用与推进开发的能力,是其底气,因此这份愈挫愈勇的“开山怪”成长史,令作品有料、有型;再就是,语言、故事和人物、情境都既“潮”且“炫”又有日常性的扎实,自成积极新鲜的调式、紧凑饱满的节奏,是其才情,令作品有趣、有光;更难得的是,作品的关键词是“天真”,在想象力的一路盛放与目标落成并无限延展的颠簸之旅中,那份要做一个“干净的公司”的有所秉持、那份不做“土豪”的有所谢绝,是其态度,也是时代与青年相契合的能量,令作品有神、有力。
无力青年形象过剩,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多年。说到底这种现象来自对生活的懒散观望和信心不足,闭门瞎想,视野越写越窄、形象越写越矮,常常有许多人许多年都在重复着同一个“梗”——人物关系、俗世味道、情节路数相近的同一个故事。中国的创造、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天真,那些不可破碎的形态、不可轻慢的抵达、不可丢弃的心灵,《故事星球》都给予了有点吃力而决不气馁的现实回应。当今时代,真切存在着无穷的为实现美好梦想而奋斗的各具神采的探索者们,他们不在自闭的懒人日益窘迫的冥想中,而是在需要我们以天真去探寻和以初心去深扎的广袤地带。
“好内容力大无穷。”中国在长高,中国故事亦应如是。
——《人民文学》二〇一七年四月卷首语
创作谈
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
彭扬
乔布斯去世的那一年,由于航班延误,有天我被困在了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夜晚的登机口怨气盘桓,灯光炽烈,恍若白昼。我站在一间不远处的书店打发时间。乔布斯的传记排山倒海地包围了我。我注意到,拐角处的一本传记旁边,还放着另一本书:艺术家岳敏君的画册——封面那张荒诞不经的笑脸,看起来戏谑、解构,如同一个空空如也的玩笑。相较之下,另一张面孔神色肃静、深刻,闪烁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崇高。这两张面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在我看来,它们象征了我们身处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变迁。
我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但即使在创作《故事星球》这部我比较熟悉的题材的小说之前,我还是会感到困惑。这种困惑,正是来自那两张面孔的目光的凝视。我们的民族也许不笑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迎来了一个空前大笑的时代,这是我能理解的。但同时我也发现,我们低估了去描写伟大的、崇高的、深邃的、真挚的、美善的情感和生活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带有偏见的。而一个真实的优秀的创业者形象,我认为,是应该容纳这些品质的。他是一个创造者,对外部世界的建设而言,他是在“造物”,对内部世界的处理上,是在“造心”。
从艺术史的维度看,岳敏君“玩世现实主义”的笑脸倾泻的是时代的空虚,而在文学史上,“玩世”也是中国古代作家和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一种处世姿态。但如果我们只允许“玩”,不允许“不玩”;只允许“笑”,不允许“不笑”;只允许“微小”,不允许“伟大”,或者带有一种不平等的眼光,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专制呢?而小说家的天职之一,我想,应该就是对抗专制。唐·德里罗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有过类似但更为宽泛的表述:“我们需要对抗性的作家,需要用写作对抗权力,需要用理想主义对抗同化机制的小说家。”
所以,我决定按照我的方法来写《故事星球》。在我的个人创作中,这是一次由“个人的情感”向“辽阔的体验”的出行,是一次由与周遭的俗世生活温驯相处的记录者向到世界上去的探索者的转变,也是一次让无力者重新找回力量、悲观者再次上路前行的尝试。在为小说命名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备选的标题,叫《仆街的阿信》。之所以想过用这个标题,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相对于学习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人,更应该把如何与失败相处当成第一门的必修课。我们文化中的主流思潮都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成功的人,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最后都是失败的。因此,在狂欢般地朝成功奔跑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如何先学会做一个有着基本的尊严感和幸福感的普通人?
创业题材让我着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天然地暗含一个长久以来我渴望去探索的主题:我们究竟能够去过什么样的生活。这种主题的内核是自由意志(我想,它带有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的色调),具有某种思想启蒙的光芒。对创业者来说,他无法从现成的生活模板中顺手牵羊;在创业这条漫漫长路上,也没有谁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把握世界的边界。所以,合格的创业者大多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机警地保持着自由思考的能力和开放的意识,远离“意义的浅滩”,让不同的思想形态和人生境界能够兼容共存、彼此参考,以便找到柏拉图所谓属于“另一半的自己”的生活。我以为,这种兼容共存,就是自由的精髓之一。“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是捷克作家哈维尔写下的句子。追随心中的自由,锲而不舍地去做某件“对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伟大的生活。即使最终失败,这也是一位“伟大的失败者”。
当然,创业固然有属于自己的“规则生态系统”,但仅仅用惯性的规则标准去比照是不恰当的。我愿意去塑造的创业者形象,并不是一群情绪化的反抗动物,因为我知道,在真实的创业中,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希望他们是平凡的、天真的、诚恳的,也是有力的、深刻的、智识的。
莫里斯·布朗肖说:“写作就是发现异己,把思想中的那个不认识的自己发掘出来。”对我而言,这样一种微弱的光亮,却像汪洋大海的罗盘和世界的慧心般,照亮着我的写作旅程。而对于对小说有着更高期待的读者来说,阅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评论
现时代的青年精神
聂梦
1
小说,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如果没有现代世界的兴起,没有探险、发明、工业化、征服和暴力,我们就不会结识堂吉诃德,如果人类未能飞行、画面无法活动、声音不曾在空气中遥遥传递,作家们就不必因时代的节奏而调整步调,文学史册中就只须辑录下狄更斯和艾略特——那些属于马车代步时代的人和事,而错失K先生或吃着著名小玛德莱娜蛋糕的马赛尔。必须承认,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中,每位文学“新人”的呼吸,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无论举起长剑刺向风车,还是由一口蛋糕展开大段回忆,他们的举手投足,终究要收纳到时代巨大的身影里。而今,属于中国的时代正上演着巨变。奔走于其中的人们所携带的面貌、分量、色彩、范围与日俱新,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学,也在不断地自我展开,日渐丰盛、开阔。有论者称,20世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世纪,中国的小说家自那时起便开始学习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体验和表达。然而,就在今天,置身于声势如此浩大的时代声息中,我们却迟迟未能收到来自文学“新人”的消息。换句话说,在当下文学已然贡献出的青年形象里,“新人”常常缺席。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长久以来,或者说近二十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摹写,始终为一种成见所支配——我们对于多义、复杂乃至混沌,从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而在单纯、热望和一往直前面前,却留下了大片的沉默。这种选择性的无视或退避,与小说家们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焦虑有关,与将个体从宏大叙事打捞出来的冲动和责任感有关……它最终将自己卷入了一个悖论里:它所衍生出的对失败的偏好,本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面相,最后却众口铄金地达成了单调。于是,具体到青年身上,各种“无力青年”“无为青年”甚至“失败青年”的形象如约而至。小说家们对于青年群体的外部考察与观照,缺乏细致辨认的耐心,缺乏切实的理解和同情,一不小心就滑落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框框里。而青年的自我审视,又往往过于耐心,过于自我理解和同情了,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现实精神、成长动力和行动的勇气,有些甚至直接演变为碎片青春的自我哀怜。如此往复,人们对于时下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的认知,不得不简化为一系列形容词:无序的,迷惘的,怀疑的,不知方向的,不明所终的。
迷惘和怀疑不是不能谈。它们本身也是时代的面孔之一,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眼下的疑问是,我们的青年除了愁苦嗫嚅、自怨自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表情和声音?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几无事实。所以眼下的情况是,在小说里,在最应当展示人类无穷可能性的文学里,一百张生动的年轻面容正在合唱着同一段旋律。想法、风格迥异的小说家们为了重建主体性而付出的苦心孤诣的创造,非但没有让笔下人物的表情清晰独特起来,反而越变越模糊,直至退融到色调单一的背景板里。
我们早已过了用一个人物命名一个群体、用几个人物俘获所有想象的时代。倘若在文学中,为了破解旧的俗套而形成新的俗套,并任凭这新俗套一直延续下去,那么恐怕就真的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它引发的不仅仅是文学形象的同质化,更会将小说家们的写作带入一种无所建树的精神的虚无里。一种无目的、无将来、为否定而否定的虚无。这首先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但它也提醒我们,或许我们的青年,或者我们的时代,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2
还是有人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的行动——这是我阅读彭扬的《故事星球》时最大的感受。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我们都容易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谈论梦想是危险的,在小说中谈论梦想尤其危险——骨感的现实常常会将丰满的理想刺穿,而小说家也有可能因此而失去阅读者的信任。《故事星球》就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一个关于如何兜售故事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彭扬写阿信,就是在写自己。在我看来,彭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整个时代都如此激动人心了,我们又岂能疲乏无力?因此,他甘愿冒着风险,做一个无限大、又大得刚好可以实现的梦,然后再用文字安排一切,一步步化解风险,最终让风险成为好故事力量的一部分。
《故事星球》的外壳有种“酷酷的萌”。主人公阿信在千帆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天真而不幼稚,这既是彭扬追求的调子,同时又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骨架,让阿信和小伙伴们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但我所关心的,是故事中传递出的节奏,是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奔跑与急停所带来的速度感。小说中一共写到六次仆街,阿信和他的团队仆街很快,爬起来也很快。就是这样一种“奔跑——急停——再奔跑”的速度感,把我们的心也搅动得不安分起来。真正寓于跑停之间的,是一种现时代青年的心理节奏。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飞速奔驰的年轻人,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绊倒,但他并不肯在泥淖中过久停留。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跌倒,有同义重复,也有递进成长。阿信的奔跑,不单单是消耗热量的机械运动,还是一种心境,一种创造,一种时代的具象和表征。阿信奔跑的背影,甚至让我想起了阿甘。
从阿信身上,我们辨认出了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新人”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姿态。这姿态同时也属于彭扬,属于更多的青年作家,这姿态中,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路向——现实里属于文学的不仅仅是“多余人”的摔打,还一定有“新人”的奋斗史和自主成长经验,以及那些“不可破碎的形态,不可轻慢的抵达,不可丢弃的心灵”(《人民文学》卷首语)。
但问题仍在继续。支持阿信一再奔跑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单单是属于青年人的焦虑吗?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新质的形象,他来自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自父亲空难去世后,“官二代”张展便在一条叛逆不羁、呼朋唤友、自我放逐的路上人间蒸发了。待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时,形象已然变得低调谦和、富有爱心、才华横溢。作者大海捞针,最终找回了完整的张展,而阅读者则收获了一些富有意味的对照项:叛逆对应权力和物质的异化,谦和对应对过去和真相的体察、对父辈苦衷的理解、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愿景。张展和阿信也许并不相像,姿态也不一致。张展想要的是自我辨认和自我寻找,阿信的任务则是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张展是回溯的,阿信却一往无前。但就是这样两股完全异向的力量,却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和续接。在这呼应和续接之下,他们分享着同一种精神。
我以为,这就是青年的精神。
3
事实上,精神和梦想的属性一致,都是危险物,让谈论它们的人故步自封、自设陷阱。但既然已经从阿信聊到了张展,这陷阱却是不得不跳了。并且在我看来,如果不触及精神问题,就永远无法抵达两位人物的内核所在,只能在创业怪咖和官二代的层面上不断绕圈圈。
在阿信和张展身上,选择始终都是他们的人生关键词。略萨曾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将选择分为自由选择和自我选择(自主选择)。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它们两者的待遇又各不相同。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一个青年被认真爱护,甚至过分爱护的时代。选择的自由被严密保护着,选择的自主则有赖于年轻人自己去解决。时代微笑着提示青年:要么干脆做一个挂着青年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要么让更多的反思和自觉融进你的选择。
顺着张展的目光向回看,阐述现时代青年的自我选择、青年的自主精神,首先出现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有所“疑”,有所“不为”。这条原则几乎可以溯源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青年传统,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青年人应有的常态。但问题是,实现了“疑”和“不为”,接下来的“信”和“为”,方向又在哪里?阿信的发问“未来怎么不能现在就来”,与第二关的方向性疑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一同指向了青年往何处去的内在困局。阿信肯定是听过鲁迅先生的教导的,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但阿信的时代,已经是呐喊和不破不立的需求及其必要性正在减弱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年轻人提出了新的考验:路在脚下了,大胆说话的人也多了,你们自己决定该怎样勇敢地进行吧。
“选择一条让自己尊敬自己的路”,这是阿信给出的回答,在他和张展翻越了无数高峰低谷之后,在经历了反抗、抱怨、宣泄而对历史、传统和现实有所理解有所认可有所责任之后。事实上,这样的表述我们早已在年轻的马克思那里听到过。热情有可能须臾而生,又须臾而逝,我们受到的鼓舞究竟是不是一种迷误?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有尊严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尊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出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的勇气,向着自身最大的潜能处探寻。
的确,这是一个对青年友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可以定义自身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生活”(阿信语),只有这样,未来才能现在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