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相反,以心灵的奇迹召唤现实的奇迹 ——读李浩诗集《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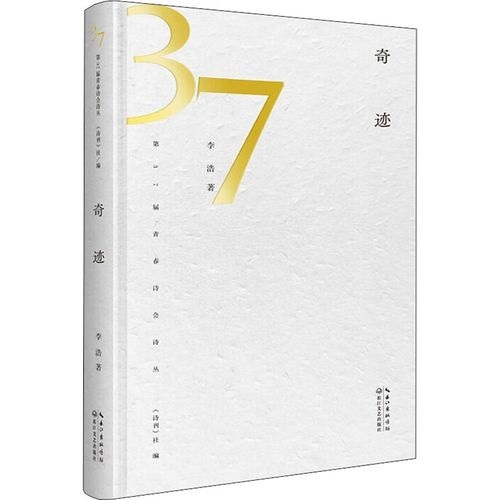
在我漫长而庞杂的诗歌阅读经验里,李浩的诗,绝对无疑是非主流的,另类的,特立独行的。其诗——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读之可能令读者深为困惑,备感焦虑。
这些诗作,就完整的单句来考察,大抵能依稀感受其意绪,倘若就其中数句(某节)或整首来看,又感觉颇难把握总体的诗歌意旨,就像满天繁星,你大体看得清其中几颗最灿烂的星辰,说得出星座名目,但放眼遥看去,却只是朦胧、暧昧、苍茫而抽象的浩瀚大美;这些星空一样让人迷惑的诗作,读来真的是令人惊奇而莫名其妙,若有所得——妙处却难与君说。其中有些诗作,你读罢可能一头雾水,完全不明其意,但你不会拒绝阅读随时激起的“惊奇”。
某种意义上,李浩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唯美的诗歌文本,在文本中固然也呈现/埋藏了一些抵达诗境的基本线索和方向,至于怎样解读其诗之蕴藉,如何品味和欣赏李浩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及诗学精神塑造,完全取决于读者自身的敏感和领悟力。
我在阅读李浩的诗歌时,总会想起耿占春关于所谓“奇迹”的断言:“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份期盼,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他们总在等待与今天黯淡的日子不同的奇迹。一些小小的奇迹。但如果期待本身很小的话,就足以带来那种微笑和那样的忧虑。”(《没有奇迹的世界》)
在诗歌书写题材、诗歌表情、审美追求和主题意象(甚至编辑导向)各方面高度同质化,对少数优秀诗人的写作技艺/表现手法模仿成风和风格庶几乱真的当代诗坛,李浩的诗歌具有孤绝的异质格调和清晰的文本辨识度。但阅读其诗是艰难的,想真正读懂其诗并非易事。换句话说,李浩现代性极强的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老妪能解”的大路诗,而是挑选读者的;其诗断然拒绝浅读、快读,必须专注细读、慢读。
某种程度上,李浩的诗属于典型的“小众经典”,不以所谓“名句”惊艳、取悦读者,好像不追求流行也不太适合在诗会上被大众朗诵。之所以作如此判断,并不是说其诗刻意炫技,执意雕琢深奥而逞晦涩之障眼术,更不是故作神秘故弄玄虚。
在我看来,这些意旨丰富的诗,是诗人冥想与苦吟的心血结晶,考察其诗尾着意标注的成诗时间、地点(有些诗作写稿发端和成稿地点涉及数处,定稿跨度长达数年),可以想象,诗人在写作诗歌时总是习惯于反复斟酌和认真修改的工匠精神和艺术痴心。因此,读者在面对李浩的诗歌时,总是能感受到一种冷静、端庄而雅正的诗歌氛围:这是需要倾情对待、用心灵去感悟的严肃的诗,关切心灵的诗。
研读《奇迹》(第37届青春诗会诗丛,诗刊社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这册短诗集,我们能略窥李浩诗歌的艺术魅力,通过品鉴诗作,亦可感知其宏大深沉的诗学抱负。
《奇迹》计收105首诗,除了三首篇幅超过两页,其余均为单页短制。但这些短诗之主题,大都能指、意指丰繁,其意蕴深厚可观。而因其诗创作——从命题、立意到修辞、终结——所指的繁富和能指的多变,意象的多元、考究和句式的峭拔、率性,遂使每一首诗读来都具有多维的、复杂但却深远而实在的体验。非深读不能得其妙旨,非强大的神经感应无从想象其诗疆域之辽阔。
要而言之,李浩的诗,总体上分明是入世之诗,却洋溢着出世的气息(《绝对之我》);其诗即使是书写瞬间感受和眼前景象激发的经验,却不止于肤浅的感受,不拘于表层的经验,最终指向高远的天空和辽阔深厚的大地,引领读者思接千载,神游八荒。
此处先表诗题之奇异美。李浩的诗题,大多极惹眼,颇具吸引力,比如《奥德修斯之旅》《少女葬礼》《我源自深渊》《昴星团时刻》《二十一世纪的白天》《今晚我是所有的人》《我沉浸在金子的目光里》《从圣–琼·佩斯故居到曹雪芹的家》《这一天你众多》《精神病院》《杜甫》诸诗题,无论具体的、抽象的,还是以人名、时间拟题的,都格外大气、响亮,领异标新,既有诗眼之婉转灵动,又有隐喻之妙趣横生。
令读者惊喜的,不仅仅是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诗题。在这些好诗题的下面,是更为精彩的诗意狂欢——敏感的读者会发现,在李浩这里,诗题,有时只是一个关于“诗意远方”“理想圣地”的方向性的指路碑;有时却只是一个由头,一种起兴,一顶神奇的“魔法帽子”,从它里面会飞出什么精灵、怪物,你无法想象,但呈现出来的奇迹,最终都令人惊叹。《词语》一诗关于“词语”之于诗歌意义的揭示,从实在的感人画面和诱人景观,将读者或世界倏忽引向幽暗无涯的深渊,可与博尔赫斯的《字》之隐喻旨在相近矣。
再略说诗歌句式之灵动美。李浩的诗,就诗句而言,总体呈均衡、稳重之势,长句、短句参差相间,具有很美的形式感。其诗语速疾徐有度,韵律灵活,语调坚定而不乏抒情性。其诗句与句之间,在表意层面上诗思之跳脱,跨度之大,之剧烈,之快速,之变幻莫测,着实令人拍案称奇;而其内在逻辑之缜密,之严谨,之精细,之合乎情理,端然令人叹为观止。其诗起句,大都孤峰突起,气象非凡,气势磅礴,而结句(结尾)多为开放式,意境宏大,指向辽阔,余音绕梁,余味无穷。
说到句式之好,在此短文中无法具体枚举——几乎每首诗都有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即使是给友人的交际诗,句式亦灵活可观,别具情怀,不落俗套。
最后说诗意之丰沛美。尽管博尔赫斯极度推崇说过,有些诗歌没什么含义却很美。且扬言——而为了写出一首美丽的好诗,诗应该没有什么含义。但博氏传世的好诗中,哪一首没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繁茂含义呢?相反,没有含义的所谓“好诗”是不存在的。一首诗免不了“兴观群怨”的具体实用功能,何况还有诗人别具情怀和抱负的诗之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以《奇迹》论,这部诗集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斯之旅》开篇,诗集中涉及葬礼、悼亡、灵魂、复活诸主题,还有大雪、风暴、私人日记、书信和情歌,以及精神困境等常见母题;诗集止于《静物诗:七日唐璜》。
读者读完诗集会发现,用作诗集之名的“奇迹”——其中固然有诗句里出现过这一关键词,但却没有一首诗特别以此题名;而“奇迹”确实如星辰似繁花般散落于这些诗歌里,每一首诗都在寻找、探索、召唤、导向、抵达和捕捉、描摹、刻画、反映、呈现奇迹。
李浩的诗里有多种诗意维度,诗思呈枝状发散,有多种具体读法,不同的读者都有可能获得相应的阅读快感,获得与之心智和悟性相匹配的启迪和教益。我们在阅读这些貌似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诗作时,最后总能感受到某种温情脉脉的亲切回应,获得相应的心理慰藉或捕捉到希望的光芒。
也即是说,李浩颇多及物的诗虽然直视人生/生活乃至人性的苦难,深刻触及了深入骨髓的生命痛苦,深切体验了人性的荒芜悲哀,温柔抚摸了灵魂那敏感又疼痛的伤口,但他最终并不会将读者有意引向消极、仇恨和绝望的深渊。相反,他能平和地抑制激情,克制悲伤,自解自叹,自怜自救,安然净化心灵和诗境,最终直指或体现出堪称崇高但不局限于人文道德层面(包括宗教意味)的理性追求。
比如《私人日记》,该诗以密集的意象和离奇古怪的骇人景象,深刻而含蓄地讲述了一个家庭三代人(也可以引申理解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族群)的命运遭遇。诗歌开头意境壮阔,气氛肃穆而令人震撼,诗人凭借暴力而精准的娴熟技艺以全视角直接切入,“天空和土地,插进黑夜无比/辽阔。风吹过村庄”,接下来以蒙太奇技术推拉聚焦——镜头对准的是大雪后的荒凉景象和隐藏洞穴的几种小动物。
随后,思绪如悲风陡起,席卷悲情喋血的既往史实:“它如同一颗绿色的/子弹,停在深邃的高空里,正在哀嚎的鹤身上”——在此贸然援引诗句试图说明问题,是野蛮而不明智的做法,因为李浩独特而绵延不绝的诗句很难简单割裂,它们不是炫才的、简单的、取巧讨好媚俗的口水“金句”,也不是故作高深刻意提炼的苍白警句,但不援引却又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站在湿淋淋的
杉树林里,贫瘠的乡村在我的
血管里结冰。我吐出肺叶上,晶莹的
冰粒,那些从我身边经过的人
‘他们的未来
还没有确立,他们的敌人
还没有出世’。他们的脑子,
如同墙上,骷髅里的蝎子。我的父亲
嘟嘟囔囔:他们的毒牙,都长在肚子里。他们舔过
我曾祖父的血,啃过我爷爷的
骨头,修理过我父亲,关押过
我母亲。他们的裤裆里灌入的淤泥,在生之链上,
春夏秋冬,同生共死,
无一获救。当少年在伤口里,对自己隐藏很多不敢
面对的毒蛇时,那只在院子里偷喝了
农药的兔子,跑出父母家,
就再也没回来。从此以后,我一想起她,
星星就开始流眼泪,我的痛苦就漫过
我的生命……
从上引述的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某种重大的事件,非必要清楚呈现但却能感受到那事件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而且能够体会到叙述者深藏内心的巨大悲愤。但我想提醒读者,完全不必要将诗人说出的此一事件当真,作为隐喻,事实上我们当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可能曾经历过类似的不幸,尽管事件和受伤害的程度不同。
然而,就是这样足以令人铤而走险的一个黑暗主题,最后却遽然止于:
有时,我总是想把耳朵里,那些神乎不定的
金属的细碎声串连起来……但我不能,
我在火中逐渐接受“爱是我们最高的喜悦”,
也是“最深的愁苦”。我尝试过宽恕,掌握另一份
工作和生活:“欢乐是为了人类”
就是这样一首短诗,其蕴涵的题旨完全可以演绎成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宏大的、迷人的、类似于《白鹿原》那样的家族史(小说)。某种程度上,李浩诸多时空交错且意义密集的精美抒情短诗,可谓“浓缩的诗小说”——它们均可加工改写为蕴藉风流的短篇小说。难怪李洱会说:“优秀的小说家,都离不开诗歌的滋养。就我所知,李浩的诗歌已在很多小说家朋友当中传诵。”
作为浪漫的现实主义者和怀抱尘世幸福生活信仰的诗人,李浩有着看似神秘实则清晰而又明确的写作动机,或谓重塑神祇(缪斯)、使语言和生命意义持续生成的诗学抱负:“我想动笔,让神影响我心里的淤泥”(《盛夏》)。“我在这个如此孤独的/星球上,抗拒食人”(《峰顶》);“生活给了我太多恩赐,/我的世界,存活于启示之中”。
李浩在《写给近海的西西废》中说:“到处都是生活。孩子们的脸都很新鲜。”耿占春认为,“使自己的生活琐事具有意义是一种漫长的修行”——据此而言,坚硬的生活现场是李浩修行的道场,喧嚣薄情的世界是他悟道之庙宇;在崇高的诗学精神维度上,他是一个虔诚的观察者和聆听者,是不倦亦不懈的奇迹求索者,是满怀激情与活力的思想者。
“我深居心底,/全身吵闹的剧痛呵,/足以品味猛虎的狂喜”(《颂歌》)。在他眼里,不可言说的灵魂是风中天空里的孤云(《灵魂》),时间是浩瀚的荒漠(《花冠》),也是星空里会飞的钥匙(《农历日》),有限生活里总有永恒的瞬间闪现,“世界与某天,任何一个/地点,好像一本书打开”(《雪屋》)。
尽管多年来“一直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时间的入口提炼痛苦”(《赞美我们途中的谜》),但李浩对阴郁沉闷的命运和未来仍怀抱美好希望,“在这天命的形式里,你将走完夜的行程”(《一再地》);这只穿梭在荆棘丛中的山雀(荆棘鸟),虽然“一直没有寻找到生活中的乐园和歌者,/就挫败了内心。但我没有放弃。/我知道我要追寻的是什么,我不惧怕,/因为在绝望的路上,你是给予”(《波斯风》)。
“你是给予”“谦卑寻找,必得寻见”(《第二十四个生日》)——这也是我们阅读李浩的诗最大的感受和收获:他是一位执著虔信,甚至可以说是自身心怀奇迹的诗人,他以其光芒闪烁,精致唯美的诗歌追逐/创造生命的奇迹,或相反,以心灵的奇迹召唤现实的奇迹,“沿途的清晨走向须弥。生命与生命的根茎,/在沙漠之中:接受筛选,接受恩宠”(《静物诗:七日唐璜》)。
- 育邦:处处惹尘埃,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2023-02-16]
- 韩东:我从来不想神化日常或者尘世[2023-02-13]
- 马占祥:思想、语言和精神气象是诗歌写作三要素[2023-02-08]
- 小饭VS.王小龙:只要还在写诗,就会很敏感[2023-02-06]
- 渴望诗意生活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诗歌[2023-01-31]
- 丁东亚、谷禾:诗歌要保持对语言和世界的诚实[2023-01-31]
- 渴望诗意生活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诗歌[2023-01-30]
- 年轻人正成为写诗读诗绝对主力[2023-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