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音 弋舟:让故事成为事件,让事件成为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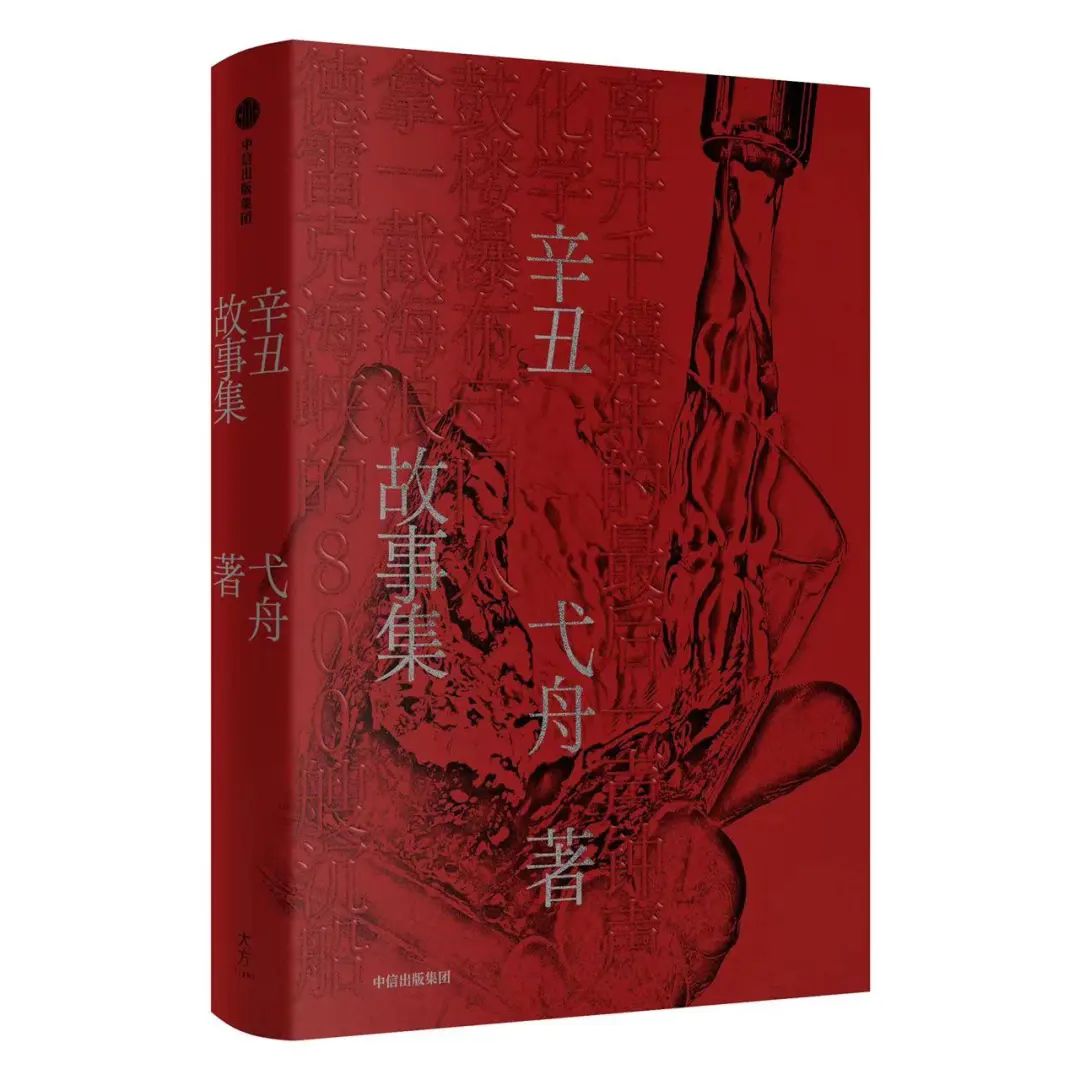
《辛丑故事集》,弋舟 著
中信出版集团(即将出版)
编 者 按
弋舟的《辛丑故事集》(“人间纪年”系列的第四本,前三本为《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即将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依照惯例,每部小说集请一位批评家进行对谈作为后记。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李音和弋舟就《辛丑故事集》的对谈。二人从《辛丑故事集》代序中提到的画作《女人,小鸟,星星》谈起,由艺术联系文学,就区分“故事”与“事件”、“现代”与“当代”问题分享各自的见解。在哲学意义上,与具有稳定意义的故事不同,“事件”指意外,带有“奇迹”性质,是某种逃逸、偶然之物。李音认为弋舟的一系列短篇写作,与其叫“故事集”,不如称之为“事件集”。弋舟强调事件有赖于我们积极主动地发现,有了“发现”,我们才可以将所有的瞬间任意截取,使之升级为“事件”。不过所有这些讨论,借助于当代艺术的变迁参照和一些哲学概念,试图谈论的核心问题是,当下小说创作如何表达当代感、如何在形式上当代化,以及评论如何摆脱更适用于阐释现代文学的思想和工具,找到把握和阐释当代世界的问题和方法,对一些具有当代新特质的小说有审美准备和判断力。比如对谈中反复提到的,弋舟的小说中植入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非文学的、其他学科门类的术语),这使其小说在技术和艺术特质上具有类似于当代艺术的“装置性”。这些异质性概念的植入,能够将不新鲜的“故事”变成“事件”。这些概念可以在意象意义上理解,但又不仅仅是意象,它们并不对人和事构成一种强力阐释意义,只是一个参照装置,指向文学“事件”的偶然性和开放性。
弋舟
李音好。显然,我们这个对话稍微滞后了一点。这本集子定名为《辛丑故事集》,说明有个时间上的规定——它需要在辛丑年完成。好在滞后得不算那么过分,而且,这“不过分的滞后”还些许缓释了来自时间的压迫,令人如同冒犯了铁律,反倒透了口气。
李音
延迟的对话,也许反倒成就了一个“事件”。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事件是意外,带有“奇迹”性质,是某种逃逸、偶然之物。也许更需要被重视的恰是偶然和意外之物,不是吗?在我看来,你的写作就一直具有这种特征啊。
在这本集子的序言里,你谈到了米罗的画——《女人,小鸟,星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画框规定了这幅画,由此艺术作品才得以诞生,交流也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壬寅年谈论辛丑事,异曲同工,同样是在时间的画框外去看一件以时间命名的作品。一切都恰逢其时,而“事件”,正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如你所说,《最后的晚餐》里耶稣与门徒的故事,代表着曾经被给定了的、稳固的世界,以及将隐喻都彰显出明喻的人间,如今一切坍塌、破碎,现代绘画似乎只能在被画框聚拢的空间里表达与呈现,其内容是拒绝阐释的,乃至是弥散的,只是因了“有框”,才被赐予了一些可供我们讨论的余地。这是非常精彩的洞见,我很同意。不过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些概念,我们习惯性的、大概齐使用着的词语,需要略微讨论和厘清一点,否则有些问题会谈不清楚。比如,我们(不止你我)喜欢混用“现代”和“当代”,你虽然明确了什么是“事件”,但多少还是不愿意和“故事”做个区别。在每年都出一本的“故事集”里,这一次你却在序言中讨论着“事件”和短篇小说艺术的问题,我想先听听你对“故事”的理解。
弋舟
文艺到了今天,的确是越来越依赖“规定性”了,正是有了“框定”,其品质才得以被指认和理解。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继而做些什么呢?一如这本集子的发生,全然是一个规定性的产物,我要求和被要求着创作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且在时间上也被强加了限制,这些,都是框住了女人、小鸟、星星的边框。为此,看上去当然丧失了某种“自由”,但如实说,我却也藉此实现了某种创造的契机,那些涣散而抽象的情感或者情绪,被约束着显形,并且,被定名为了小说艺术,不如此,它们势必只能混淆在几无差别的、浑浊的经验里。
这篇用来做了代序的文章,原本是《小说界》的约稿,其性质,如同作业,既然是作业,当然就同样是一个规定性的动作。你瞧,如今的我们就是这样被“驱使”着的——但你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驱动”,由之,积极性的一面或许便也随机展开了,而在我的理解中,“事件”不应当是一桩纯然消极与被动的事,它有赖于我们略为积极主动地“发现”。有了“发现”,我们才有可能将任意的瞬间随手截取,使之升级为了“事件”。
关于“现代”与“当代”的确凿分野,老实讲,我也是大而化之着的。无论“现代”还是“当代”,在我,它仅仅是用来区别于“破碎”之前的那个世界。在那个完整的、行将破碎的、正在破碎的世界里,“故事”一定不是“任意的瞬间”,它始终是某些“特定的瞬间”,一如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与门徒们所经历的那个时刻;当一切破碎,“故事”也随之弥散,我们于是被迫在所有的瞬间里去“发现事件”,而“事件”本身,全然是虚妄的,是构成河流的水,乃至是水的分子式,它只有在被“发现”中才得以成立。在这个意义上,将这本集子叫做《辛丑事件集》,可能倒也合适。
李音
你说的我全部理解,还可以夸张一点地讲——深感共鸣。我不是一个严谨的人,更不是概念控,只是今天要谈的问题,可能有必要强调和借助一些概念。在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历史分野是古典和现代,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的文学通用定义上,我们处在“现代文学”的时期,所谓的当代文学,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和性质。但是法国学者让·贝西埃提出,现在有必要为当前的文学新趋势提出新的命名——“当代小说”,以区分现代主义的和被描述为具有后现代特征之类的文学,他认为“当代小说”的创作趋势,主题和理念,思想和范式,其全球文化背景和问题性等特征,有必要被视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变化,需要进行分析和凸显。不论是观察近几年的中国小说,还是国外的状况以及一些现象级的文学新事物,我们显然对他所描述的趋势是有所感知的,但是这个“当代小说”的概念好像还没有被广泛地接纳使用。
在此,我只是想反向强调“现代文学”的当下普遍延续适用性,尽管,我们早已在口头上认可了自己生活在当代的这个事实。在艺术界,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是被非常明确区分了的。1917年,杜尚的小便池作品《泉》是一个标志性、肇事性的事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仅止于传统美术遭遇了来自印象派的危机,而且抽象艺术以及各种前卫艺术、工业制品等对艺术领域的入侵或瓦解,都在逐步消解19世纪的艺术制度和审美规范。当下我们去看艺术展,最惹眼的肯定是各种装置艺术与行为艺术。当代艺术和传统审美是割裂的,这也是大众和当代艺术有着较大接受距离的原因。话说回来,经典艺术也和大众审美关系不大,因为个人的趣味左右不了经典的地位,想想还是蛮悖论的,但大家就是觉得“看不惯”、“看不懂”当代艺术,甚至觉得当代艺术看起来都是一些莫名奇妙的东西,总之和“美”是没有关系的。这只是因为对于当代艺术,你无法用现代艺术的逻辑、范式、审美去有效地感受和阐释了。
问题来了,一方面,我们总觉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没有新突破,似乎有些作品也不差,然而整体来看,文学界便显得了无生趣,乃至需要呼吁“革命”;另一方面,我想问大家,是否都对新的小说有审美准备或预期?如果说有一种当代小说,一种有新技术、新质素的小说出现了,我们是否会像对待当代艺术那样,发生审美的失效和错位?在我看来,“故事”和“事件”的区别就非常近似这个问题。
弋舟
“大家是否都对新的小说有审美准备或预期?”,这几乎是一个根本性的诘问了。那么,有了吗?大约是没有。而且,我也不大能够相信这种准备和预期会时刻为我们预备好,那来自于学院严格地训练,同时也严重地依赖天赋。
但是我想,有时候,我们是否也夸大了新与旧、古典与当代的差别,如果这种夸大的确存在,我们不妨纠正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古往今来,所有合格的创造者都在经历着对于往昔的反动?于此,我们往往会放大昨日的威力,将其视为某种“代”的庞然大物,由之,视自己的反动为有力。可能我们不过只是动了早上那位创造者的奶酪,却不由自主地想象为推翻了一切人类盛宴的桌子。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几近妄想的假设中,人类既往的经验被愈推愈远,终于弄到了让·贝西埃所描述的那番境遇,不得不在“现代”之中找出一个“当代”的边界。对此,我真是有些为后人发愁,古代,现代,当代,都被我们征用了,他们将如何描述自己的境遇?当“故事”变得无效,我们找到了“事件”,假以时日,“事件”也不足消愁,是否意味着一切古老艺术的消亡?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好在我们的时代还有着相对稳定的“画框”,虽然这个“框子”本身的意义都渐渐大过了它所框定的内容,却至少还给我们提供着纠结不已的可能。我可以用《辛丑故事集》这个框子框住几个在我而言别具意义的瞬间,也因了这个框子,传递给我的读者们几个别具意义的瞬间。如果,当他们在这些瞬间与我达成了意义的共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去想象了:某种对新的小说的审美准备和预期开始悄然发生了。当然,这种想象必定只是所有妄想之一种,参与的趋势,不过也是人类轰轰烈烈地迈向更为破碎的破碎。
李音
强调边界或断裂,只是为了廓清和凸显我们要讨论的事物的权宜之举。“断裂”都是人的回溯性发明,时间之流哪有中断之处?历史也没有截然分明的进程。针对我那个随意而鲁莽的想法“大家是否都对新的小说有审美准备或预期?”做一点点补充。经典艺术有一个名称叫做“造型艺术”,显然,这个称呼已经有点削弱其神圣化的意味和效果了,这也暗示着适合于理解现代艺术的经典艺术理论和批评,面对当代艺术,阐释未必一定不恰当(对阐释还是要留有开放性的态度),但一定会变成拙劣的不趁手的工具。
我关注的是与事物相匹配的思想工具。你反复说的“框”,可以理解为一种“艺术场域”,场域和艺术(事件)互相生成。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另外一个分野就是艺术边界的突破,何为艺术及其标准开始成为悬而未决、持续不决的问题。所以,场域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普通的行为、日常之物,由艺术家来处理,放进艺术场所,被艺术家署名,性质就会改变。当然,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也不是随便胡闹的。你的小说就给我一种强烈的装置感。
当代艺术与传统造型艺术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其高度的理论化,依赖概念,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性、形象性,与各种社会理论、哲学思想交互颇多。与其说当代艺术倾向于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故事性),不如说很多艺术作品本身意图成为插入世界、介入社会的一个“事件”。不能说你的小说不讲故事了,但从小说技术和作品特质上,我认为它们更接近当代装置艺术作品。
弋舟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更接近当代装置艺术作品”,对于这个判断,我衷心拥护。让我略有迟疑的是——如你所言,它们也是“高度的理论化、依赖概念”的吗?如果是,那么我得警惕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我愿意发生在自己写作实践中的事实。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期待自己是一个“没有理论,忘记概念”的家伙。在下笔的每一刻,都寄希望于“偶然”,最终让理论与概念为框,在它们的一框之下,我所写下的东西才侥幸成为了“艺术”。最准确的描述是:我只凭直觉触摸整全,但依然活在破碎的现实里。
李音
我在以当代艺术现象互证文学现象,即便你的小说充满理论,我认为也大可不必立刻拒绝。好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概念含量的多少没有必然关系,但充满理论性也不一定必然就是坏事,想想福柯、罗兰·巴特、本雅明吧。你在小说“织体”中通常会植入一个概念,譬如“刘晓东三部曲”的第一部中,用了海洋学的“等深”,《化学》用了化学的“键理论”,这些概念和以往我们所说的意象、隐喻等有相同之处,但性质却是判然有别的。理论概念等于为事和人重新划定一个“框”,一种理解和认识的新框架,会让事物的性质瞬间发生变化。一件寻常之事,一个也许不构成蕴含深意的丰富的情节,因为这种异质性概念的植入,却变成了一个使人不得不去瞩目的“事件”。可能,如果没有这两个概念,《化学》与《等深》,一个会变成散文,一个会变成通俗故事。
这些概念,与你要保持的“直觉”(背后还是强调着“感觉”,再推及背后,就是一整套的文学观念),看上去构成蛮强烈的冲突,但这个冲突与异质化的效果是重要的。某些本来不属于感觉范畴的、不具有文学性的词语,植入故事中,却改变了文本的质地,同时也为术语自身赋予了某种文学性。
当代艺术对边界的扩展不仅依赖新的科技手段,也特别喜欢具有某种文化世界主义,就是进行各种学科思想的融合,风格,材料,形式,混搭交叉拼贴。如果将你的小说比附艺术,就是这种依赖某种概念的装置艺术——核心概念既构成了题眼与机巧,又构成了一种可被称之为事件的“框”。这与你是艺术家有关系吗?我看过一些你画作的照片,蛮喜欢的,同时也启发了我对你小说的想象。还是禁不住老生常谈啊,再为难你一次,但我们不去谈艺术的“通感”。
弋舟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概念”,约等于“意象”,你将其强化为“概念”,是富有力量感的。这个“概念”即是对于“意象”的升级,指向“一种理解和认识的新框架”,它甚至是直接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征用,而这种征用本身,正是基于准确表述我们“当下感”的需要。如果说,“意象”还颇有古典感,是对于既往经验的陈旧使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迫于当代处境,我们不得不展开的新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之中,人文也许会反哺强势的科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整理着世界,使其至少看上去有了一些再度被认知、易于我们去把握的可能。
我也不好再三摆脱自己“艺术家”的嫌疑,我想要说的是,当科学都被我们用来武装小说时,所有既定的身份,或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李音
《辛丑故事集》里,第一篇的“千禧年钟声”,第二篇的“化学键理论”,第三篇的“鼓楼”,第四篇的“宇宙瀑布”,第五篇的“海浪”,第六篇的“德雷克海峡”,都具有同样的“装置”效果。只不过方式有所变化。比较而言,“海浪”和“德雷克海峡”,我觉得在文本中的使用更具装置的典型性。
弋舟
最后这两篇是同一个时间段写的——西安疫情封城的时候。也许,特殊时期,作为写作者,这种“装置性”更能对应我彼时的情绪吧。当世界变得格外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新的表达方式会成为潜在的需求。
李音
《拿一截海浪》和《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具有不同的精巧结构,与集子里的其他小说不同,其设置的参照物——装置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文学性”的作品。
从隐喻的意义上讲,《拿一截海浪》可以理解为一个失败的男人、不称职的父亲,远离故乡闯荡海南,又从海南返回故乡,带了一件制成“一截海浪”的砗磲工艺品给女儿做结婚礼物,其颠沛流离、一事无成的沮丧和恐慌感,被路途中遭遇的群峦起伏、排列有序的山峰瞬间拯救。群山如同海面上涌动的波浪,命运看起来不能更糟糕了,但此刻,无意拆开的这个命运的盲盒,却让人收获到了顿悟与抚慰:“不过是从一片海去了另一片海,”“不过是从一片海回到了这一片海。”
《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含义显明,没有人真正在凶险神秘的德雷克海峡及其上空航行着,但我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比海难与空难少一分惊心动魄,运气全然无法把握。
这两篇小说在虚与实和轻与重之间搭配得非常特别。更具特色的是,“一截海浪”的“概念”以一件砗磲“艺术品”的实体出场,灵感来源则出自诗人蒋浩《悼亡友胡续冬》的一行诗:其实,我想拿一截海浪,因为住在岛上,周围全是浪,浪,浪 / 浪与浪之间全是互问与互否。你也在小说结尾处注明,“本篇的题目,出自诗人蒋浩的《我辈复凋零》”(出于对故人的尊重,特意取了蒋浩诗作的题记作为题目)。在工艺品和诗歌的双重符号上,这“一截海浪”均已经是一件艺术品,本身带有自己的意义和场域。德雷克海峡则可以理解为一件常见的当代媒介影像作品。有关神秘的德雷克海峡的灾难传闻,各种跨时空的,不限时效、不控渠道传播的数据和报道,其本身就独立构成一个事件,而且语义不清,充满着暧昧怪异的文学性。
这两个完整的“文学性”的装置对小说的嵌入,作为语言材料拼贴混搭以后,使小说要讲述的故事具有了多次意义回流和意象叠加的效果,不是互相阐释,而是好比物体被映射到一个混杂不清的感光底片上,且被多次地重复冲洗和曝光。人对命运不断地观望,回溯,拯救,观众是在这种叠加的影像中,多次分辨后,才看清命运的面庞。
蒋浩的诗歌是献给早夭的挚友胡续冬,非常感人。但“一截海浪”在这里本身就是把大自然“装置化”了。杜尚可以将日用品作为艺术品,这一次你搞大型山水装置。参悟山水,映照生命,本是中国人的长项,但你和古人有着不同的招数,在注重“当代化”这点上,你和蒋浩有着共同之处。
弋舟
“拿一截海浪”是对诗人蒋浩诗句的直接转用,如你所言,那首诗本身便感人至深,我很难说清,是整首诗的力量使得这一句熠熠发光,还是这一句本身便自带光芒。现在,我似乎更倾向于后者——这五个字组合出的汉语效果,本身便足以对我构成文学的驱动。
“德雷克海峡”的意象完全源自一则新闻。2019年12月,参加完中国作协主办的博鳌论坛,我在返程的飞机上读到了这则新闻。当时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感召般的触动,如今我已经很难回忆起具体的动机,唯一确凿的是,我用手机拍下了《环球时报》上的这则新闻,现在照片依然保存在相册里。时隔两年,昔日从海口飞回不久,疫情便在武汉爆发了,当我决定写这篇小说时,恰是西安封城的日子,我难以说这其中有着什么难测的天机,而事实则是,我又的确从中仿佛窥见了“命运”。小题大做吗?可能会有一些,但具体到一次写作,这藉由一则新闻连缀着的两年时光,于我而言,却真的堪称重大。我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线索,尽管不知最终会如何按图索骥,但当两年前我在飞机上摸出手机对着一张报纸拍照时,一定是怀着某种确信的——我相信,“所有的瞬间”都将成为“事件”。
现在回顾这两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也让我进一步厘清了自己的某种创作路径,那也许就是你所说的“装置对小说的嵌入、作为语言材料拼贴混搭……”
李音
由于艺术作品替代抽象概念的置入,这两部小说具有了双重的虚构性。日本学者小林康夫有一个深刻的洞见,他说,文学书写的语言“不单是将虚构的现实赋予现实中不能发生(没发生)的事件,它既是现实亦非现实,毋宁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的自身结构的语言。在此,二元对立的区别丧失了意义,而这便是文学文本。我们在说某个文本的文学性时,其实说的是关于文本组织生成的事件,即我们发现它具有独特的时间结构。”接下来,他的观点更是令人顿悟,“我们不妨说虚构的其实是能够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只不过还不具备其发生的场合。或者我们也许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事件的本质并非现实的,而是虚构的。不论是哪一种事件,如果是真实的,我们就将其本质视为文学性的。”在他看来,文学就是语言事件,文学就是事件生起的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就是我们存在的根源性形态。那么好了,人类注定需要文学这门技艺,只不过需要不断地去发明。
弋舟
小林康夫的观点真是给人提气,尤其在文学被普遍唱衰的时刻。我只是保守地认为“事件”有待于我们的“发现”,你则干脆给了文学一个更高的荣誉——发明。这是“再造”一个世界的勇气,是犹如创世一般的魄力。
李音
是的,也有很多人讲过文学的“发明性”,但小林康夫的表达最具“神性”,如同圣谕。小林康夫说人发明了文学这个技艺,我觉得要不断地发明,因为小说的思想和技艺需要不断地“当代化”。
这本集子中那些小小的“事件”,带有故事的模样,但却没有“故事”通常所有的因果、意图、预测(包括其背叛、翻转),而是瓦解一些观念以及生活的结构,使之具有突发性,发生之后,才可能回溯性地产生若干关联性的理解。按小林康夫的观点,这就是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没有所谓的预计的事件的场域,没有经过文学书写之前,便不存在。也许《辛丑故事集》真的应该叫《辛丑事件集》,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奇迹,尽管它们灵光乍现,转瞬即逝。
弋舟
如此一来,叫做《辛丑装置集》大约也勉强可行。无论“故事”还是“事件”,可能都是对于平滑时光人为地“崎岖化”,如果人真的具备了“发明”的能力,大约他是不需要额外从时光中遴选特殊材料的,每一个变动不居的瞬间,一经截取,都将成为奇迹。
李音
你看,小说家总爱强调文学艺术的“自然化”,但你的实际写作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不迷信“自然化”,效果上最自然化的作品,恰恰需要最讲究的技艺,遴选材料和截取瞬间都更加考量小说家的眼光(思想)。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并非常规截取,自然也不是常规故事,你书写的多少都是一些难以归类与划分的经验和事物,深具破碎感,人和事、事和事的关系链条虚弱,不具严密的可“叙事性”,说其很难常规分类、划分,也就意味事件本身难以清晰阐释、难以结构。这就特别需要妙思和巧工将其容纳在一起,构成一个场,一个事件。无论是借助于科学术语,还是像“一截海浪”和“德雷克海难”这样的文学艺术品,都是非常巧妙的机关,它们构成了事件的场域与隐形的框。它们是意象,又不仅仅是意象,主要作用不是用于互相阐释。这就是你的技艺,这种技艺对于书写溢出我们生活常规结构之外的经验和遭遇,是契合有效的。而且,它还不是颠覆、反转我们的常规故事、现有经验和观念,我甚至觉得它也不是另外容纳进某种零碎器物,而是临时搭起了一个场域般的景观,旋生即灭。
弋舟
旋生即灭,方生方死,当然是这样的,那个“自然化”需要有“发明”的眼光与技艺。但我怎么好意思自诩已经部分地拥有了这种眼光与技艺?我甚至会猜测,那些完全具备了这种“发明”特权的家伙,必定会痛苦不堪吧?喏,想象一下:他们要毫不停歇地面对每一瞬间都一览无余的、意义陡峭到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世界。
李音
所以天才总是少数,才华要承受相应的重荷。我之所以想到容器这个意象,是想到一个典故:希腊人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柏拉图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野蛮人并不是被正面界定的种群,这个概念无非是指那些不是希腊人的人,所以野蛮人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容纳那些非希腊人的容器;国际学术玩咖齐泽克说,以此类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类似的容器,无非指的是地球上那些不符合欧洲的生产方式。这些容器都是负面概念的,一旦被容纳进去,就够成了对变动不居、朝生暮死的偶然性的取消,将其形式化,结构化。各种负面容器造成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可大可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及其连锁效果,我们要费很大劲才能去蔽。在这个角度上,我特别看重文学“事件”,不是颠覆,不是解构,而是保持偶然性和开放性。起初,我感觉你的小说装置化是一个有意思的技艺,现在我更看重这种开放性阐释场域的价值。就是说,这些术语并没有对人和事构成一种强力的阐释枷锁,只是一个参照装置。我觉得这很当代。
《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鼓楼》《瀑布守门人》,对事物都没有评判,人物行为随起随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要书写出意义的努力,对溢出常规的行为,扯不清的情侣关系,荒唐的父母情感生活等等,均抱持着不具对抗性的理解,甚至与“理解”相比,小说更愿意让千禧年的钟声响起,让大型流星雨这种宇宙景观,让无处不在的鼓楼意象去映照事件。《瀑布守门人》比另外几篇小说还多了一些和解性与疗愈性。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说,“想象使无名之物具有形式 / 诗人的笔给了它们如实的貌态,/ 空虚的无物也有了居处和名字。”这些话适用、也不适用我刚刚的想法。当下这些破碎崎岖的经验,经过文学书写,也许会有一个保持变动性的映照或命名。
弋舟
将对象与他者“容器化”,隐含着的,是不公正、至少是不平等的姿态,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样的姿态我一定是要反对的。这无关道德立场,仅仅是有违我对小说这门当代艺术的理解——那么做,太轻易了,缺乏应有的难度。“很当代”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首先是一个对于“难度”的强调,这种对于“难度”的确认非常必要,唯有如此,才能平衡杜尚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这个看上去确乎轻易的“发明”。给小说一个开放性阐释场域的价值,这种内在的自觉,基本上我们是不会亮明的,但它必须“内在”,并且“自觉”。我们是不能够允许自己凭借着“有意思的技艺”,将自己的所为之事降格成仅仅像是一个噱头。
在这本集子中,《瀑布守门人》是显得比较特殊,它除了相对的“完整”,也更具“妥协性”。你知道,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正关在怀柔评奖,而保持一定的“完整”与“妥协性”,几可视作我身为评委时对自己的提醒与告诫,这个时候,我们得暂时忘记莎士比亚。
李音
技艺有时候是噱头,有时候意味着思想。《瀑布守门人》有“柔软”的爱,也有点中产味,很合适放在丽江啊。我其实也挺喜欢这一篇,最后出来的“宇宙瀑布”这个说法给小说注入了一些壮阔。毕竟现在人类确实正在向着宇宙挺进。
弋舟
这篇小说正是关于丽江的一个作业。三月份,《小说月报》组织了八位作家一起写“有丽江元素”的小说。八个人结伙去了丽江,回来后欠下八份作业。五月份在海口(这本集子似乎跟海口飙上劲儿了),田耳,黄德海,我,在一家卖烧鹅的小馆子里喝酒。一贯奇计迭出的黄德海倡议:三个人,分别以对方的旧作为名,各自写一篇新的小说。爬梳一下,就是:我写一篇田耳写过的,田耳写一篇黄德海写过的,黄德海呢,写一篇我写过的。没错,就是一个圈,或者一个闭环。三个人可能是被海南的热风吹晕了,可能是被火上浇油的酒搞傻了,竟均无异议。总之,我认领了田耳的《瀑布守门人》。这些全是随机性的,但写着写着,我认识到了,终究,当你在写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无可救药,你就是被规定了的。除了男人和女人,其实,我们在小说里可以结构的角色关系,并没有太多的余地。尤其是,当你已经写出一千五百字之后,你的余地就更加逼仄了。是的,我所能写下的,不过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一如人间的那些事儿,有“柔软”的爱,也有点中产味,等等。和每一次的写作一样,你只有不断使劲儿,在规定性中,看看能不能搞出些随机性。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海口的闷热黄昏,我晕头晕脑认领下的,是田耳创造出的这样一组词:瀑布守门人。不是吗,这组词本身就是对于规定性的一个漂亮的反动。为此,小说还没写完,我就就迫不及待地、慨然以题记的方式,在篇首写下了郑重的献词——本文致敬老田。
我想,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完全是有赖了这组词,我才重拾信心和耐心,又写了一遍世界的规定性强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伤害,又写了一遍那种伤害着我们的规定性,原来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我们的“自重”——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施压者。我们受制于自己强劲的欲望与爱莫能助的软弱,对此了如指掌,只能盼望夜观天象,在一场星空的高潮里,短暂的、心悦诚服地去做回一个平静的小孩。
李音
我记得你们在海口商量同题小说的事。《瀑布守门人》写作最终定稿的时间是在七夕节,除了致敬老田,这本集子扉页的献词是“献给20年代”,看上去轰轰烈烈,有如情书一样,说说你的动因?
弋舟
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奥,“人间纪年”这个系列写到第四本了,循例,每一本我都郑重地写下了献词,用以承载我个人的情感而已。这一本“献给20年代”,看上去壮阔了一点,但我觉得也还能映照自己的一己之情。这个认领是写到最后一篇小说时才涌现的,它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在微信群里,有人没头没尾地说了句“所有世纪的20年代都辉煌”,那一刻,是2019年的年末,距离“辉煌的20年代”仅有一步之遥。当我写下这个情节的一刻,突然就决定了这本集子将献给谁了。就献给时光吧。何况,这个系列的创作本就是藉由时光之名。小说中,我写到了疫情,这是世界迈入20年代门槛后遭遇到的最大事件,延宕两年,辛丑岁末,我又在亲历着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封城,凡此种种,似乎心情不“壮阔”一点都不行。现在看,这个献词与这本集子是协调的,当我写出第一篇《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时,也许这个献词就已经在结束的地方等着我了。一切都关乎着时间,我们就是这样难以摆脱即便是略显矫情的对于观念的依赖。我们早已被一切命名,不过是妄图去命名一切。
当然,写下这个献词,我仍旧难以信任自己已然身在了辉煌之中;但是,既然写下了这个献词,那么,我便全然相信自己已然身在了辉煌之中。
李音
把小说集献给一个年代,令人有莫名的感动。我不太清楚究竟所有的20年代到底有什么共同的辉煌,但隐隐感到自己迈进的这个20年代,可能意义非凡。据说一些哲学家预言传统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要完蛋,那么,像我们这样昼夜谈论文学,基本就是前未来动物的行为了,很古典。
对于何谓“事件”,阿甘本举过一个例子:两人满怀激情的相遇相爱,会转变人的一生,由此开创共同生活,这次相遇就构成一个爱的事件;同样,当一次偶然的社会叛乱催生出新的普遍解放愿景,开启了重塑社会的进程,这次暴动就成为一个政治的事件。而你,视“当女人以某种方式朝你张望”为一个文学的事件。
仅就历史、社会观察而言,稳健持重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到激越的哲学家齐泽克,都从不同角度出发,认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去政治化,去事件化的世界,是一个正在对以往的革命性事件进行撤销的世界,公共领域在萎缩,男男女女很难变成政治上活跃的公民,世界局势看起来风起云涌、波橘云诡,但真正的、广义的政治事件的发生,并不乐观。齐泽克讽刺资本主义世界每日迁流不息,就是为了让一切保持不变,事物层出不穷的变化,也是为了让一切不变,年轻人都在“爆肝”,当社畜,但却没有新的解放之路,因为每个人都成为了拥有自己劳动力的资本家,自己(并非自由地)疯狂压榨自己。一些看不见的壁垒阻止着新事物的产生和真正事件的发生。生活看上去刺激极了,各种讯息和突变令人瞠目结舌,但大家又感觉所谓命运、生活都在固化……
这一切看起来也许离《辛丑故事集》有点远,但《鼓楼》一篇不是写到了吗?——人生到哪里不是“打尖儿”?不是每个城市都有鼓楼,但处处又有鼓楼。怎么定义有和没有?世界简直需要我们去参禅悟道、领悟偈子了。你的整体文学观念与感受力,以及“刘晓东三部曲”等等之前的作品,都在佐证着我的判断。
真正的事件将会转变这个世界的规则,那不是简单的变化,而是开创出新的普遍原则。不过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先接受我们身在这个时代的事实。霍布斯鲍姆对将一切都以“后××”来定义很悲观,这些前缀像葬礼一样,它们对死亡做了正式的承认,却没有对死后生命的本质达成共识,也不认为死后生命的本质具有某种确定性。接受分裂与破碎,也许比简单地追求某种普遍性更重要,因为在承认破碎与坍塌中,我们将重新去定义什么是“爱”什么是“政治”。于是,从瞩目和截取一个个微型的事件开始,这很重要。就此而言,我们应该致敬自己的20年代。
但是人也不能过于执念自己的维度。宇宙和自然有其人所不能掌控的巨大的偶然性。最近汤加火山还爆发了,地球上必定有着诸多的灾难并没有被我们广泛地意识到,此刻,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正感觉自己的失恋比汤加火山爆发更具灾难性。《辛丑故事集》写于灾难频仍的时期,但只在《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有一笔提到了疫情,而整部集子以很多自然装置——群山,海峡,宇宙瀑布,还有化学键理论,从文学的意义上回应了当下的世界与人的处境。这一切还远未结束呢。所以你看,小森康夫说的对:事件是文学性的,虚构才是现实的根源。我们需要《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里的那个钟声,你说的也对,冥冥之中,这个钟声构成了一个序曲——我们需要一个个奇迹,需要某些瞬间的神来之笔。
弋舟
感动何其重要,尤其它还出自宝贵的“莫名”。致敬20年代,也许本身就是对于我们“此在感”的一个确认,是一个当代人的“当代”自觉。人类理性愈发捉襟见肘的时刻,没准感动的莫名升起也不失为一种方案。我们在小说中定义爱,政治,从微茫的当代瞬间学习理解宇宙,这些努力,即便愚蠢,也自有其密码一般的效力。
现在,一本集子完成了,也许反而一切刚刚开始。
谢谢李音,和我一同展开了这次“自己(并非自由地)疯狂压榨自己”。
- 《瀑布守门人》:生命亲情的疏离与交融[2022-03-07]
- 《一飞冲天》:在生活中思考,在思考中生活[2022-01-27]
- 《瀑布守门人》创作谈:短篇小说的随机性和规定性[2022-01-20]



